在中国诗论史上,以断代论诗,并非从严羽开始。司空图的《与王驾评诗书》就曾对诗歌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唐诗的变迁作了简要的勾勒,并给予李、杜以最高的评价。而严羽则从断代的角度更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诗史观,充分体现出史、论、评结合的特点。这种诗史观是奠定在诗识的基础之上的,而他的诗识常常是通过不同朝代诗歌作品的比较而加以呈现的。严羽对具体诗歌作品的评论,也体现了他的诗史观。其中涉及到诗之为诗的本质,即对诗歌宗旨的认识,还涉及对体裁、体式和风格变迁的认识,并将具体的诗人放到整个诗歌史的发展进程中去把握。他对唐代诗歌不同阶段的划分,对以盛唐为法的标杆的树立,以及扬唐抑宋的态度等,都对明清时期的诗史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同朝代诗歌的区分标准严羽的诗史观,首先是奠定在他评判诗歌品第优劣的审美标准的基础上的,他对不同朝代诗歌的区别,乃是以具体的审美标准加以划分的。同时他对诗歌流变的看法也影响了他的品第标准。在严羽看来,通过对不同时代的诗歌审美风貌的辨析与考察,可以看出它们的特点和流变规律。南朝钟嵘《诗品序》强调诗歌是春风春鸟、秋月秋蝉等感荡心灵的产物,是嘉会、离群者寄托情思的家园。严羽继承了钟嵘等前人的观点,强调“诗者,吟咏情性者也”,并重视诗歌的审美特点,以“悟”“气象”和“词、理、意兴”等范畴作为品评标准,以此区别不同朝代诗歌的特点。
严羽以“悟”作为诗歌的评价标准,把“悟”看成是诗歌的“当行”、“本色”,以悟来区别汉魏、盛唐和其他诗人的诗歌。严羽的“悟”是指诗歌创作和鉴赏活动中的直觉思维方式,是一种瞬间灵感降临、豁然贯通的感觉。而妙悟,则是悟的最高境界和最好的感觉。严羽认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他把“悟”分为“不假悟”、“透彻之悟”和“但得一知半解之悟”,以“悟”的程度来界定诗的优劣,以“悟”的深浅作为不同朝代诗歌的评价标准。“悟”是诗之为诗的当行本色。孟浩然的诗远远高于韩愈,就是因为“妙悟”。严羽极力推崇汉魏诗人的不悟而悟,是自然的真情流露,同时也推崇谢灵运至盛唐诗人的“透彻之悟”,他们都是第一义的,是第一流的诗人,他们的诗作就是第一流的诗作。

严羽
严羽以“气象”作为诗的五法之一。“气象”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中多用来指涉艺术作品呈现于外的神采和风格特征,不同朝代的作品在“气象”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严羽的“气象”是指作品本体呈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包含着时代的烙印和诗人的个性特征。在《沧浪诗话・诗评》中,严羽以“气象”论诗:“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强调汉魏诗歌整体“气象”的自然混成。他把“气象”作为区分唐宋诗的标准。“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他以气象划分唐宋诗歌的整体风貌,扬唐而抑宋。严羽删除谢朓《新亭渚别范零陵云》中的“广平听方籍,茂陵将见求”一联,原因正在于其余八句作为整体的气象浑成。他还根据气象甄别诗人的具体诗歌作品。如晁文元家所藏的陶诗中,《问来使》虽然很好,“然其体制气象,与渊明不类,得非太白逸诗,后人谩取以入陶集尔”。“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民间以为是杜甫诗句,黄伯思把它编入杜甫诗集,都是不对的,严羽认为它“决非盛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这些都是严羽以“气象”评判诗歌时代及诗人的实例。
严羽还以“词”“理”“意兴”的不同特点,界定不同时代的诗歌特征,作为诗歌历史分期的内在依据。其中的“词”是指文辞及其藻饰,包括音节等语言形式。“理”是指内在的思想,包括客观事物的规律和社会法则等。“意兴”是指物我相遭,由外物所感发的情意,包含着趣味,是意与兴的统一。严羽在《诗评》中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他认为南朝诗歌辞采华丽,但缺乏深刻的意蕴;宋代诗歌力图表达深刻的意蕴,但在意味的感发方面显然不够,所以会有“以文字为诗”的诗歌;唐代人则在意味的感发中包含着深刻的意蕴;而汉魏之诗,其中的词、理和意兴,则浑然天成、融为一体。郭绍虞说:“意与兴相统一,意象相化,情景交融,故盛唐诸公称为透彻之悟;词理意兴相统一,则‘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故‘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严羽虽然强调“以盛唐为法”,并没有刻意主张盛唐高于汉魏晋。严羽虽然强调诗歌“非关理”、“不涉理路”,但是诗歌要想“极其至”,必须多穷理。理要像水中盐、蜜中花那样包含在诗中。所以南朝人“病于理”、宋代人“尚理”而缺少意兴,都是不妥的。唐代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诗歌词、理、意兴不着痕迹地水乳交融在一起,这两种形式,才是优秀诗歌的形式。
诗体的源起与流变在《沧浪诗话》中,严羽要求“辨体制”。严羽以“五法”辨诗,所谓“五法”,即“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而“体制”居“五法”之首。严羽所谓的体制,包括体裁、体式(格式)和体貌(风格),而体貌他有时称为“家数”。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严羽再三强调体制,他批评吴景仙不分体制,并以能辨尽诸家体制而感到自豪:“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今人作诗,差入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市缣帛者,必分道地,然后知优劣,况文章乎?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吾叔试以数十篇诗,隐其姓名,举以相试,为能别得体制否?”严羽主张通过体制分辨出好诗坏诗,哪一朝代的诗,乃至哪位诗人的诗。他提出以盛唐为法,也与盛唐古今体制成熟、诗体大备有关。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对很多诗歌的评价,大都是从体制入手的,他的诸多考证也是辨体制的结果。这也是他所说的作为赏析和评论诗歌能力的“识”的表现。
严羽强调楚辞汉魏晋的诗体源流,其中以楚辞为本。严羽认为:“功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对楚辞的追溯,就是向上一路。在《沧浪诗话》中,严羽故意避免谈《诗经》,这是对儒家诗教观的一种矫枉过正。严羽从诗体的角度简要明确地概括了诗歌的流变历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的第一部分就提到“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他继承了刘勰的诗歌通变观,大致勾勒出了《诗经》以后我国古代诗歌体裁发展的几个重要的阶段,抓住了诗体流变的脉络。他对不同时代的诗歌体裁特征及诗人个性的分析也颇为精准。
严羽在对诗体的罗列中,强调了汉魏晋时代对诗体的开创之功。中国古代大量的诗体,源于汉魏晋。严羽说:“五言起于李陵苏武或云枚乘,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四言起于汉楚王傅韦孟,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三言起于晋夏侯湛,九言起于高贵乡公。”从诗句的字数追溯诗体的源流。在“以时而论”的诗体分类中,汉末魏晋南北朝就占了八种,分别为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和南北朝体。唐代仅分五种,即初唐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而宋代,严羽也只分了本朝体、元佑体和江西宗派体三种。

严羽
严羽尤其强调汉魏晋诗歌在开创诗体中的重要作用。他所举的诗体例证大都来自汉魏晋诗歌。例如:“有半五六言(晋傅玄《鸿雁生塞北》之篇是也),有一字至七字(唐张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应诏有三十字,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为法,故不列于此也),有三句之歌(高祖《大风歌》是也。古《华山畿》二十五首,多三句之词,其他古诗多如此者),有两句之歌(荆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诗有《青骢白马》《共戏乐》《女儿子》之类,皆两句之词也),有一句之歌(《汉书》‘枹鼓不鸣董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汉童谣‘千乘万骑上北邙’,梁童谣‘青丝白马寿阳来’,皆一句也),有口号(或四句或八句),有歌行(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长歌行、短歌行,又有单以歌名者行名者,不可枚述),有乐府(汉成帝定郊祀立乐府,采齐、楚、赵、魏之声以入乐府,以其音词可被于弦歌也。乐府俱被诸体,兼统众名也),有楚词(屈原以下仿楚词者,皆谓之楚词),有琴操(古有《水仙操》,辛德源所作;《别鹤操》高陵牧子所作),有谣(沈炯有独酌谣,王昌龄有箜篌谣,穆天子之传有白云谣也)。曰吟(古词有《陇头吟》,孔明有《梁父吟》,相如有《白头吟》),曰词(《选》有汉武《秋风词》,乐府有《木兰词》)”等等,都是汉魏晋诗体多样化的例证。这一方面证明了很多诗歌体式源自汉魏晋,另一方面严羽也是在说明从楚辞、汉魏晋诗走向盛唐的诗歌体式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严羽还根据诗句的字数划分四言、五言、七言等,还包括不常见的半五六言、一至九言等;又以乐府歌谣的曲调不同而分成的歌行、琴操、谣、吟、词、引、咏等,都是和音乐配合的诗歌体裁;因抒发感情的色彩不同,分为叹、愁、哀、怨、思、乐、别等;此外,他还从作诗的声律不同各分其类,乃至将“四声”、“八病”等形式要求也归为诗体,当然他本人反对拘泥于此,“作诗正不必拘此,弊法不足据也”;由于文人的作诗方式不同,他把一些隐语、字谜等文字游戏方面的诗歌类别也一一罗列。其中虽然存在分类标准不明确、杂乱堆放的缺点,但基本上已经涉及了南宋时代所能见到的各种诗歌的体裁,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从严羽的体制的划分中可以看出他“体”、“格”、“法”不分的毛病,在分类上也有重叠和分类方法不一致的现象,例如永明是齐的年号,齐、梁都属于南朝,再加一个南北朝体,就显得重叠。而江西宗派体也与以时代划分的分类方法不一致。后面的“以人而论”中,严羽在韦苏州体、柳子厚体之外,又加韦柳体;在白乐天体之外,又加元白体。这种“韦柳”和“元白”的合称,说明了在各自的个性风格之外,两人有共同的风格。如果对《沧浪诗话》作同情的理解,可以看出,这种划分实际上也反映了诗体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合而言之和分而论之均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严羽还根据几部选集将诗歌划分为“选体”、“香奁体”、“玉台新咏体”等,是颇有见地的做法。因为选诗者无疑应该有自己对体制的卓识,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选者个人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唐代殷璠就曾经在《河岳英灵集》序中说:“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认为辨体是编诗者的首要责任。

《沧浪诗话》
严羽的诗歌流变论,除了诗歌的体式流变外,还强调了诗歌风格的变迁,其中包括时代风格和作者的个人风格及其变迁。在讲到时代风格时,他特地强调诗歌语言风格的差异。“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如此见,方许具一只眼。”大历以前、晚唐和宋代的诗歌,在语言风格上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在讲到个人风格时,严羽以唐诗为主。在唐以前,严羽列举了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五种。宋代他则举了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七种。而唐代,他从沈宋体到杜荀鹤体,一共列举了二十四种,是汉魏晋和宋代相加的双倍,这既是唐代诗体大备盛况的表现,也足见严羽对唐代风格的重视。这些风格的区别,在《沧浪诗话》的其他部分,也得到了具体运用。如《考证》中:“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数句类太白,其他皆浅近浮俗,决非太白所作,必误也。”而在探讨五言绝句风格时,则体现了他对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综合运用。他说:“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朝诸公是一样。”充分体现了他对风格辨析的能力。诸如“《木兰歌》最古,然‘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之类,已似太白,必非汉魏人诗也。”既说明了个人语言风格的差异,又说明了时代语言风格的差异。
严羽不仅罗列了各种诗体,阐明了它们的流变,还高度重视诗歌的兴致,重视诗歌的“吟咏情性”,言之有物,重视生活中真情实感的流露。他认为:“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对于各种游戏诗的类型,严羽批评它们“只成戏谑,不足法也”。他甚至批评“和韵最害人诗”,都是一些炫才逞技的花样。这也影响到了明清的一些学者。如王世贞说:“和韵联句,皆易为诗害而无大益,偶一为之可也。”同时,对于诗歌的格律,严羽也不过分拘泥。“有律诗彻首尾不对者,(盛唐诸公有此体,如孟浩然诗:‘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轴轳争利涉,来往接风潮。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坐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标。’又‘水国无边际’之篇,又有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八句皆无对偶。)”说明严羽不过分在意诗体形式,而更重视诗歌的言之有物,反对无病呻吟。
严羽辨体制、溯源流的很多说法都是继承了前人的提法,是此前学者辨体的集大成者。在重视体制方面,严羽受到了王安石等人的影响。严羽说:“荆公评文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而具体的体制及其名称,则早已有之。如严羽称谢灵运诗为“谢体”。《南齐书》中就有“谢灵运体”的说法:武陵昭王萧晔“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上。”《梁书》也说伏挺:“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再如严羽所说的“西昆体”,北宋惠洪《冷斋夜话》卷四就曾说:“诗到李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又如“王荆公体”的提法,南宋周煇的《清波别志》就曾提到:“秦会之忠献公自著文字,惟尚简古,自云效王荆公体。”诸如此类,都说明严羽继承了前人的诗体称谓。
严羽对辨体的重视,对体制源流和特点的分析,目的在于正本清源。从形式上看,严羽采用了以朝代的更迭作为诗史的划分依据,实际上他更重视诗歌自身的内在审美意味的变迁规律。朝代的更迭当然会带来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变化,因而影响到诗的内蕴和体裁、体式、风格等,但诗歌在形式和表达方式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和流变规律。对此,严羽重视“起”,强调“变”,深刻揭示了宋以前中国古代诗歌起源与变迁的规律,以此作为学诗者入门正、“不为旁门所惑”的基础。正是通过诗歌体制高低优劣的辨识,严羽才得出了“以盛唐为法”的结论。其中虽然有不少混乱的分类,但对明清时期的辨体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前修未密,后起专精,对于明清时代条理井然的辨体研究来说,严羽的诗体研究有着开创之功。
宗唐说严羽的宗唐说是严羽诗史观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方面。严羽不仅对唐代诗歌的诗史地位做出了恰切评价,其宗唐的诗史观也深深影响了明清诗学中的宗唐抑宋观念和四唐分期等观念。严羽的宗唐说包括五唐分期、以盛唐为法和扬唐抑宋三个方面。这与宋代江西诗派、四灵诗人、江湖诗派和王安石等人推崇晚唐有着本质的区别。

司空图
首先是五唐分期说。唐诗分期并非从严羽开始。司空图的《与王驾评诗书》:“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琼,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焉。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指出了唐诗从唐初由于统治阶层的喜好而发展,走向顶峰,又由盛而衰的变化特征,其中已有唐诗分期的端倪。欧阳修、宋祁编撰的《新唐书》也有唐诗分期的阐述。北宋理学家杨时曾说:“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杨时明确提出了盛、中、晚三唐说,而惟“元和之诗极盛”的说法与后来的诸位理解不一。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把唐代的诗歌分为初唐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抓住了诗歌特殊的时代特征。《沧浪诗话・诗辩》说:“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中虽然有开元、天宝与李杜二公的分开论述,但从时间和内容、乃至气象上看,他们的诗歌属于盛唐之诗,只是将李杜独立开来,加以突出,给他们一个特写而已。而对于大历和元和时期,严羽分开说也有他的道理。事实上,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已经渐渐褪去了盛世的繁华,诗人们的信念和理想受到了摧残,诗人及其诗作也失去了昂扬的斗志和磅礴的气势,大历至贞元、永贞年间的诗歌骨气衰微,大历才子们多寄情山水,崇尚精工,呈现出幽清冷寂的诗风。到唐宪宗元和年间,元稹、白居易发起新乐府运动,推崇通俗、写实的文风,针砭时事,重视诗歌的教化功能,这与大历才子们的诗风是截然不同的。当然大历和元和的诗风显然已经没有了盛唐气象,这一点是相同的。所以,严羽有时把“大历十才子之诗”和“元和之诗”统称为“大历以还之诗”,加以贬抑,其中实际上已经有了“四唐说”的端倪。这种对唐代诗歌的分期,体现了严羽的史识。
严羽的唐诗分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中就有唐初、盛唐、中唐和晚唐的说法,已经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他在评论许浑《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时说:“予选诗以老杜为主,老杜同时诸人皆盛唐之作,亦皆取之;中唐则大历以后、元和以前,亦多取之。晚唐诸人,贾岛开一别派,姚合继之,沿而下亦非无作者,亦不容不取之。”惟唐初与严羽不类。他在多处诗歌评论中申述“四唐”思想。如评陈子昂《晚次乐乡县》云“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晚唐下细功夫,作小结果,所以异也。”与严羽思想基本合拍。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继承了这种“四唐说”分期主张,把元和体视为趋于晚唐之变,加以具体而明确的阐述,为后世的诗歌史研究广泛采纳,一直沿用至今。朱东润《沧浪诗话参证》云:“元至正四年杨士弘辑《唐音》成,分列唐代作家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即隐宗沧浪之说。明初高棅继之作《唐诗品汇》,遂为明代之权威,朱彝尊《曝书亭集・高棅传》所谓‘终明之世,馆阁宗之’者指此,而沧浪之主张,亦由此书间接影响于当世。”罗根泽也说:“自元人杨士宏撰唐音,明人高棅撰唐诗品汇,论唐诗的每分为初、盛、中、晚四期,穷源索本,实始严羽。”查元代杨士弘的《唐音》以音辨诗,从音律正变的角度分期,有所谓“始音”、“正音”、“遗响”,而“始音”中初唐类似于方回,只录“四杰”,而初唐的“沈、宋”、陈子昂与盛唐并未分开,而“遗响”也不分类,大抵只是按照严羽五唐的顺序加以排列,与严羽的五唐说和高棅的四唐分期并不对应,不知朱东润、罗根泽先生何出此言?抑或罗根泽先生乃人云亦云,沿袭朱东润先生之误?
其次是“以盛唐为法”。“以盛唐为法”本身体现了严羽品第诗歌的审美标准。这个法,不仅是后人效法的楷模,而且是法度和规则。从楷模的角度讲,首先要讲究诗道在于妙悟,要达到盛唐的“透彻之悟”。从法度和规则的角度讲,要在诗法上学习盛唐诗人。严羽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其中就包括了形式上的体制和音节。在体制上,严羽之所以重视以盛唐为法,并不是贬低楚辞汉魏晋,也不是简单地因为盛唐高于汉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众体兼备,近体律诗和绝句等已经成熟,诗体到盛唐已经大备了。他自己解释说:“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汉魏和盛唐在严羽那里都是“第一义”的,都是最优秀的,他对阮籍、谢灵运、陶渊明等人的诗,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就是说,汉魏有的,盛唐也有,盛唐还有汉魏所没有的近体律诗等。朱霞《严羽传》称严羽:“论诗推盛唐,谓:后之过高者多法汉、魏而蔑视盛唐,不知诗之众体至唐始备,唐之不能为汉、魏,犹汉、魏之不能为唐也。”同时,严羽还重视音节。诗歌的语言应该具有音乐性,具有“一唱三叹之音”,言有尽而意无穷。“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宮商之声。”强调音节的重要性。“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八句皆无对偶。”可见,在严羽看来,音韵比对偶更重要。
同时,他对盛唐的推重,还包括侧重于内容的格力、气象和兴趣。格力是指诗歌作品中体现内在生命力的骨气。他所谓:“李杜数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这里的“金鳷擘海、香象渡河”,指的就是盛唐诗歌的格力。他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评价盛唐之诗“雄浑悲壮”、“笔力雄壮”的特点,就是所谓的“格力”。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盛唐诸公之诗“气象浑厚”。他在《沧浪诗话・考证》中指出:“‘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决非盛唐人气象,只类白乐天言语。”正是强调盛唐诗歌有其独特的气象,有时乃至“似粗而非粗”,“似拙而非拙”。严羽也以“兴趣”为盛唐诗歌的标志性特征。严羽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诗歌中的“兴趣”,是作者在外在物象或事象的感发下,将情性融铸于诗歌的意象整体,从而产生含蓄蕴藉的效果。兴趣是盛唐诗歌优越于其他时期的重要标准。这种空灵剔透、无迹可求的“兴趣”,“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以感性意象本身获得感染力。而所谓别趣,则是在强调诗歌兴趣的独特性。

严羽
严羽最推崇的是汉魏晋盛唐诗歌,他尤其重视盛唐诗的传统,将盛唐诸公之诗比为“大乘正法眼者”,说明诗之为诗,有法可依,反对误入歧途。他要求“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他对江西诗派、江湖诗人和四灵诗人的批评都是奠定在以盛唐为法的基础之上的。当时四灵诗人也曾反对江西诗派,主张复古,可惜他们复的是晚唐,却也自诩为唐音。严羽批评四灵诗人和江湖诗人,说他们独喜贾岛、姚合之诗是在学习坏榜样:“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同样宗唐,四灵诗人和江湖诗人的路子不对。他们不是效法盛唐,而是偏好贾岛、姚合的清苦之风,严重背离了严羽所说的诗道正大的精神。
严羽认为,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巅峰之作。在严羽看来,盛唐诗歌的最高境界,就是李杜的入神境界。“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要求学诗者像做学问研读经书那样研读李杜的诗:“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在阐述熟参各朝代诗歌并进行比较的时候,他特地说“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一个“独”字,表明严羽对李杜的特别强调。“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李、杜数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这是对李杜磅礴的气势和骨力的形容。他称颂“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高度赞扬李白“开门见山”的起头。他还继承李阳冰《草堂集序》的说法,称李白的诗是“天仙之词”。他说杜甫“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这种“自得之妙”和“集大成者”的说法,正是对杜甫的崇高评价。以严羽率直的个性,完全相信他对李杜的评价是真心实意的。
第三是扬唐抑宋说。在竭力推崇盛唐和李杜的基础上,严羽激烈地批评宋诗。他继承了北宋魏泰、叶梦得、张戒等人指摘苏黄和江西诗派的诗歌在议论、用事、押韵等方面的偏颇之处。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就曾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在前人的基础上,严羽从透彻之悟、气象、兴趣,以及词、理、意兴的关系和音乐性等方面肯定唐诗,批评宋诗。他主要批评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 ,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对于苏轼、黄庭坚自出己意,乃至以文为诗,改变了诗之为诗的审美特征,完全抛弃传统,不合于古人之诗,偏离了诗歌的正确轨道,严羽则给予否定,认为他们不符合汉魏晋盛唐古人诗之为诗的传统,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他评价杨万里的创新,也属于微词:“杨诚斋体。其初学半山后山,最后亦学绝句于唐人。已而尽弃诸家之体,而别出机杼。”这里“别出机杼”的评价,也在批评杨万里象苏轼、黄庭坚一样自以为是、别出心裁。

刘灼
严羽同时代的刘克庄也曾说宋诗:“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这也开启了后代争讼不绝的唐、宋诗之辨。钱钟书所谓:“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显然也受到了严羽的影响。而在唐诗的发展动因上,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还强调外在条件对诗歌发展的影响:“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他提出了促进唐诗发展的动力,即科举制度推动了唐代诗歌的繁荣。对于严羽崇尚盛唐,一味批评宋诗探索的态度,当时和后世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严羽有偏颇之处,或者替宋诗辩解。如刘克庄曾说:“然谓诗至唐犹存则可,谓诗至唐而止则不可。本朝诗自有高手。”尽管严羽认为宋代也有合于古人、即合于汉魏晋盛唐的诗,但他对宋诗总体上确实是持贬抑态度的。而刘克庄为宋诗辩护,针对的就是严羽的这种态度。清初邵长蘅也说:“诗之不得不趋于宋,势也。”更是把宋诗的风格特征看成是大势所趋。清代蒋士铨《辩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则为宋诗所处的历史境遇提出辩护。
正变观中的辨证意识从诗歌正变观的角度看,严羽重视诗之为诗的自身特点,要求以楚辞为本,倡导以汉魏晋与盛唐名家为榜样。他提出“先须熟读楚词,朝夕讽咏,以为之本”,而“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他要求向上一路,以楚辞、汉魏晋至盛唐的名家诗歌传统为本,酝酿胸中,自然悟入。在此基础上,他又强调“变”,这个变,既包括由楚辞向盛唐的变,代表了历史的正确方向;又包括中晚唐向宋代诗歌的变,则是错误的方向。严羽要求诗歌的流变应当遵循正确的方向。他肯定诗歌由楚辞向汉魏晋和盛唐诗歌发展的方向,而贬抑晚唐和宋代诗歌的发展方向。他以盛唐诗歌为顶峰,认为此前的诗歌是不断发展的,到盛唐诗体大备了。而中晚唐诗歌则开始衰微了,宋代的变化更使诗歌走向歧途,而且“路头一差,愈鹜愈远”。因此,他要求拨乱反正,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但是,严羽也不是简单地推崇楚辞汉魏晋盛唐诗歌,而否定其他一切诗歌,也没有简单地认为楚辞汉魏晋盛唐诗歌乃至李杜诗歌涵盖了最优秀的诗歌。以朝代论诗只是就大体而言的,其他诗人依然有优秀的诗歌,诸如律诗、绝句等,汉魏晋盛唐之外依然有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从中体现了严羽正变观中的辨证意识。美国学者宇文所安认为:“《沧浪诗话》的流行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或许是最严重的),那就是把盛唐诗经典化了,唐诗从此成为诗歌的永恒标准,其代价是牺牲了中晚唐诗人。”这种说法是偏颇的。首先,诗至盛唐,到达了一个顶峰,出现了李杜这样的大家,把盛唐诗经典化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例如严羽认为:“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杜甫就是一个好榜样,杜甫的诗歌就是经典。其次,对于具体的诗人,严羽也没有绝对地以朝代评诗。严羽认为:“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他要求“合于古人之诗”,即合于楚辞、汉魏晋与盛唐的优秀诗歌,而非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一切古人之诗。因此,严羽并没有全盘否定中晚唐诗歌,也没有全盘否定宋诗。根据同样的标准,汉魏晋盛唐之外的诗歌,也有不少得到了严羽的好评。这就是继承优秀传统,把真正的好诗发扬光大。
严羽在评价不同时代的诗人时,虽然以时代对诗歌的价值和特点进行评价,但他并没有作简单的褒贬,而是重视诗人的个体差异。在总体评价的基础上,严羽并不是简单地以诗人所处的时代划分诗人的等级,单纯地以时代论诗。他重视具体诗人和诗作的特殊性,辩证地看待个别诗人超越时代的特点。“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以古人之诗的建安风格称许阮籍的《咏怀》。“谢朓之诗,有全篇似唐人者。”唐诗成熟,以唐人来对谢脁加以肯定。而对于建安七子中的刘桢《赠五官中郎将》“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王粲《从军行》“窃慕负鼎翁,愿迈朽钝姿”,严羽批评他俩以商汤、刘邦作为圣君比喻曹操,拍曹操的马屁,这是严羽所不屑的。在汉魏晋诗人中,严羽对谢灵运的评价甚高,把他与盛唐诗人并提:“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甚至说:“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但是当严羽把谢灵运与陶渊明放在一起比较时,又认为谢诗不及陶诗:“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这些对具体诗人的评价,都体现了严羽的辨证意识。

顾况
严羽也并没有简单地肯定盛唐的诗人,而绝对否定晚唐的诗人。他认为盛唐也有少数差诗,晚唐也有好诗,不搞一刀切。“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严羽说:“冷朝阳在大历才子中为最下。马戴在晚唐诸人之上,刘沧、吕温亦胜诸人。李濒不全是晚唐,间有似刘随州处。陈陶之诗在晚唐人中最无可观,薛逄最浅俗。”他也看到诗人的创作风格在诗史流变中有交叉和延续。“戎昱在盛唐为最下,已滥觞晚唐矣。戎昱之诗有绝似晚唐者。权德舆之诗却有绝似盛唐者,权德舆或有似韦苏州刘长卿处。”“顾况诗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风骨处。”“大历以后吾所深取者,李长吉、柳子厚、刘言史、权德舆、李濒、李益耳。大历后刘梦得之绝句,张籍、王建之乐府,吾所深取耳。”其中体现了严羽注重个体差异性的辩证观点。
当然即使对那些不学盛唐的宋代诗人,严羽也没有全盘否定,只要他们是符合汉魏晋盛唐等古人传统的,严羽都加以肯定。“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可见,严羽虽然要求以盛唐为法,但他不反对学习中唐白居易、晚唐李商隐,只要符合汉魏晋盛唐之诗的精神。但是学习的榜样也是有选择的。宋诗中的优秀诗作“合于古人者”,也被严羽所肯定,如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集句惟荆公最长,《胡笳十八拍》浑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腑间流出。”王安石能将集他人诗句如出一己之手,符合严羽所推崇的汉魏晋那种“不假悟”的浑然天成的风格特征。
严羽对李白与杜甫诗歌的评价,也反映出他对多样风格的推崇,而不是简单地以个人风格偏好作取舍。“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其中体现了严羽风格多元的价值取向。当然这也受到了前人和时人的影响。例如王安石就曾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在《沧浪诗话》中,严羽与宋代流行的扬杜抑李明显不同,始终将李白与杜甫并举,同尊兼重,将两人的诗歌共同视为诗的最高境界,即“入神”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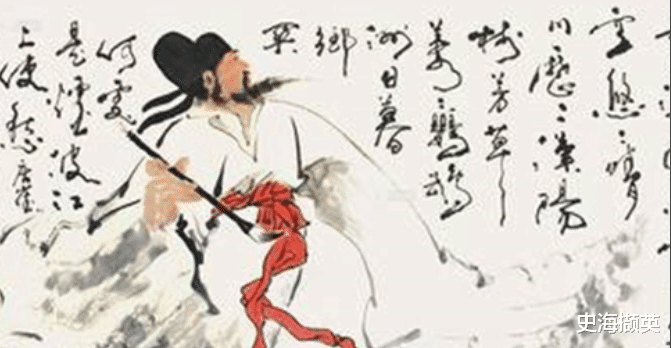
崔颢
严羽虽然认为李杜的诗歌成就最高,但并不代表在他看来所有文体的诗歌都是李杜最高。严羽对很多诗人的优秀作品都能给予实事求是的高评。他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灏《黄鹤楼》为第一。”据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李白也曾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同样盛唐的诗歌,严羽也称赞孟浩然的“一味妙悟”和“宫商金石之声”,以及高适和岑参的悲壮:“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其他如“刘梦得之绝句,张藉、王建之乐府,吾所深取耳”、“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等,都是严羽所推崇的。
宋代以前的不少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虽然前人有一定的评价,但是由于严羽的评价而得以确定,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柳宗元在诗歌史上地位的提升,即是一例。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说:“若柳子厚五言古诗,尚在韦苏州之上,岂元、白同时诸公所可望耶?”此前杨万里《诚斋诗话》和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都把韦柳诗看成一体,严羽在列出“韦柳体”的同时,还专门提出“柳子厚体”。曾季狸《艇斋诗话》云:“前人论诗,初不知韦苏州柳子厚,论字亦不知有杨凝式。二者至东坡而后发此秘。”到了严羽,柳宗元更是被视为元和杰出诗人。《旧唐书》曾说:柳宗元“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新唐书》也说:柳宗元“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严羽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力推崇离骚,认为功夫须从上而下,因此对学骚的柳宗元评价甚高。元、白被严羽看成位于柳宗元之下的诗人。元白在形式上比柳俗(严羽力倡除五俗),柳的诗歌题材多征戍、迁谪、行旅、离别等,与严羽的审美观相契合。而严羽对柳宗元的强调,一方面说明他并非因为与苏轼等人诗学观的不同而唱反调,也使柳宗元的诗歌地位得以确立。
总而言之,《沧浪诗话》是严羽要求诗歌回归楚辞汉魏晋盛唐正道的宣言,从中表明了他的诗史观。严羽以“悟”“气象”“兴趣”和“词、理、意兴”等诗歌的审美特点作为区分不同朝代诗歌特征和品第优劣的标准,厘清了诗体和风格的发生与变迁,突出汉魏晋和盛唐诗歌的典范价值。他的五唐分期、以盛唐为法和扬唐抑宋等宗唐主张,为后世的唐宋诗评价留下了精辟的见解和有争议性的话题。同时,严羽也能做到辩证地看待具体诗人在诗歌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他在诗歌体制与风格等方面的一些观点,虽然不少是借鉴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一些主张,但是他对若干诗人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对诗歌史的概括和总结,对明清诗史观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