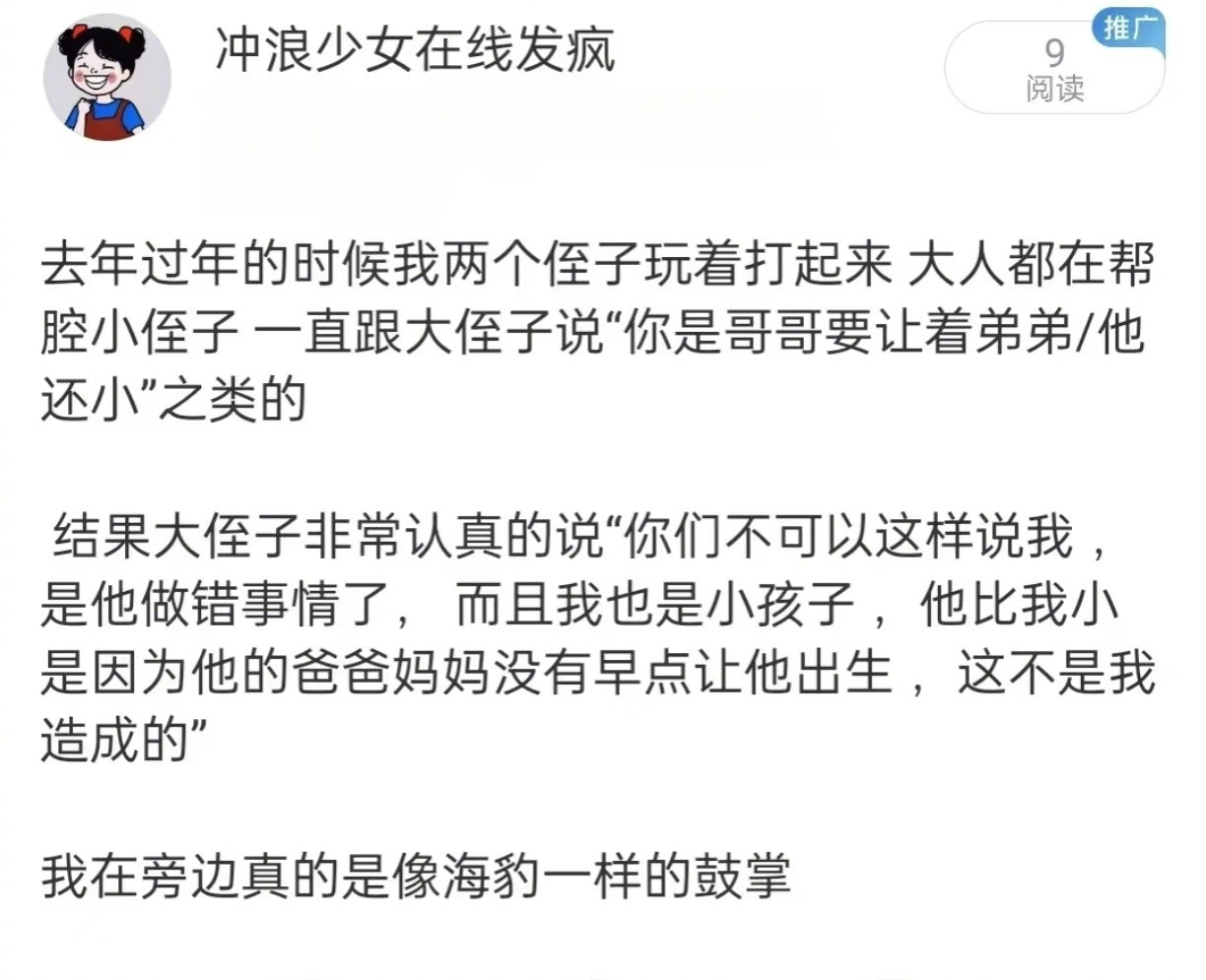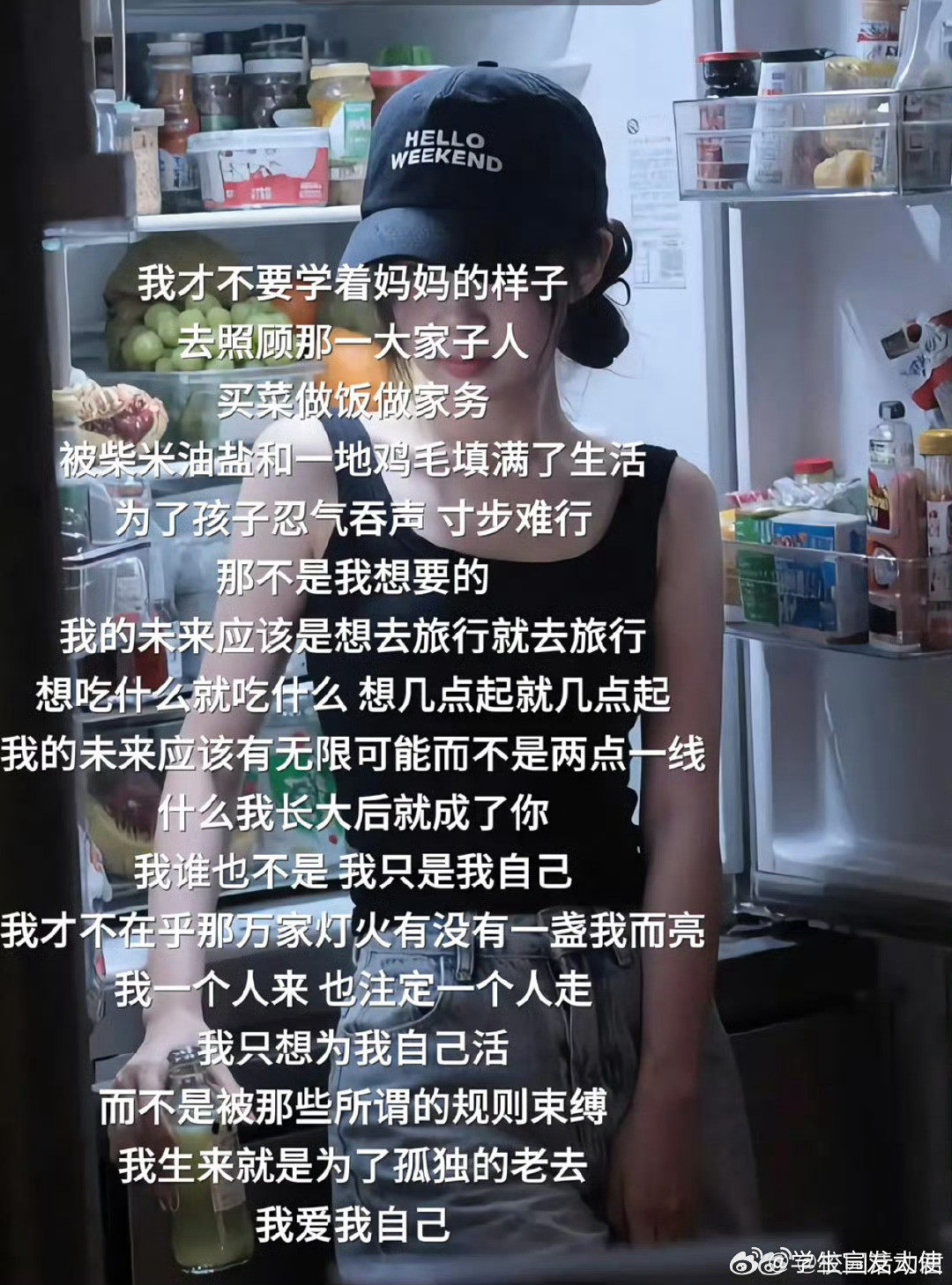七年前的事了。
我那年生娃,医生问胎盘要不要,我看了一眼,血淋淋黏糊糊的,青筋明显,那叫一个恶心。思前想后犹豫半晌,还是要了。
回去丢在案板上准备处理,我看着那一坨死肉,拿着刀比划来比划去,犹豫半晌,实在下不去手,就去找我妈。
我妈说,你不是要带回来埋啊,这是要吃啊?你连个鱼都不敢杀,你会弄么?
我吓得眼泪都快下来了,握着刀哆哆嗦嗦的说:我不会啊,那咋办啊?人家都说这玩意补身体,我爷……
我妈听懂了,让我去去去,一边跟孩子玩去,就给我轰走了。
那天晚上我们家吃蛋炒饭。“饭不够,爸,你吃饺子吧”,说着我妈就给我爷端了一碗饺子。
我爷那时候89岁了,胃癌。人已经不太能单独行走,大部分时间要么坐在他屋里,要么躺在医院,吃的也不多,一天就吃一顿饭,多了就说自己消化不了。但是,但凡他能起身,都是自己慢慢走到厨房吃饭,坚决不要我们把饭送到床头。他认为人就活一口气,躺在床上等吃就离等死不远了。他要死也要干脆利落的死,绝不要瘫在床上等人伺候。
“都行,我吃啥都行”,他拄着拐杖,撑着桌子,慢慢挪过来坐下,毫无察觉地接过碗,手里哆嗦着拿着筷子,微微倾身,慢慢往豁牙的嘴里巴拉。
我一边吃自己碗里的,一边从碗边偷偷瞄我爷。六七个饺子,他个豁牙老头慢慢吃了近半个小时,我偷偷瞄了半个小时。等到他最后慢慢捧着碗把酱油饺子汤都喝掉,我才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
反观我妈倒是神色自若,帮我爷收拾碗筷,还问他:“爸,蛋炒饭还有,再来点?”
我爷摆摆手,歇了会,又慢慢撑身起来,拄着拐杖,慢慢挪回去了。
我看着我爷的背影消失了,跟我妈交头接耳:“他没吃出来么?我还担心他吃出来呢,好腥的啊。”
我妈:“人老了,味觉会退化的——我用酒去腥了,还放了一堆姜蒜……”
我看了一眼我爷的碗底,心想,你这黑胡椒面面也没少放啊。
我爸耳背的很,全程毫无知觉,直到他吃完饭去洗碗,看到灶台上的瓶子,下一秒就开始跳脚:“你们谁把我的酒开了!我不是放在储藏室的嘛,谁把我的酒开了!我存了三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