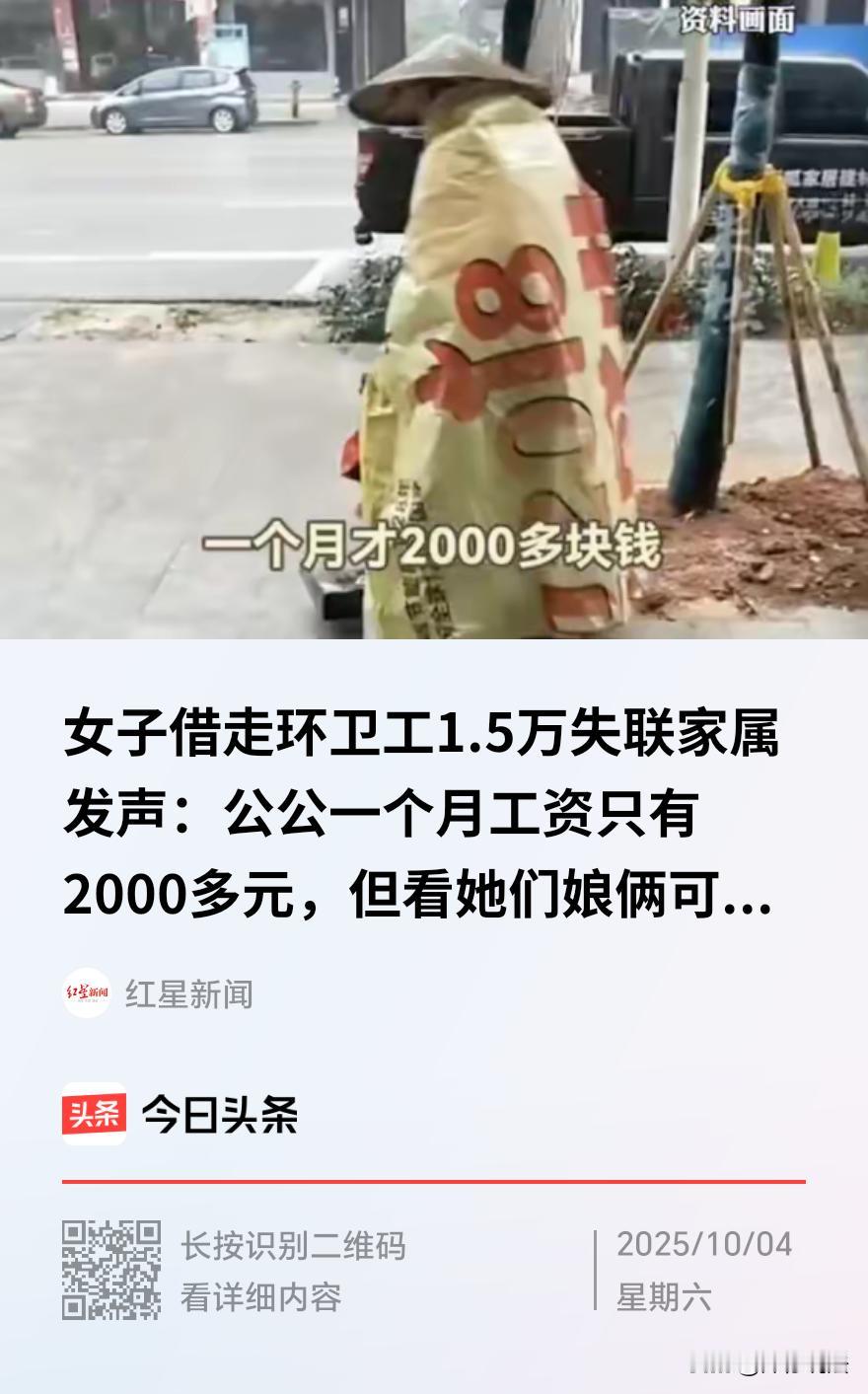浙江温州,一70岁环卫工大爷辛苦攒下15000元,这本来是自己的养老钱,不料,相识的离异带娃女子,先是哭着说家人车祸急需用钱,接着说孩子学费没着落,后来又说要后续治疗费,大爷心软,分三次,悉数借出,几乎掏空了所有积蓄。起初,女子连张欠条都没有,全凭一份信任。在家人催促下,女子虽补写了欠条承诺还款,但期限一到,她便连夜搬家和所有债主玩起了“人间蒸发”。家人后来才震惊地发现,这位看似可怜的女子,早就是法院榜上有名的“老赖”,负债累累。 张大爷(化名)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穿上橙色的工作服,拿起扫帚,开始他作为一名环卫工的工作。 张大爷的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勉强够维持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妻子早年病逝,他独自将儿子抚养长大,如今儿子已成家,但经济条件也不宽裕,张大爷便继续工作,贴补家用。 张大爷负责打扫镇上的几条街道,其中一条街旁住着一位名叫李芳(化名)的女子,李芳离异后,带着一个孩子生活,平时靠打零工度日。 张大爷和李芳并不熟络,但张大爷心地善良,看到李芳和孩子生活拮据,心里总存着一丝同情。 2025年6月,张大爷像往常一样在街上清扫落叶和垃圾,李芳急匆匆地走过来,脸上带着焦虑和疲惫,她拦住张大爷,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张叔叔,我妈妈在老家出了车祸,住院急需用钱,医院催着交费,我实在没办法了,能借我5000元钱吗?我保证尽快还你。” 张大爷一愣,他积蓄不多,但看到李芳眼里的泪水,又想起她独自带孩子的艰辛,心里一软,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第二天,他从自己微薄的存款中取出5000元,交给了李芳,李芳连连道谢,承诺等事情平息后就归还。 几天后,李芳又找到张大爷,这次她的理由更令人揪心:“张叔叔,孩子的学校要交学费,我一时凑不齐,能再借我5000元吗?我一起还你。” 张大爷心里有些不安,但看到李芳那无助的眼神,他还是同意了。 又过了一周,李芳第三次上门,说车祸的后续治疗还需要钱,恳求再借5000元。 张大爷虽然手头紧,但想着“帮人帮到底”,又凑了5000元借给她。 这样,在2025年6月期间,张大爷分三次借给李芳共计15000元,每次借钱,李芳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会尽快还款,张大爷则因为善良和同情,没有要求她立即写借条。 张大爷的儿媳妇周丽(化名)在7月底偶然听公公提起这件事,顿时觉得不对劲,觉得李芳的借款理由虽然听起来合理,但频繁借钱且没有还款迹象,可能有问题。 8月初,周丽和丈夫一起找到李芳的家,坚持要求她给个明确答复,李芳这才松口,答应写一张欠条。 8月4日,在李芳的家中,她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欠条,内容大致是:李芳向张大爷借款15000元,承诺于2025年8月30日前还清。 到了8月30日,李芳并没有如约还款,周丽多次打电话联系她,但电话总是无人接听。 9月初,周丽和丈夫再次上门,却发现李芳的出租屋大门紧锁,邻居说她已经好几天没露面了。 周丽开始四处打听,了解到李芳欠了不少人的钱,早在2024年12月就被法院列入限制消费人员名单。 张大爷知道情况后,沉默了许久,坐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低着头,手里捏着那张皱巴巴的欠条,眼神里满是失落和自责。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评价呢? 《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 张大爷与李梅之间就三次借款分别达成了口头协议,李梅提出借款请求,张大爷表示同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之后,张大爷分三次将15000元现金交付给李梅。 尽管初期没有书面凭证,但张大爷实际交付了借款,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李梅作为借款人,负有按期偿还借款的法定义务。 在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是基本原则。 张大爷一方若要胜诉,必须向法庭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借贷关系存在。 三次借款发生时,均为现金交易,且无任何收据、录音、聊天记录等佐证,在诉讼中,如果李梅出庭并否认这三次借款,张大爷将面临举证困难。 不过,张大爷可以提供李梅出具的欠条,这是对借款事实的自认,明确了借款金额、还款期限,是完整的债权凭证。 但若李梅抗辩称欠条是受胁迫所写或内容不实或没有实际交付钱款,仅凭欠条单一证据,其证明力会受到挑战。 接下来,张大爷要对李梅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李梅偿还借款本金15000元及逾期利息。 不过,李梅已是“限高”人员,偿债能力有限,即使法院判决张大爷胜诉,在执行阶段,若经查询李梅确无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可能会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这意味着,债权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暂时无法实现,只能等待未来发现李梅有新的财产时,再申请恢复执行。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