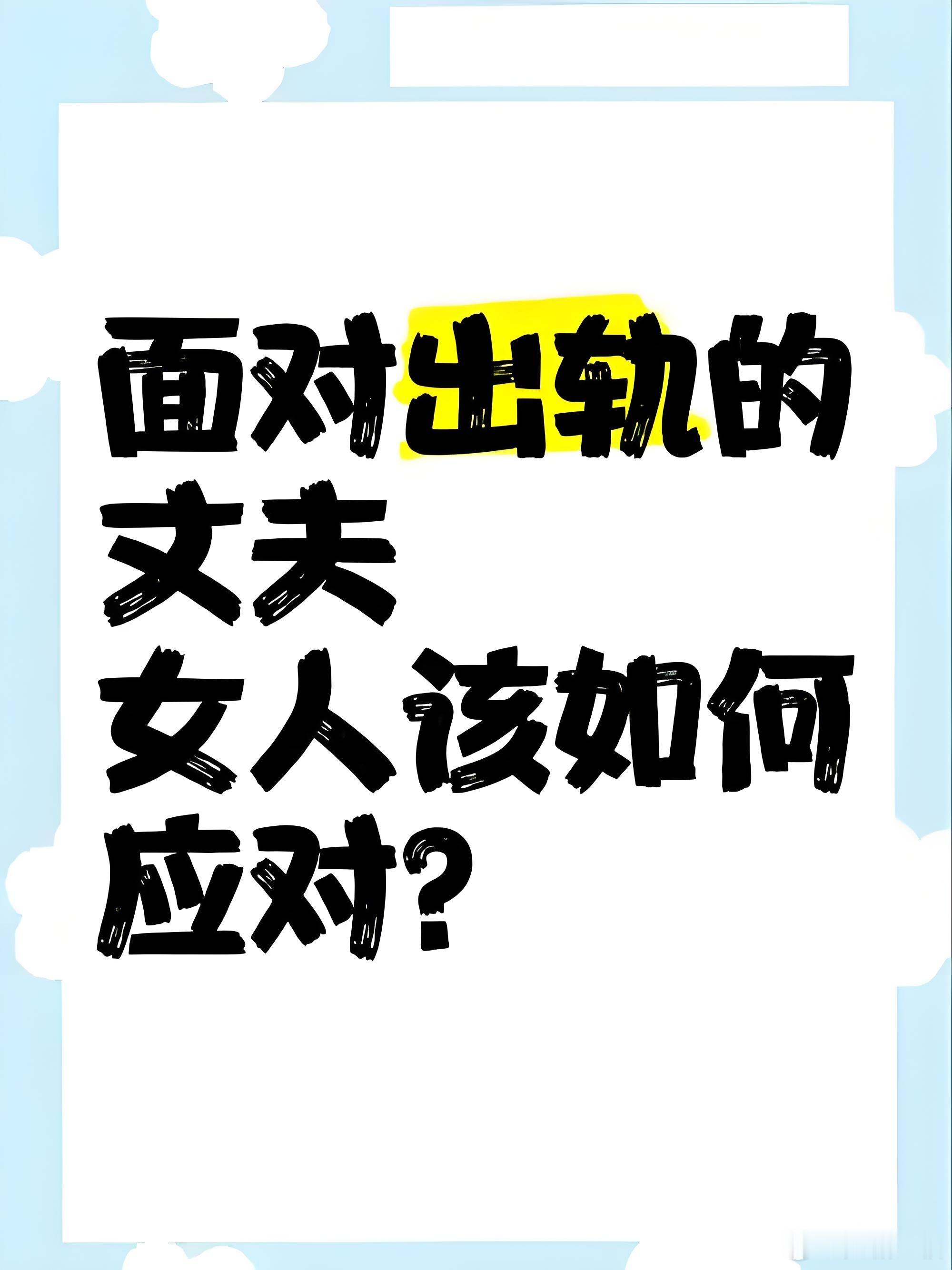李敖说: “金钱与女人的生殖系统一样的脏,可是都是男人的最爱,没有之一……” 古玩行的老师傅常说,玩古董的人分三等:下等玩真假,中等玩贵贱,上等玩因果。四十二岁这年,我才算真正懂了这句话。 昨夜清点库房,那只南宋龙泉窑青瓷碗在射灯下泛着柔光,像极了初恋小荷的肌肤。二十年了,我依然记得她递给我这碗时说:“古董最干净,比人干净。” 我的第一桶金来自一只明代官窑瓶。 那时我二十八岁,在潘家园帮人看摊。香港来的陈老板指着瓶子问价,我伸出三根手指。“三十万?”他挑眉。我摇头:“三百。” 他愣住了。其实我知道那是真品,市值至少二十万。但我更知道,陈老板的叔父是故宫博物院的专家。 三个月后,陈老板带我入行,第一单就赚了八十万。他在酒桌上搂着我的肩说:“记住,让人占便宜,就是最贵的买卖。” 那晚我醉倒在酒店卫生间,抱着马桶吐的时候,突然想起小荷分手时的话:“你迟早会变成你最讨厌的人。” 认识苏小姐是在一场拍卖会上。 她举牌的手势很特别,小拇指微微上翘,像在跳芭蕾。我以高出底价三倍的价格拍下她看中的玉佩,然后走到她面前:“物归原主。” 她笑了:“李老板果然如传闻中大方。” 后来她成了我的情人,在陆家嘴的顶层公寓里,她喜欢赤脚走在波斯地毯上,说这样像踩在云端。有一次她问:“如果我和那只汝窑笔洗同时掉进河里,你救谁?” 我认真思考的样子惹恼了她。其实我在想:笔洗还能修复,人碎了就碎了。 转折发生在三年前的体检。 医生指着CT片上的阴影说:“少碰两样东西:古董和女人。”我笑了:“那还不如直接要我的命。” 住院期间,苏小姐来了一次,带着煲了四小时的汤。她坐在床边削苹果,突然说:“我要结婚了。” 我把汤喝完才问:“他对你好吗?” “他不懂古董,”她放下苹果,“但会在下雨天来接我。” 她走后,我看着窗外的雨,想起这些年收集的每一件古董背后,似乎都有一段破碎的感情。原来我爱的从来不是物件本身,而是拥有时的征服感。 上个月整理收藏,我又拿出那只龙泉窑碗。 在放大镜下,碗底有道极细的冲线,像时光留下的皱纹。突然明白,我之所以珍藏它二十年,不是因为它最值钱,而是因为这是唯一一件,我从未想过用它换取什么的东西。 昨天有个年轻人来店里,看中了康熙时期的青花盘。他紧张地数着银行卡余额的样子,像极了二十八岁那年的我。 “拿去吧,”我把价格抹去一个零,“记得好好待它。” 他千恩万谢地离开。伙计不解:“老板,这亏大了。” 我但笑不语。有些道理,要摔过很多跟头才懂:让人占便宜,确实是世上最贵的买卖,但也是唯一让灵魂保持洁净的方式。 今晨下雨,我没去店里。 泡一壶普洱,独坐窗前看雨打芭蕉。手机里,苏小姐晒出女儿周岁照,曾经的陈老板发来破产消息。而小荷,听说在南方开了间茶室,终日与紫砂壶为伴。 我摩挲着青瓷碗的釉面,温润如初。李敖说得对,金钱与情欲确实是最脏的,但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在红尘中反复淘洗,直到能分得清:什么是欲望,什么是爱。 雨停了,阳光穿透云层。我把青瓷碗收进匣中,终于决定明天去南方走走。不是为寻回什么,只是想去喝杯茶,看看那些不曾被交易的人生。 叔本华曾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脏",并非指物质本身,而是指欲望永不满足的本质。金钱作为交换媒介,情欲作为生命本能,本无善恶之分。 但当它们成为被无限追逐的对象时,就会显现出其"肮脏"的一面,让人迷失本心,让人相互倾轧,让人在得到后陷入更深的空虚。 智者明白,真正的洁净不在于拒绝欲望,而在于理解欲望背后的真相:我们渴望的从来不是金钱或肉欲本身,而是它们所代表的自由、认同与生命力的彰显。 庄子说:"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 "男人的最爱",实际上是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 我们对金钱与情欲的执着,往往源于内心的匮乏与恐惧,害怕贫穷,害怕孤独,害怕不被认可,害怕生命虚无。 其实,所有外在的追逐,最终都是与自我的对话。当我们能够直面内心的深渊,外在的诱惑自然会失去掌控我们的力量。 歌德在《浮士德》中写道:"有两个灵魂居住在我心胸,一个要同另一个分离。" 真正的解脱不是否定欲望,而是通过认识欲望的本质,将其升华为创造的动力。 真正的自由,来自于认清欲望的本质,而后超越它。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是对欲望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欲望中保持清醒的能力。 就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欲望可以是堕落的深渊,也可以是升华的阶梯,区别只在于我们是否拥有驾驭它的智慧。 愿我们都能在认识欲望的过程中认识自己,在超越欲望的过程中成就自己。这或许就是李敖这句惊世之言,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那些我们明知不洁却依然无法抗拒的诱惑。



![果然自作多情是最伤人的[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2134059969775708882.jpg?id=0)

![你以为你错过了一段姻缘,殊不知是躲过了一劫[吃瓜]](http://image.uczzd.cn/17146512476488251528.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