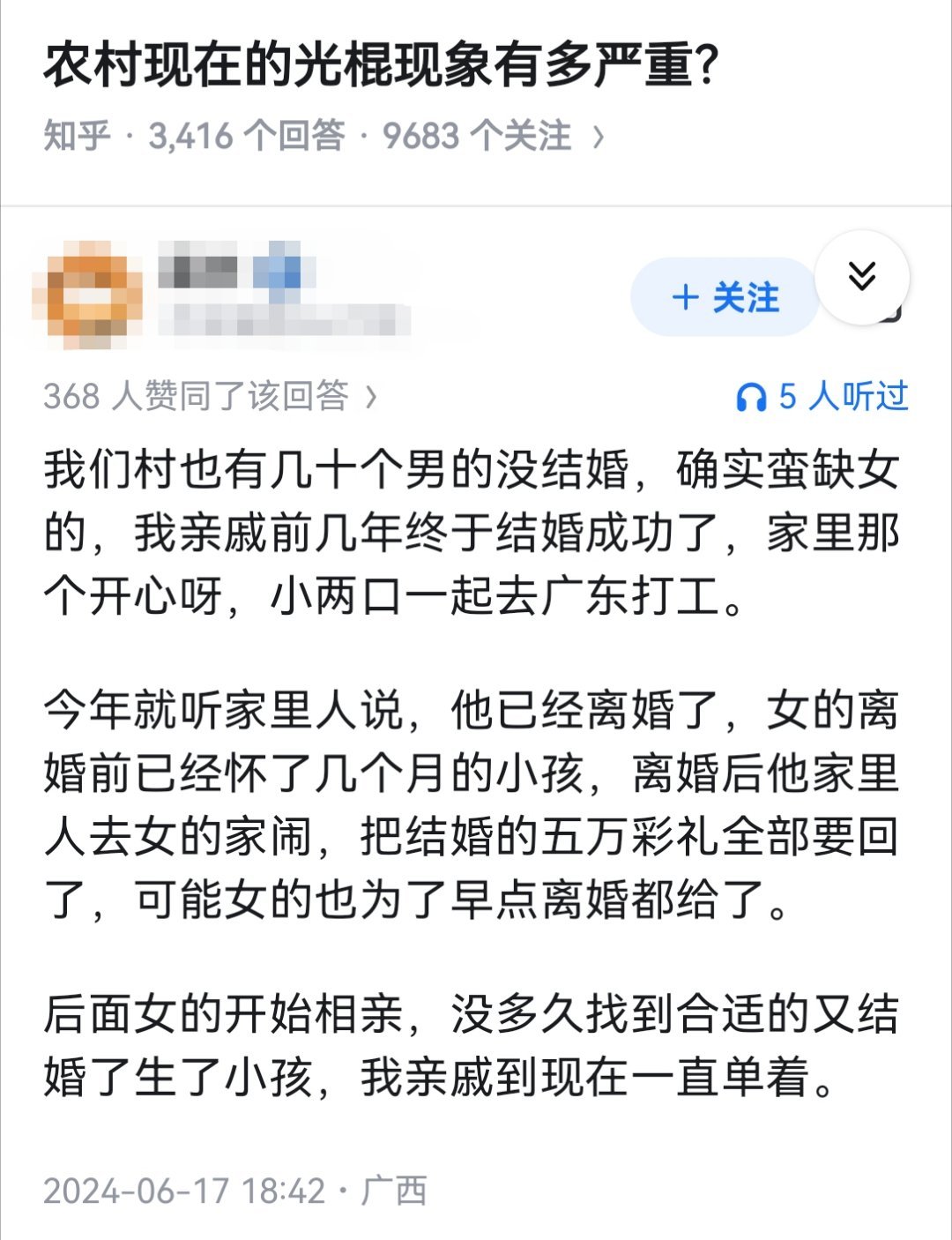我丈夫出身农村,我公公在一个公社当书记十多年,当我丈夫上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我公公已经是县政府的农委主任,下面联系好几个农业相关口的局,曾经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他们县里,也是一个很有知名度的人。虽然如此,我丈夫家除了公公是城镇户口外,家里其他人都是纯农村户口,住在乡下。我丈夫的两个哥哥,都依靠自己努力,摆脱了农民身份,到外地站稳了脚跟。按照公公的意思,两个儿子都已经不在身边,就想让我丈夫接替他顶班,不要考大学了,将来身边好有个照应。可是,我丈夫当时年轻,不懂老人意思,执意要考大学。 我公公这辈子,在我们县也算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从公社书记到县政府农委主任,干了十多年,手底下管着好几个农业口的局,还去过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可老家的户口本上,除了他那页盖着“城镇户口”的红章,我们婆家人,包括我丈夫,都是实打实的农村户口。 两个大伯哥早就靠自己闯了出去,一个在南方开工厂,一个在省城当老师,过年才难得回趟乡下。 老家堂屋的土坯墙上,还贴着他当年参加会议的黑白照片,相框边角磨得发亮,照片里的人穿着中山装,胸前别着钢笔,眼神里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笃定。 我丈夫上高中那年,正赶上要考大学,公公突然把他叫到煤油灯底下。 “别考了,”公公吧嗒着旱烟,烟圈在灯光里打了个转,“我这位置,过两年你顶班,县里上班,离家近。” 他以为小儿子会懂——两个大儿子像风筝一样飘远了,线攥在手里都快没了温度,他想留个能天天看见的人,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在灶房里递双筷子。 我丈夫当时十七岁,心里揣着大学梦,满脑子都是书本里的“外面世界”。 他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红薯稀饭,米粒粘在碗边,半天没抬头:“爸,我想考大学。” 公公的烟杆“咚”地磕在桌角,烟灰撒了一桌子:“大学毕业又能怎样?我这农委主任,多少人盯着!” “可我想自己考。”他声音不大,却像块石头,沉在煤油灯的光晕里。 那时候他哪懂啊? 只看见“顶班”两个字像道墙,挡住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光;却没看见父亲捻灭烟头时,指节捏得发白——两个哥哥寄来的奖状贴满了东墙,可空荡荡的老院里,风穿过屋檐的声音,比奖状上的金字还亮。 后来我问他,后悔过吗? 他说不后悔考大学,但后悔那天没抬头看看父亲的眼睛。 老人一辈子要强,从不说“我怕孤单”,只会把牵挂裹进“顶班”“稳定”的壳里,像把核桃塞进孩子口袋,以为那是最好的干粮。 他到底还是考上了大学,走的那天,公公没去送,只让我婆婆塞给他一沓皱巴巴的零钱,里面有毛票,有角币,还有张崭新的十元纸币。 车开的时候,他从后窗看见父亲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背比照片里驼了些,风把他的衣角吹得飘起来,像面没人收的旗。 现在我们也有了孩子,每次送孩子去外地上学,他总要站在校门口多看会儿,直到看不见人影才转身。 我知道,他是想起当年那个煤油灯底下的夜晚了——原来长辈的“安排”,从来不是要捆住你的翅膀,是怕你飞远了,忘了回家的路。 前阵子回老家,堂屋的灯换成了节能灯,亮堂堂的,照得墙上的照片更清晰了。 他站在照片前看了很久,突然说:“爸那时候,是不是也在这灯光下,想了一夜两个哥哥在外地的日子?” 我没说话,只是觉得,这屋里的光,和当年的煤油灯一样,都照着些说不出口的牵挂,在岁月里慢慢温成了暖。
我丈夫出身农村,我公公在一个公社当书记十多年,当我丈夫上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我公
张郃高级
2025-12-09 17:19:05
0
阅读: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