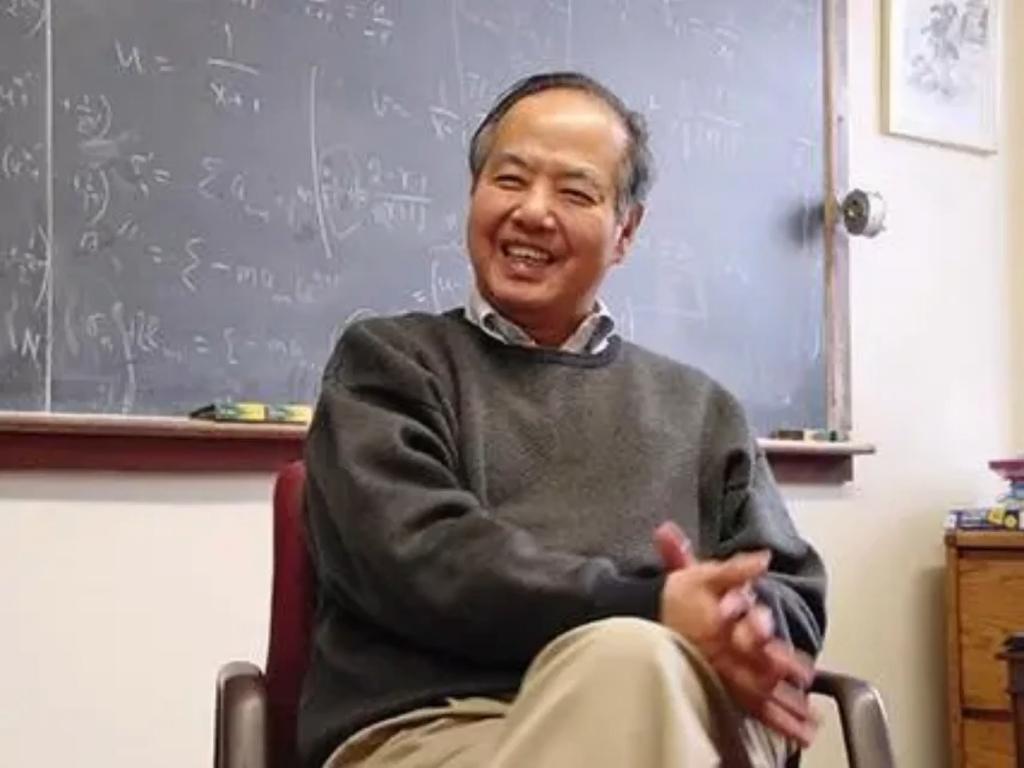1946年,老师突然问到:“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脱口而道:“我从书上看过,大概1000万度。”费米听完批评他:“你这样是不行的!” 这句话落进了李政道的心里。那一刻开始,李政道意识到,科学不靠背诵,科学要靠推到最后一步的计算。 费米没有马上放下这个问题。为了让年轻的李政道明白“自己算”的意义,费米把整整一周的时间都压出来,和李政道一起制作了一把长长的计算尺。 他们站在芝加哥大学昏暗的办公室里,一段一段地推公式,刻度反复核对。几天后得出的数字仍然是那本书上的1000万度,这个结果让李政道脸红,却又让他在心里生出一种重生般的踏实。 这一段经历在1956年忽然找到了去处。那一年,杨振宁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李政道连续讨论弱相互作用的难题。 那段日子里两人几乎每天都在对比实验数据,翻阅历史论文,找问题里的漏洞。弱相互作用的混乱让许多物理学家头疼,但李政道越研究越觉得,旧概念里的“宇称守恒”根本没有人真正验证。 他把当年费米那番话再次记起,反复算衰变可能的结果。杨振宁更敏捷一些,两人合在一起,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缝里,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的想法。 发表论文那天,李政道很平静,却也隐隐觉得物理学界会被推上一条新的路。 果然,1957年吴健雄在美国国家标准局做出的钴‑60 实验直接验证了宇称不守恒。世界各大实验室的记录像雪片一样传来。瑞典皇家科学院那一年的评审里赫然写着:这项理论改变了现代物理的结构。 颁奖台上,31岁的李政道站得很直,他心里想起的不是荣誉,而是那个被费米批评的春天。 这些成就并没有让李政道远离故土。1972年他第一次回到中国,看见科学教育的现状心头发紧。实验室设备老旧,人才断层明显,年轻学子渴望上升却缺乏平台。 他在北京访问期间,提出要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才培养体系。 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成立。李政道参与方案讨论,希望把天赋特别突出的少年送上科学道路。 再往后,恢复高考带来了大学生,但培养博士生的通道不顺,他又提出一个更大的计划,培养能与世界对话的物理学群体。 于是1979年,CUSPEA计划启动。每一名报名的中国学生都要经历严格考试,再由美国教授匿名审卷。那几年李政道常常自己掏钱寄材料,忙得连家里人都不清楚他到底在推广什么。 这个项目坚持了十年,送出915名学生,其中后来成为院士、科学机构负责人、国际大奖获得者的多达数百人。 随着国内博士教育逐渐恢复,科研体系仍缺独立成长的空间。李政道在1980年代数度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也多次向国务院建议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84年博士后制度正式实施,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中国科研生态开始稳定成形。这些制度后来成为无数青年学者能够独立做研究的起点。 晚年的李政道从纽约搬到旧金山,身边陪着儿孙。他经常拿着旧笔记本翻看几十年前的推导,也爱画草木和海边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