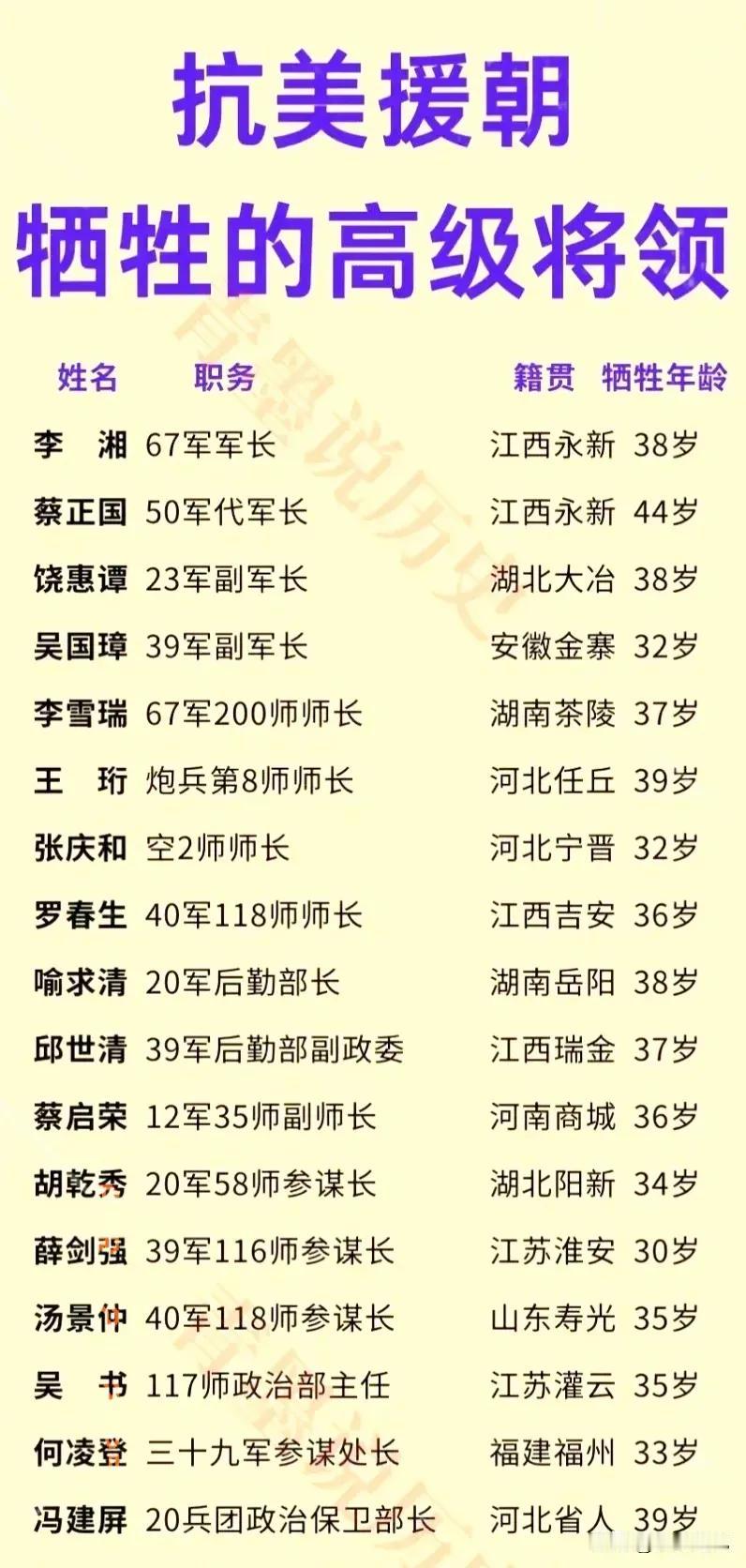三十多年前,老山前线,出发前夕,老虎山主攻连连长韦桂黔,正襟危坐,腰缠万弹,他削发明志,以死报国。 一到下雨天,韦桂黔的腿就开始疼,不是那种一下子要命的疼,而是闷着、涨着,像有什么东西在骨头缝里慢慢拧。 夜里翻身的时候最明显,稍微一动,膝盖就跟被人点了一下似的,他自己心里清楚,里面还有东西没取干净。 医生早就跟他说过,现在条件不一样了,手术风险不大,把弹片清出来,人会轻松很多,可他说什么也不肯去。 别人劝急了,他就笑笑,说老了,懒得折腾,其实他心里有本账,这点疼和当年比,根本算不上什么,那些年从身上取出来的弹片不止这一块,真正让他难受的,也从来不是疼。 这块留在身体里的,是1984年老山留下的,后来很多人通过电影、纪录片去看那场战争,总觉得有冲锋、有口号,有一股子热血。 但真正待过猫耳洞的人都知道,那地方低矮、潮湿,伸不开腿,空气里混着土味、汗味和火药味,人常年弯着腰,说话都不敢大声,谈不上什么浪漫,更多时候是紧张和疲惫。 那次大战前一天晚上,韦桂黔在洞里摸出一块破镜子,用小刀把头发剃了,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仪式,就是觉得这样干脆。 头发剃下来,他用纸包好,贴身放着,想法很简单:要是真回不来,总得留点能认人的东西。 当时他是连长,身上的装备比别人多,弹链一圈一圈缠在腰上,手榴弹挂在胸前,走一步都沉。 新兵吴冬梅守在洞里,他把随身的手枪子弹递过去,让他留着,不是不怕死,而是太清楚位置在哪,他要在最前头顶着,用不上手枪。 仗一打起来,脑子根本来不及想别的,越军从山脊线上冲下来,照明弹把整片高地照得发白,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 苗廷荣中弹后,血顺着脸往下流;吴冬梅刚探头,就被爆炸掀起的碎石埋住,那时候没人有时间喊,能喘口气就不错。 韦桂黔自己也中弹了,左眼被打中,眼球直接被震出来,挂在眼眶外面,他下意识伸手按了回去,用纱布随便缠了几圈。 血还是往外渗,但他没管,他抬头看了一眼洞外的动静,抓起步话机,报了577阵地的坐标。 他心里很清楚,坐标一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炮火覆盖下来,洞里洞外的人,谁都跑不了,话筒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炮弹就落下来了,爆炸离洞口很近,敌人被炸散,他整个人扑在苗廷荣身上,用后背挡了一下。 后来支援部队清理战场时,把他从碎石和血泥里抠出来,他几乎没意识了,现场只剩一副担架,他还抬了抬手,指着苗廷荣,意思是先抬战友,那不是多伟大的念头,就是本能。 仗打完了,老山慢慢安静下来,可他心里那根弦一直没松过,这些年,他家墙上一直挂着牺牲战友的名字。 他记得谁是哪一年走的,谁家里还有老人,水壶、压缩饼干、战友留下的东西,都被他放在一个铁皮盒子里,他说那是欠下的,一顿饭,一辈子也还不清。 后来有了孙子,孩子要是打架、逞能,他就带着去纪念馆,在照片墙前站一会儿,不说教,只说一句:当年我们拼命,是为了让身边的人活,不是为了争谁厉害。 去社区讲经历,有人问他断粮的时候怎么熬,他不多说,只把那枚取出来的弹壳放在桌上,轻轻一声响,很多话就够了。 韦桂黔总说自己是运气好,活下来的;那些没回来的,是命,他觉得自己这辈子要做的事,就是替他们把日子过好一点。 老山现在早就看不出当年的样子了,树长高了,草也密了,可每到阴雨天,腿一疼,他就知道,那些人、那些事,从来没真正离开过,他不是不往前走,只是有些东西,一旦刻进骨头里,就带一辈子。 参考:谷中欢悦赏彩虹:三十多年前,老山前线,出发前夕——个人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