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根本就不想造反,其实是关陇集团对中央集团不满,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官军。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在范阳起兵,表面上是他个人意图,背后却牵扯河北门阀势力与关中贵族的长期对立。 要说明白这事儿,得从几十年前说起。唐朝刚建立那会儿,天下的权柄基本攥在关陇贵族手里。这些人家世显赫,祖上不是跟着李渊打天下的将军,就是关中本地的世家大族,朝堂上的大官、军里的将领,十有八九都跟他们沾亲带故。他们看河北这边,总觉得是“偏远地方”,就算河北的州县比关中富,在他们眼里也只是“纳税的来源”。 河北这边呢,早就憋着股气。从隋朝开始,河北就是大运河的枢纽,沧州的盐、冀州的粮、幽州的战马,哪样不是朝廷的命脉?当地的门阀也不含糊,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这些家族传了几百年,家里的子弟读书的、经商的、领兵的,各行各业都有头有脸。可到了长安,关陇贵族见了他们,要么鼻孔朝天,要么就拿“地方人”的名头挤兑。 就说税收吧,天宝年间,关中贵族把持的户部总说河北“富庶”,摊派的赋税一年比一年重。河北的粮商们运一批粮食去长安,路上被关卡盘剥好几次,到了地方还得给管事的官爷塞红包,不然连仓库门都进不去。有回范阳的刺史想给朝廷上书,说本地百姓快扛不住了,结果奏折刚到长安,就被宰相李林甫(关陇出身)压了下来,还回了句:“河北刁民,不压着点要翻天。”这话传到河北,那些门阀老爷们气得把茶杯都摔了。 安禄山能在范阳站稳脚跟,靠的就是河北门阀的支持。他是个胡人,早年在边境做生意,跟河北的商帮混得熟。后来当了节度使,手里有兵权,河北的大族们就觉得“这人能用”——他不是关陇那边的人,跟长安的贵族没交情,又能打仗,正好替他们出头。 有回长安派来个御史巡查,到了范阳就摆架子,指着安禄山的鼻子骂他“胡人不懂规矩”,还说要查他的军饷账目。当晚,范阳最大的盐商就找安禄山,塞了个账本给他:“大人看看,这是长安那边三年来从咱们盐场多拿的好处,够养三个营的兵了。”安禄山第二天就把账本摔在御史面前,那御史灰溜溜地回了长安,再也没敢来。 河北的门阀们不光给钱给粮,还把自家子弟送到安禄山的军队里。博陵崔家的二公子,文能写诗,武能骑马,放着长安的官不当,非要来范阳当偏将,说“在长安看关陇人的脸色,不如在这边护着家乡百姓”。这些人聚在一块儿,天天说长安的不是,说关陇贵族把朝廷当成了自家的私产,早就忘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所以天宝十四载那回,安禄山在范阳城头竖起“清君侧”的大旗,底下响应的不光是他的兵。沧州的盐工们自发组织起来,把运盐的船改成了运兵船;冀州的粮商打开粮仓,让士兵们随便搬;连那些平时只读圣贤书的老先生,都带着学生去军营里帮忙写檄文。他们嘴里喊的不是“反唐”,是“让长安的人看看,河北不是好欺负的”。 关陇集团那边呢,也觉得自己占着理。他们说安禄山是“胡人乱政”,说河北门阀是“地方割据”,调集了关中的军队,喊着“保卫朝廷”的口号杀过来。两边的兵卒在战场上相遇,互相骂对方是“反贼”,可仔细问问,河北的兵家里可能有亲戚在长安做买卖,关中的兵或许祖上就是从河北迁过去的。 打了两年仗,洛阳城被烧得不成样子,黄河边的农田全荒了,到处都是逃难的百姓。有个从范阳逃到长安的老妇人,见了长安的士兵就哭:“我儿子在安禄山的军队里,我女婿在你们这边,他们为啥要互相杀啊?” 后来安禄山死了,仗还接着打,打到最后,河北和关中都打空了。有回清河崔家的老爷子站在自家被烧毁的祠堂前,看着满地的瓦砾叹气道:“原想争口气,没想到把家都争没了。”长安城里,当年不可一世的关陇贵族,也有不少因为没钱养兵,把祖宅都卖了。 其实说到底,河北门阀想的是“自家的利益不能被欺负”,关陇贵族想的是“朝廷的规矩不能被破坏”,可他们都忘了,不管是河北还是关中,都是大唐的土地;不管是盐工还是士兵,都是大唐的百姓。争来斗去,最后受苦的还是那些只想安稳过日子的人。 直到多年后,有个路过洛阳的书生,在断壁残垣上题了首诗:“河北关中本一家,何苦刀兵乱如麻?若知百姓流离苦,当初莫要争高下。” 据《旧唐书·安禄山传》及《资治通鉴·唐纪》综合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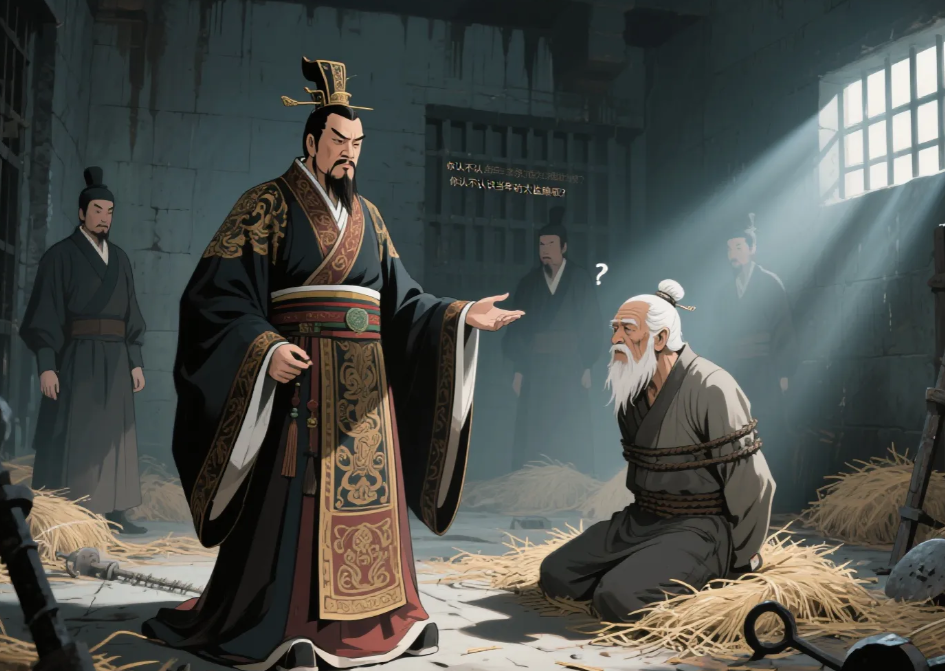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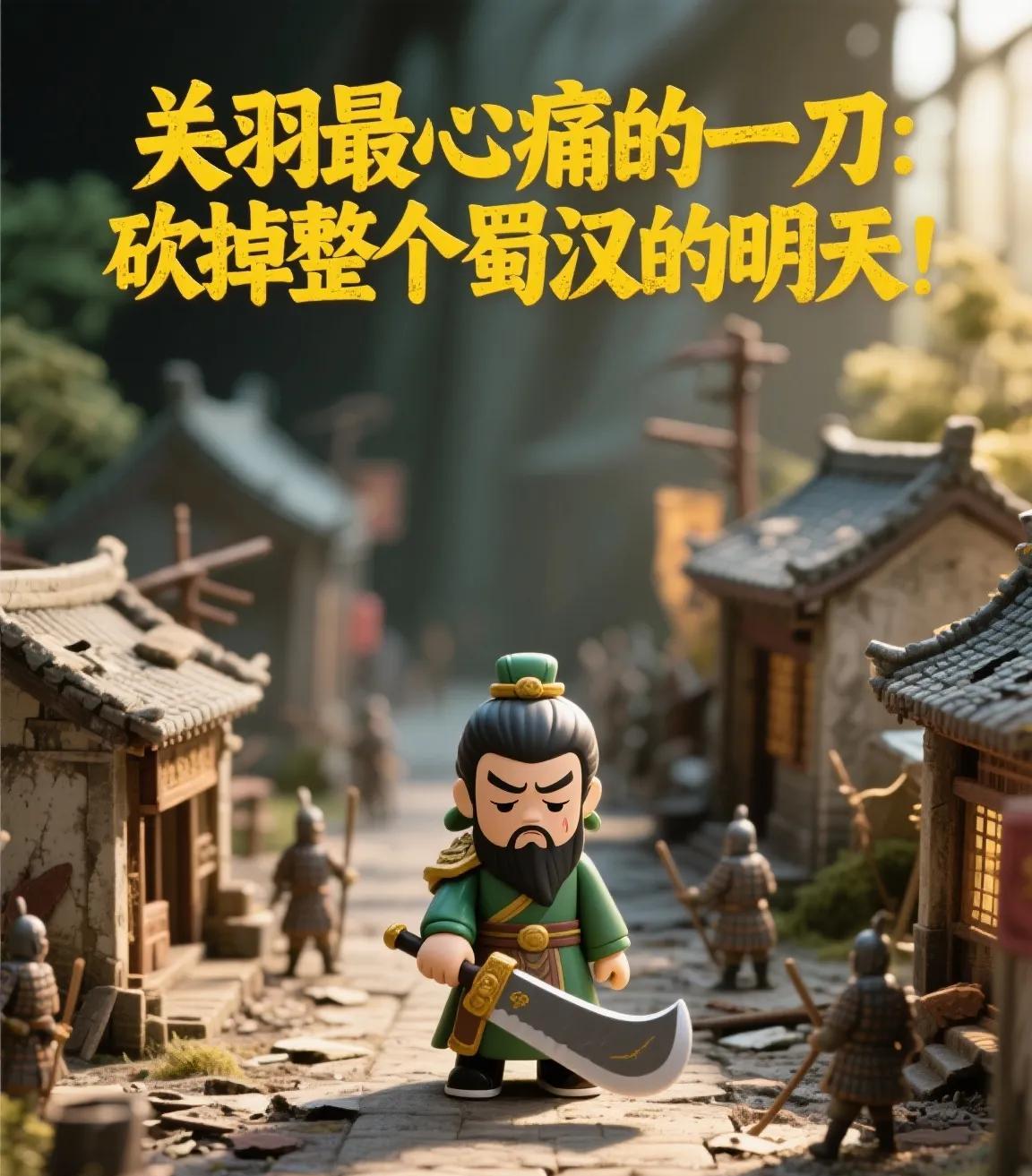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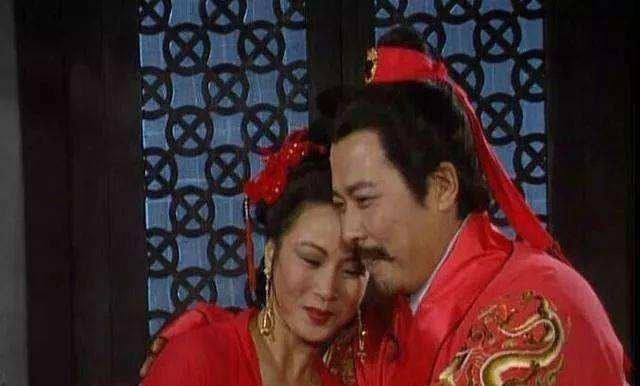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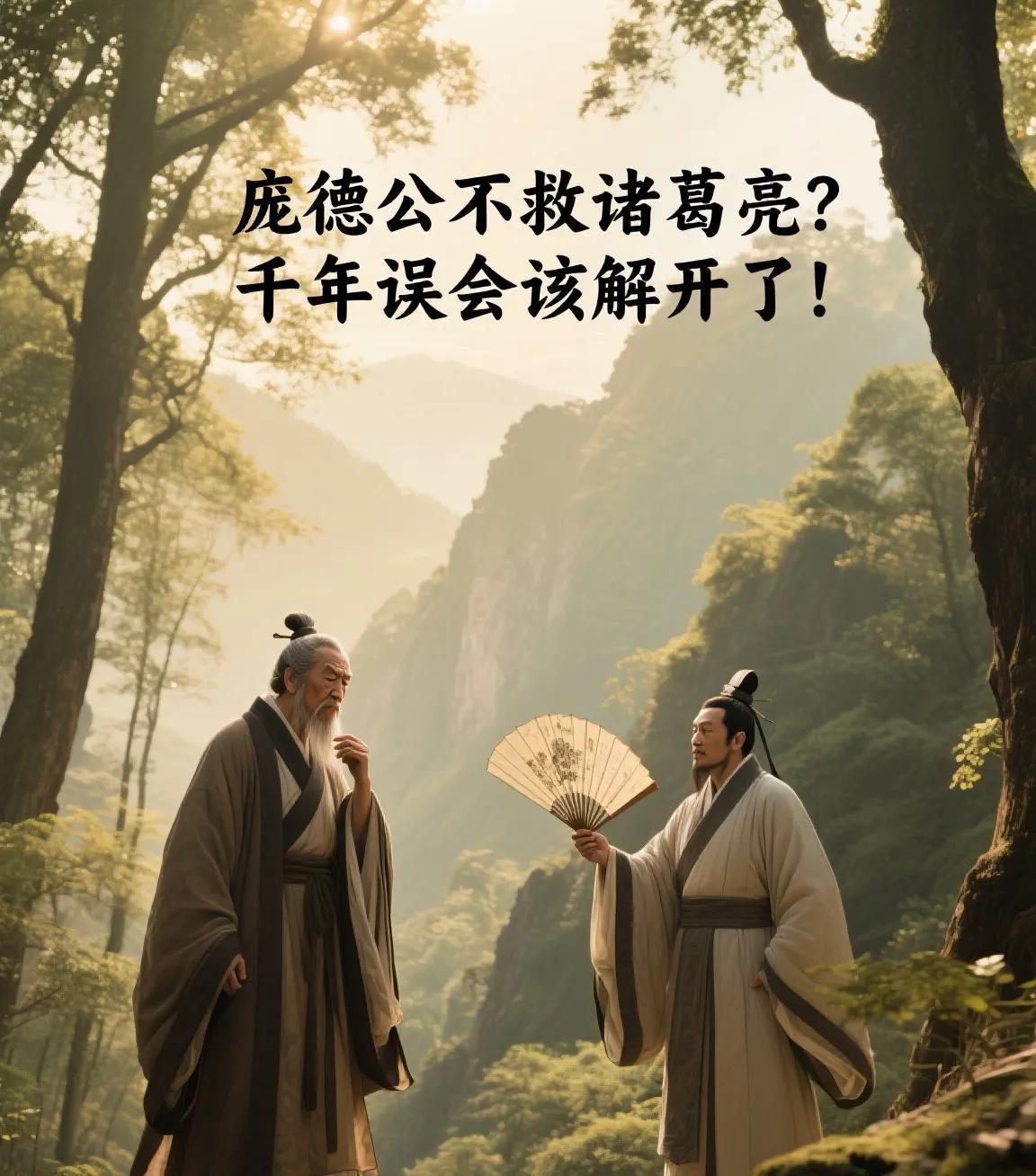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