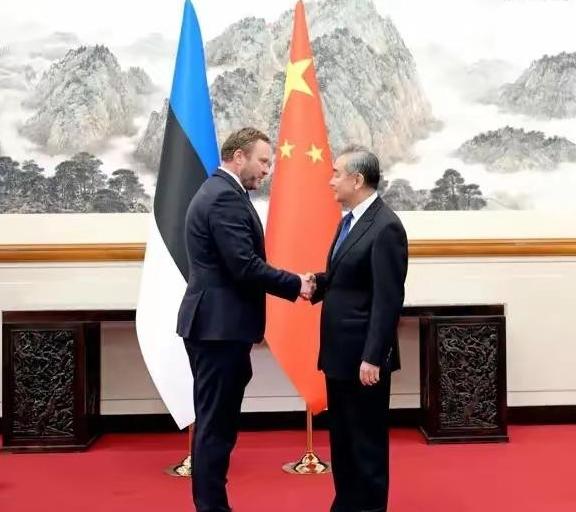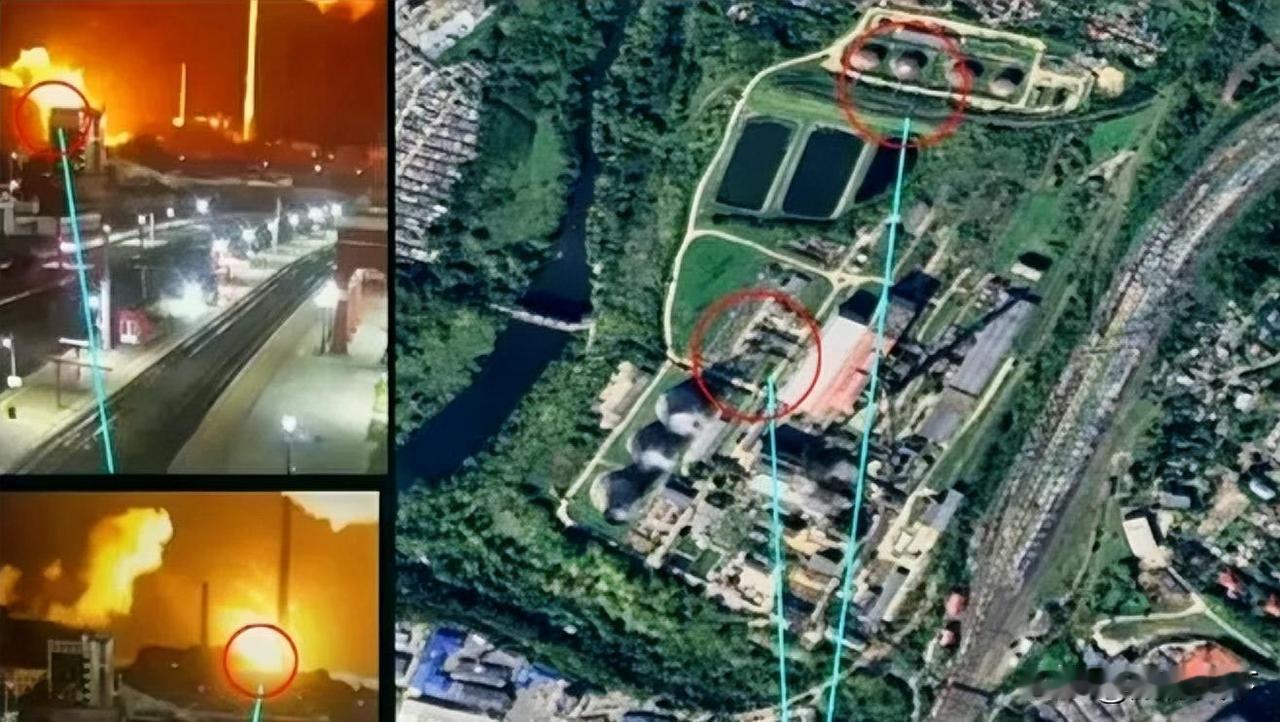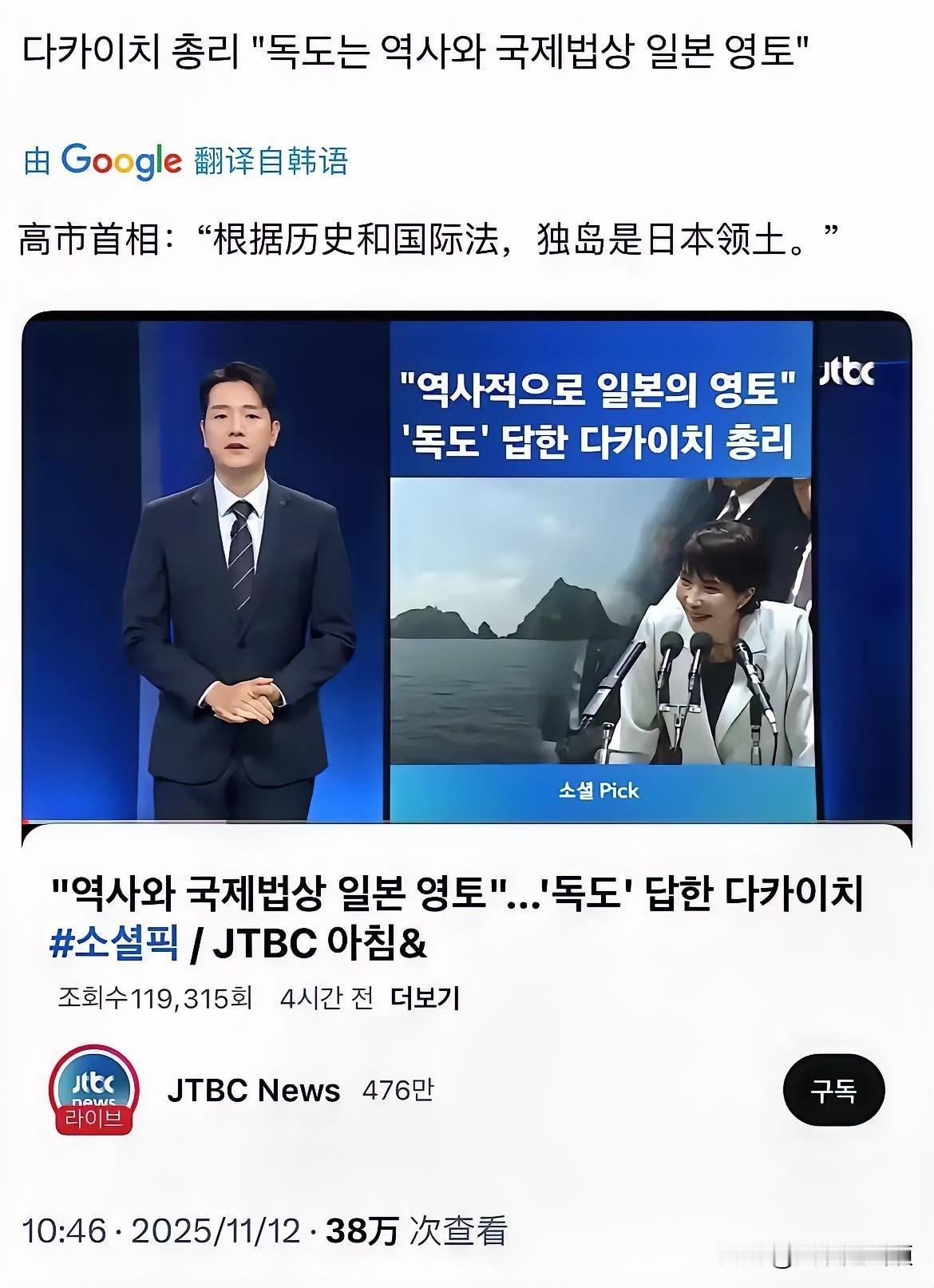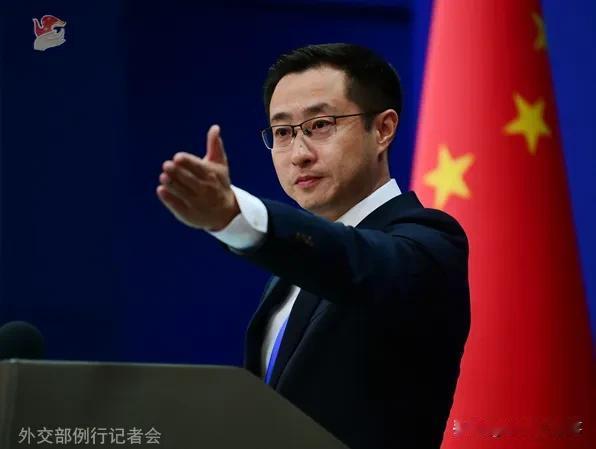美国华人表示:在美国所有华人精英,不管你第一代有多牛,是顶尖科学家还是大学教授,不出两代,你的孩子大概率会变回一个普普通通的中产,一个打工仔,这究竟是为什么?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美国的华人圈子里,常常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管你第一代有多牛,不出两代,孩子就会回归普通中产。” 这听起来像是一句玩笑话,可事实上,许多在美国奋斗几十年的华人家庭,回头一看,发现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精英光环”,到了孩子那一代,真的逐渐褪色了。 那些当年凭借一纸博士学位闯荡美国的精英,如今的孩子们,很多并没有继承父母的“学霸基因”,也没有再冲进硅谷、华尔街或者科研机构,而是选择了更轻松、普通的职业,成了美国社会中最典型的一类人——稳定、体面、但不再耀眼的中产阶层。 这事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起。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看到了“走出去”的机会。对很多人来说,美国几乎就是梦想的终点。 那时能出国的,多半是北大、清华、中科院的高材生,他们背着厚厚的资料和有限的积蓄,漂洋过海,去往一个陌生的国度。 有人在密歇根大学的实验室熬夜,有人在加州的车库里改程序,也有人在硅谷的小公司里拼到天亮。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华人精英,可以说是靠“实力”和“勤奋”在夹缝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根据当时的统计,那一代赴美留学定居的华人中,超过八成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一半以上从事STEM行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他们是典型的“技术移民”,用专业和耐力赢得立足之地。 很多人工作二十年,从工程师做到项目经理,买下了郊区的大房子,孩子读上了名校。第一代华人的成功,靠的是一股不服输的劲,一种“只要肯干就能出头”的信念。 然而,当他们的孩子——也就是第二代华人——长大成人后,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2000年后成长起来的华人二代,选择进入STEM领域的比例,比父母那一代下降了将近20%。 他们中更多人转向了教育、艺术、心理学、社区服务等领域。相比起父辈在实验室里熬夜、敲代码、做数据分析,二代华人更倾向于寻找“生活平衡”的职业。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努力,而是价值观变了。很多华人家长希望孩子能延续他们的奋斗路径,可在美国社会里长大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是另一套教育。他们被教导要“follow your passion(追随你的热情)”,要活出自我、要平衡生活,而不是“拼命考第一”。 在父母眼里,这种想法太理想化,太不接地气;可在孩子看来,父母那种“拼命三郎式”的人生,也未必值得。于是,代际间的理念差距,慢慢拉开了。 更现实的问题是,即便那些选择了跟父辈一样道路的孩子,也很难再复制父母的辉煌。硅谷的数据令人无奈:华人在工程师中占27%,但在高管层中却不到5%。 这意味着,哪怕华人是公司里最能干的那群人,他们依旧止步于“中层”。很多华人工程师在岗位上干了二十年,项目一个接一个地做,业绩年年都有,可到升职的时候,却总是听到那句熟悉的理由——“领导力不足”。 所谓“领导力不足”,往往是一种模糊的拒绝方式。白人同事或许更擅长在会议上表达自信,更懂得如何“包装自己”,而华人习惯用行动证明能力,却忽略了美国企业文化中“社交”和“话术”的重要性。 于是,当升职的机会出现时,那些能“说”的人更容易被看到,而那些默默干活的人,却被定格在“执行者”的位置上。 这种“玻璃天花板”,成了很多华人家庭无声的痛。第一代人习惯埋头干活,社交圈局限在实验室、公司和社区。他们的生活稳定但封闭,语言障碍、文化隔阂,让他们与美国主流社会的联系始终有限。而这种局限,往往也影响到下一代。 孩子们虽然语言流利,却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圈里——周末补中文、暑假回国探亲、社交对象几乎清一色是华人孩子。等他们长大后,发现自己虽是美国公民,却既不完全融入白人社会,也不太了解美国的政治与主流文化。 更值得关注的是,华人群体内部的贫富差距,正在加速扩大。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收入最高的10%华人家庭,其收入是最低10%的19.2倍。有人在硅谷做高薪工程师,有人却在唐人街开餐馆、送外卖、打零工。 华人社会表面看似富裕,其实分化严重。而且,财富很难形成稳定的代际传递。许多第一代人辛苦一辈子积累下来的财富,要么用来供孩子上学,要么投入房地产,但孩子长大后往往选择了轻松工作,不愿承担父母那样的奋斗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