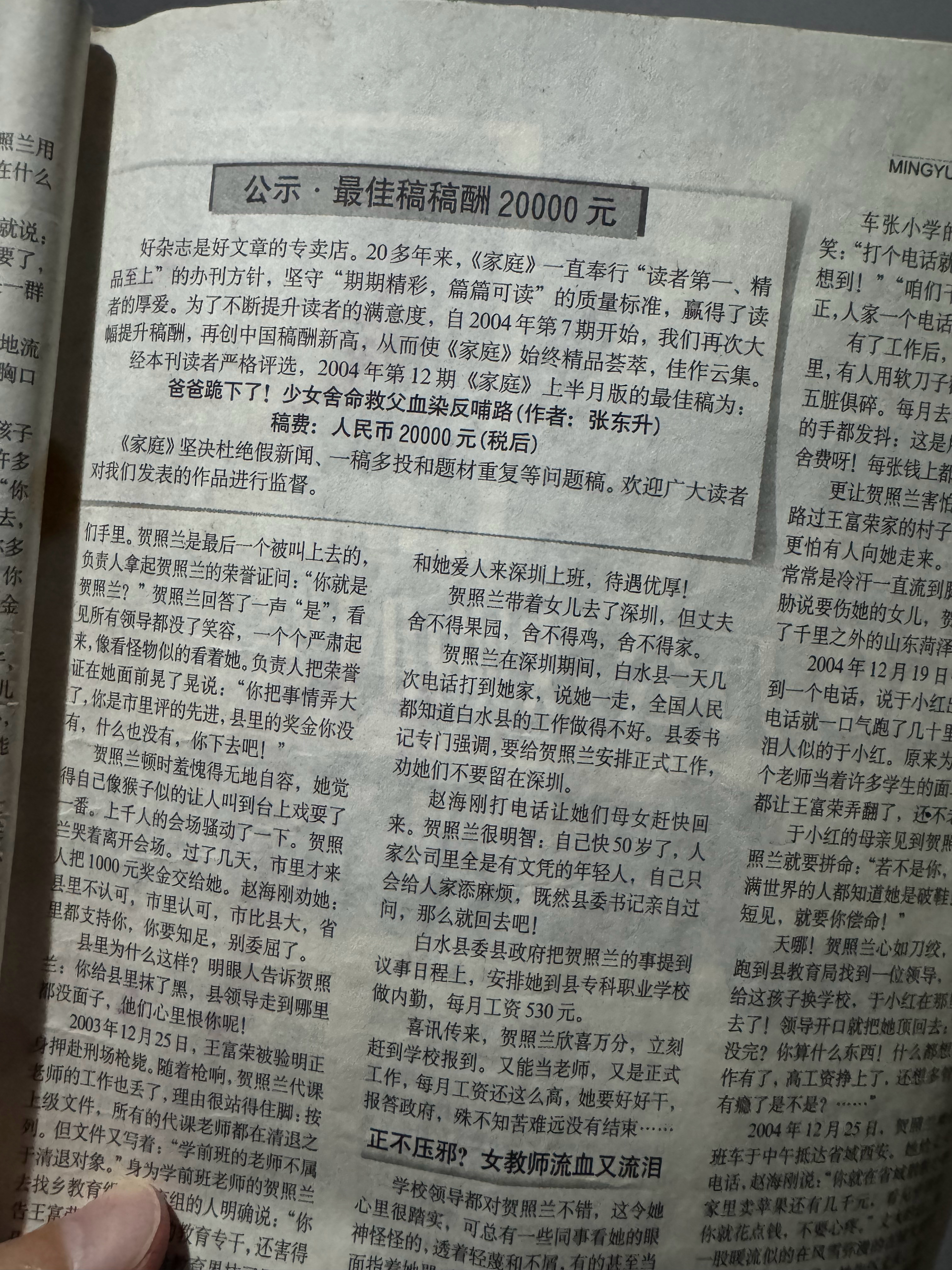母亲
县城的夜黑的早。
我在姐夫家跟大姐还有外甥喝酒,喝完酒聊天,母亲打电话催我。我回来后,父亲已睡下,母亲开着电视等我。她催我睡觉,自己也去卧室。我关客厅的灯,回卧室。睡不着,嘴里有点干,不想喝白开水,想着起来买水喝,客厅里没找到钥匙,就去推母亲卧室的门。
母亲竟然也没睡,躺在床上看大姐拿给她的妇女生活等杂志,当年是很火的,一篇稿费有的可达两万。我不忍心要钥匙,直接躺在母亲的床上,握着母亲的手,跟母亲说话。
她说,你大姐送我的这些杂志,解决了我睡不着的问题——这几天连续下雨,她没去体委打牌,于是就在家无聊的睡觉,白天睡多了,晚上睡不着,就看杂志打发时光。
母亲大约是小学毕业,或者上了初中。她母亲死的早,她有几个哥哥,我姥爷也在,但是那种缺少母爱的人。她后来说,她不想她母亲了,因为17岁没有了母亲,她眼泪早就哭干了。那是她提到我父亲经常提到我奶奶然后伤感的事儿。我奶奶更苦,我姑和我父亲他们几岁的时候我爷爷就去世了,是我奶奶把他们拉扯大的。相比之下,我母亲的命运,还稍好一些。
我躺在母亲的身边,握着她枯瘦如柴的手。我就忍不住泛泪,忍不住眨眼。
我母亲说,你天天熬夜,天天忙的顾不上吃饭,那次我打电话九点了你还没有吃饭,你早点睡去吧。
其实,那时才刚刚十点。
县城的夜黑的早。
我没有说话,我就是握着母亲的手,枯瘦如柴的手。母亲说,你看黑的,我经常去体委打牌晒黑的。是的,母亲几乎每天去体委打牌。每次我打电话,那边热热闹闹,她说,有事没,没事回去再说,正打牌呢。其实回去也没说,她耳朵不好,每次打电话基本上说不到一块儿的,大都是草草结束。
此时,我躺在她身边,犹如儿时我躺在她的身边,那时候还有她的奶香。
我写这些的时候,忍不住流泪。
母亲说,你不要每次回来买东西了。家里东西,你哥你姐买的根本吃不完,还有西瓜。
这时候已经是秋季了,我刚在卧室里看到一个西瓜,一头有些腐烂,正想怎么处理掉。母亲仿佛有感应一样,说,那个西瓜,你可不要扔,你扔了你大会心疼的——我们叫父亲为大。我每次回来,有一个任务,就是悄悄的处理掉放坏掉的东西,她大约是知道的。
我说,那是坏的,哪怕削去,也是不行的。
她说,你知道过去吗?当时为了迎接上级检查,坏掉的红薯都被人故意的制造事故用红薯窖埋下。可过了很长时间,人饿的没办法,又把这些红薯扒出来,上面长满了白毛,跟老鼠似的,但洗了洗,放到面里,做成馒头,都吃了,我跟你大也吃了,不是活到七八十,也没事吧?
我无言以对。
她肯定和父亲共同回忆过这些,然后打心里默默的驳斥他们的那个义正辞严的儿子。他们老了,他们的儿子大了,他们不敢说儿子了,只能默默的听,但内心里还在坚持,是的,他们一定还在坚持,因为他们吃过,苦过,证明过。
我沉默不语,我还能说什么!
我抚摸着她的手,黑黝黝的是色,软绵绵的是皮,硬邦邦的是骨,还有暗红色隆起的一根根的筋。我握着她的手,不敢看她的脸,我怕她看到我落泪,不看我也知道,那张脸,黑黝黝的,眼窝深陷,眼睛浑浊,面骨隆起,两边塌陷,皮肤是暗红的,头发是发白的,那是一张一年比一年苍老的脸,我不敢看,但在我心里。
我握着母亲的手,枯瘦如柴的手。
母亲说,你睡觉去吧。
我想起来跟母亲要钥匙,她颤巍巍的起来,下床,又到了客厅沙发上,把绑在一个布袋的带子上的钥匙,要解给我。我说不用解,我把母亲送到卧室里,抓着那个布袋,下去买苏打水喝。
我抓着那个母亲常常带着它去体委打牌的布袋,到了冷冷清清的大街上,买了水,喝一口,甜甜的……
县城的夜黑的早。人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