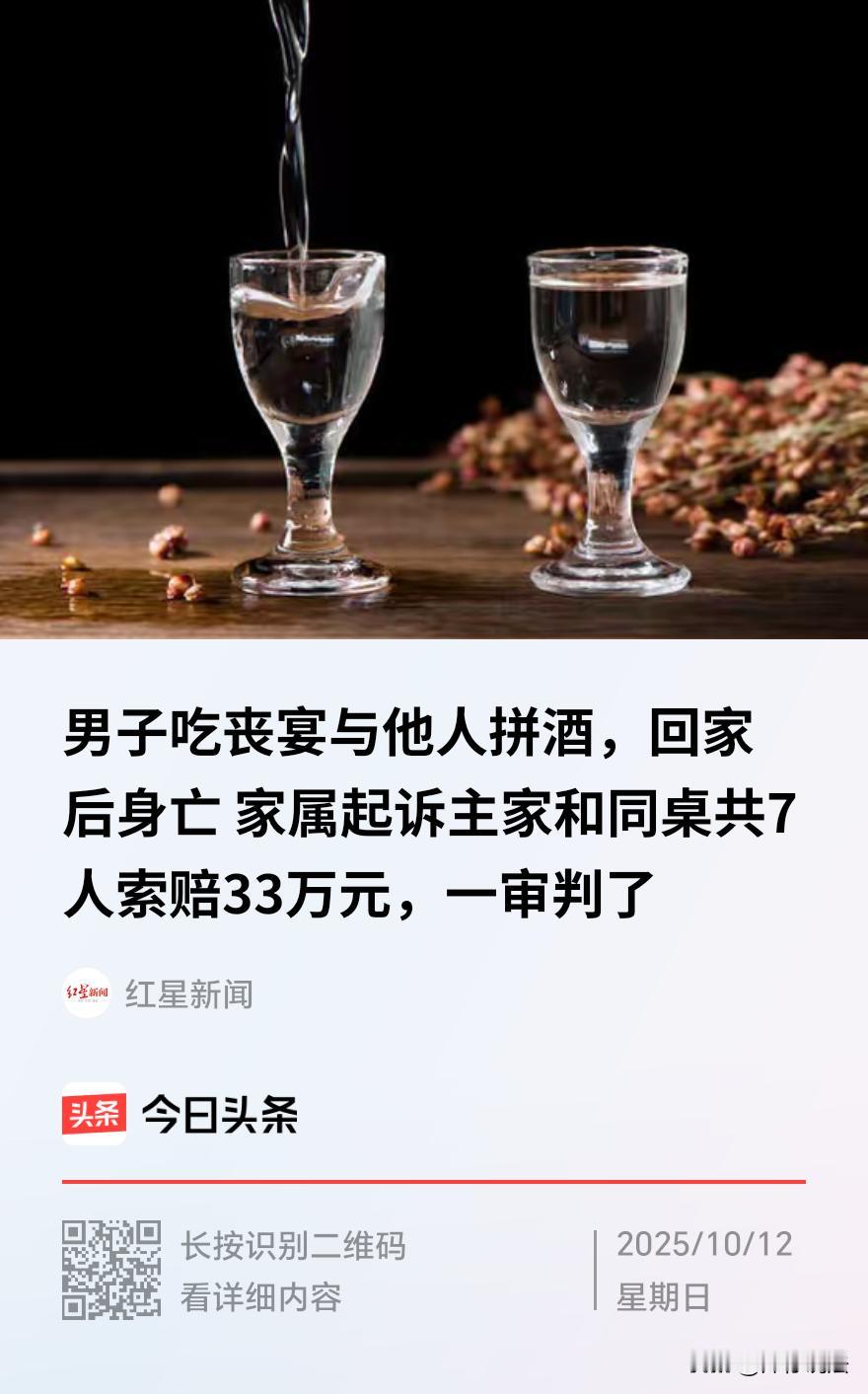云南鹤庆,一男子参加远亲家里操办的丧宴,几杯白酒下肚后,与同村汉子较上了劲。不料,汉子挑衅道:“敢不敢用碗喝?”男子拍桌而起:“谁怕谁!”接着,两人你一碗我一碗地拼起酒来,席间争吵声越来越大,却无人上前制止。很快,男子喝的烂醉,在旁人不注意的情况下,独自踉跄着离开了。次日,家人回家时惊见男子俯卧在院门内的水缸旁,身体冰凉僵硬。尸检结果显示,男子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严重超标,足以致命。事后,男子的家属一纸诉状将宴席主家及同桌七人告上法庭,索赔33万余元。 据红星新闻10月10日报道,2025年5月初,某村村民母某甲(化名)的母亲不幸去世,在家中为母亲办理了丧事仪式,并计划在5月5日晚上以自助餐形式招待前来吊唁的亲友。 母某甲认为这只是个简单的聚会,让大家在悲伤中互相安慰,谁也没料到会酿成后来的悲剧。 杨某(化名)是母某甲的远房亲戚,偶尔回村,他性格外向,喜欢喝酒,村里人都知道他酒量不错,但有时会喝过头。 5月5日下午,杨某接到消息后,特意赶回村里参加丧宴,他到达母某甲家时,已是傍晚17点30分左右。 丧宴进行到一半时,杨某遇到了同村的母某乙(化名),平时关系不错,但两人都爱喝酒,有时会较劲。 这天,母某乙见杨某喝得正酣,便半开玩笑地说:“老杨,今天咱俩比比,看谁更能喝!” 杨某本就情绪高涨,一听这话,立刻应战,两人你一杯我一杯地拼起酒来,还夹杂着一些玩笑和争执。 这场拼酒持续了约半小时,期间没人上前劝阻,母某甲作为主家,正忙于其他事务,只是偶尔瞥见他们在喝酒,但没太在意。 很快,杨某明显喝多了,走路摇摇晃晃,说话含糊不清。他独自一人离开母某甲家,没让任何人送。 母某甲和其他宾客以为他只是回家休息,没人多想。 5月6日下午,杨某的家人回到家中,发现他躺在大门内的水缸旁,身体已经僵硬。 家人吓坏了,赶紧报警,警方赶到现场后,确认杨某已无生命体征。经过初步调查,警方排除了他杀可能。 尸体检验结果显示:杨某血液中的乙醇含量高达793.06mg/100ml,这个数值已达到致死量。 警方建议进行尸体解剖以确定具体死因,但杨某家属出于传统习俗和情感原因,拒绝了这一要求。 最终报告只能推断杨某死于急性酒精中毒,但无法排除其他潜在因素。 家属在悲痛之余,认为母某甲作为宴席组织者,以及同桌喝酒的人,尤其是母某乙,应该对杨某的死负责。 2025年中,杨某家属一纸诉状将母某甲、母某乙以及其他5名同桌人员告上法院,要求7名被告共同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抚慰金共计33万余元。 庭审中,母某甲辩称,丧宴是自助餐形式,酒水自便,他作为主家已尽到基本提醒义务,且当时忙于丧事,无法时刻关注每位宾客。 母某乙则承认拼酒事实,但强调杨某是自愿参与,且他离开时意识清醒,自己无法预见到死亡后果。 其他5名同桌人表示,他们只是普通宾客,未参与拼酒,也没义务监控杨某的行为。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指出,母某乙主动发起并与杨某进行拼酒,期间还存在言语冲突,该行为客观上刺激、助长了杨某的过量饮酒。 母某乙的行为超越了普通共饮的范畴,构成了积极的“拼酒”行为,这种行为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在客观上实施了可能危害他人健康的行为。 母某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拼酒的危害应有预见能力,其未能履行对共饮者安全的提醒、劝阻义务,反而实施了加害行为,构成侵权。 同时,《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丧宴虽属私人活动,但组织者母某甲邀请不特定多数人参加,其性质可类比为“群众性活动”,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母某甲未能注意到杨某的醉酒情况,未对拼酒行为进行劝阻,未尽到合理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失,需承担相应责任。 不过,本案无证据证明同桌五人参与了拼酒、劝酒行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杨某家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此外,杨某主动参与拼酒,在无人强迫的情况下大量饮酒,存在主要过错。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杨某的自身行为是导致损害发生的直接和主要原因,相应减轻其他责任人的赔偿份额。 法院综合考虑各方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等因素,酌定杨某自行承担95%责任,母某甲承担2%的责任,母某乙承担3%的责任。 经过审慎核定,法院确认杨某的死亡发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损失合计为96万余元。 最终,法院判决母某甲赔偿19273.74元,母某乙赔偿28910.61元。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