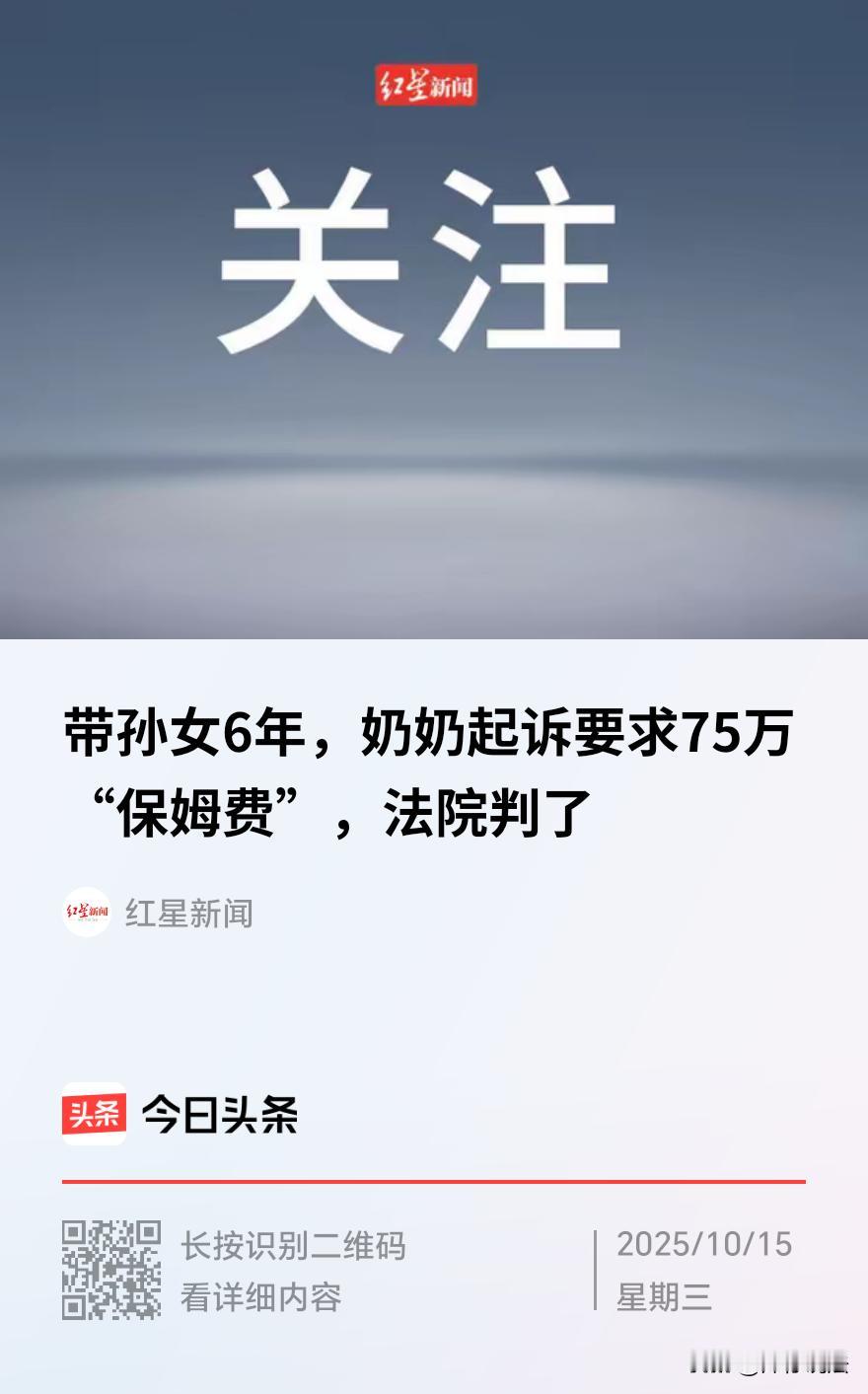新疆,一大娘辞去工作,全身心帮助儿子、儿媳照顾了6年的孙女,儿子虽曾写下每月支付8000元“保姆费”的承诺,但大娘本不打算要。不料,儿媳和儿子因感情问题离婚,大娘拿着承诺书,一纸诉状将儿子和前儿媳告上法庭,索要75万元照顾费。法庭上,儿子对此没有异议,但是前儿媳坚称这是亲情互助,而那张承诺书她从未认可。法院的判决让前儿媳出乎意料。 据红星新闻10月15日报道,六十多岁的徐阿姨(化名)本应享受退休后的清闲时光,但自从2016年孙女小敏(化名)出生后,她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徐阿姨的儿子杨某(化名)和儿媳张某(化名)都是职场人士,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出差。 小敏出生前,徐阿姨还做着几份兼职工作,补贴家用,但看到儿子一家需要帮助,她毫不犹豫地辞去了这些工作,全身心投入到照顾孙女的事务中。 这一照顾,就是整整六年。 徐阿姨是个勤劳朴实的老人,她把小敏当作心头肉,从换尿布、喂奶到陪玩、教说话,她事事亲力亲为。 小敏小时候体弱多病,徐阿姨经常半夜带她去医院,垫付医药费。等小敏长大些,徐阿姨又负责接送幼儿园、报兴趣班,甚至用自己的积蓄买生活用品和衣服。 徐阿姨从未抱怨过,总觉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亲情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家庭关系并非总是和谐。杨某和张某因工作压力大,经常为琐事争吵,夫妻感情逐渐破裂。 2020年,两人经法院调解离婚,小敏的抚养权归双方共同所有,但实际生活中,小敏多数时间由徐阿姨照顾。 离婚前,杨某和张某曾私下商量过徐阿姨带娃的事。有一次,杨某单独给徐阿姨写了一张纸条,承诺每月支付她8000元“保姆费”,作为对她辛苦的补偿。 张某也知道这事,在离婚协商的录音中,她说过“该给的给,我愿意负担一半”,杨某则提到“每人每月分摊五六千元”。 但这些只是口头说说,离婚协议里最终没写进去任何关于“保姆费”的内容。 徐阿姨在儿子离婚后,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些承诺。 2022年7月,徐阿姨忍无可忍,将杨某和张某告上了法院,要求支付“保姆费”75.28万元,垫付费用3.99万余元,并承担诉讼相关费用。 庭审中,徐阿姨情绪激动地拿出杨某写的书面承诺和离婚前的录音证据,坚持认为带娃不是免费的,自己提供了“有偿服务”。 徐阿姨说:“我为他们付出了这么多,辞了工作,花了积蓄,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如从前,他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杨某低头不语,张某则坚决反驳。 张某承认徐阿姨帮了忙,但她强调这是“亲情互助”,不能物化成商业保姆服务。 同时,她说:“那录音只是我们离婚时商量的话,没形成正式协议,没有效力。” 法院会怎么判决呢?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四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法院指出,杨某与张某作为小敏的父母,均健在且具有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经济状况,完全具备抚养能力。 徐阿姨作为祖母,并不直接负有抚养孙女小敏的法定义务,她长达六年的照料行为,本质上是出于血缘亲情,为了帮助子女分担压力而自愿实施的付出。 虽然徐阿姨的行为源于亲情且是自愿的,但法律并非对此视而不见。 《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九条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法院明确指出,在父母具备抚养能力的情况下,徐阿姨没有法定和约定义务照顾小敏,而是基于亲情的、自愿的照顾,本质上属于无因管理。 杨某和张某因徐阿姨代为履行了本应由自身承担的抚养义务而实际获益,理应对其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予以补偿,这符合民法中的公平原则,也是对长辈付出的尊重与认可。 不过,徐阿姨主张按照承诺书及录音中中“保姆费”的标准支付,与尊老爱幼、鼓励家庭成员互帮互助等价值相冲突,不宜僵化适用。 法院认为,若将家庭成员间日常的、一般性的互助行为,简单地物化为具有对价的合同之债,并完全依照此类单方或非正式承诺来计费,将严重损害家庭成员间宝贵的情感联系,不宜生硬地直接采用该书面承诺中记载的金额来计算补偿费用。 此外,对于离婚协商中的录音,双方提出的方案、报价均属于试探性、讨论性的意见,其内容可能随时变化,并未形成最终一致、明确、具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 且杨某和张某最终达成的、经法院调解确认的离婚协议中,并未包含任何关于向徐阿姨支付“保姆费”的约定。这表明,协商过程中提及的方案已被双方最终放弃,未能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条款。 最终,法院基于公平原则,综合考量了徐阿姨为小敏的支出情况等,酌定杨某和张某向徐阿姨支付补偿90277元。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