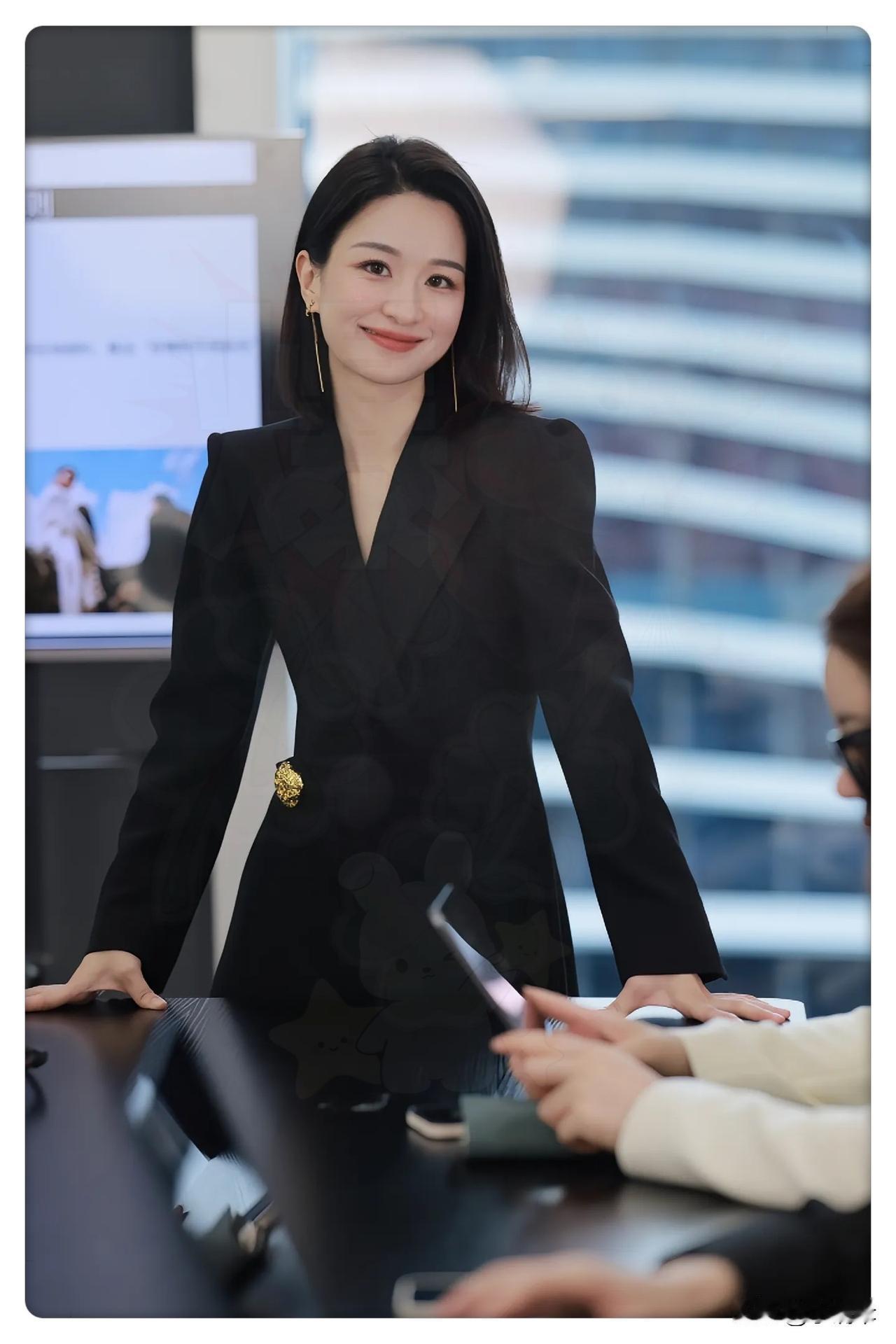老公打我后,我选择不离婚也不和他说话,每天各干各的,互相不沟通,十几年过去了,我宁愿下班回家自己发呆,但一看见他人影子就感觉恶心,再忍忍吧!一辈子就很快过去了。 现在我坐在新租的小房子阳台上,阳光暖烘烘地洒在身上,手里端着刚炒好的两个热菜——以前在那个两室一厅的家里,我连炒个青菜都得算着他回来的时间,生怕在厨房撞见。 那房子,主卧是他的,次卧是我的,客厅和厨房像块冰冷的界碑。我六点下班,先溜进厨房做自己的面条,青菜叶子在锅里翻两下就出锅,碗筷洗得比脸还干净,然后赶紧缩回次卧,手机调静音,连旧电视剧的声音都不敢放大。 他七点半回来的脚步声像定时炸弹,有时带着酒气撞进门,有时裹着烟味飘进来。冰箱下层永远堆着他的挂面、咸菜和速冻饺子,他做饭时铁勺刮擦锅底的声音能穿透墙壁,我得用被子蒙住头,烦躁像藤蔓缠上来——当年他拳头落在脸上的疼,好像又跟着这声音活过来了。 孩子上初中时还能当缓冲,后来去了外地读书,家里静得能听见灰尘落地。他退休后更糟,白天蜷在沙发看电视,或者蹲在阳台摆弄花草,我连客厅都不敢踏出去,饿了就啃饼干,面包渣掉在地上都觉得是罪过。 有次实在饿得发慌,想去煮点粥,刚摸到厨房门,他也跟进来了,说要煮茶叶蛋。两个煤气灶同时蓝幽幽地烧着,他站左边,我站右边,半米距离像隔了条河。空气凝着的时候,他突然叹气:“你也别总吃饼干,对胃不好。”我没应声,拿锅铲的手抖得粥都洒出来,端着碗往房间跑,他又在身后说:“医院体检单放茶几上了,你也去查查。” 半夜被哼哼声吵醒时,我站在卧室门口,看见他蜷缩在客厅地板上,脸色惨白捂着胸口。那三秒犹豫里,我没想过心疼,只怕他死在家里,我得处理那些我根本不想沾的麻烦事。拿起手机打120,医护人员问我是谁,我说“家属”——这是十几年里,我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承认这个身份。 他住院时我没去,孩子从外地赶回来,每天发消息说他醒了就问“妈妈怎么不来”。我只回了句“别让他再联系我”。出院那天他让孩子送回家,我正把衣服往行李箱里塞,他看见箱子愣了半天:“你要去哪?”这是他第一次在沉默里主动开口。 “搬出去住。”我拉上拉链,声音平得像结了冰的湖面。他突然蹲下去,双手抱头呜呜地哭,像个被没收糖的孩子:“我知道错了,当年不该打你,这些年我一直在赎罪……”我没回头,拎着箱子出门时,阳光刺得眼睛发酸,深吸一口气,空气里连灰尘都带着甜味。 新门锁换好那天,我在阳台坐了很久,没有酒气烟味,没有刺耳的锅碗声,发呆都觉得心里敞亮。孩子发消息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吃不喝,我回了句“照顾好自己”,然后把手机调成静音。 以前总觉得一辈子忍忍就过去了,原来真正过去的,是那个总劝自己“再忍忍”的我。现在下班回家,我会炒两个热菜慢慢吃,电视声音想开多大开多大,再也不用捂着耳朵躲进次卧——原来不用忍的日子,连发呆都是舒服的
42岁,老公偷亲我一口,我反手一巴掌,他当场提离婚,签字时我没哭,关上门却蹲在玄
【3评论】【2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