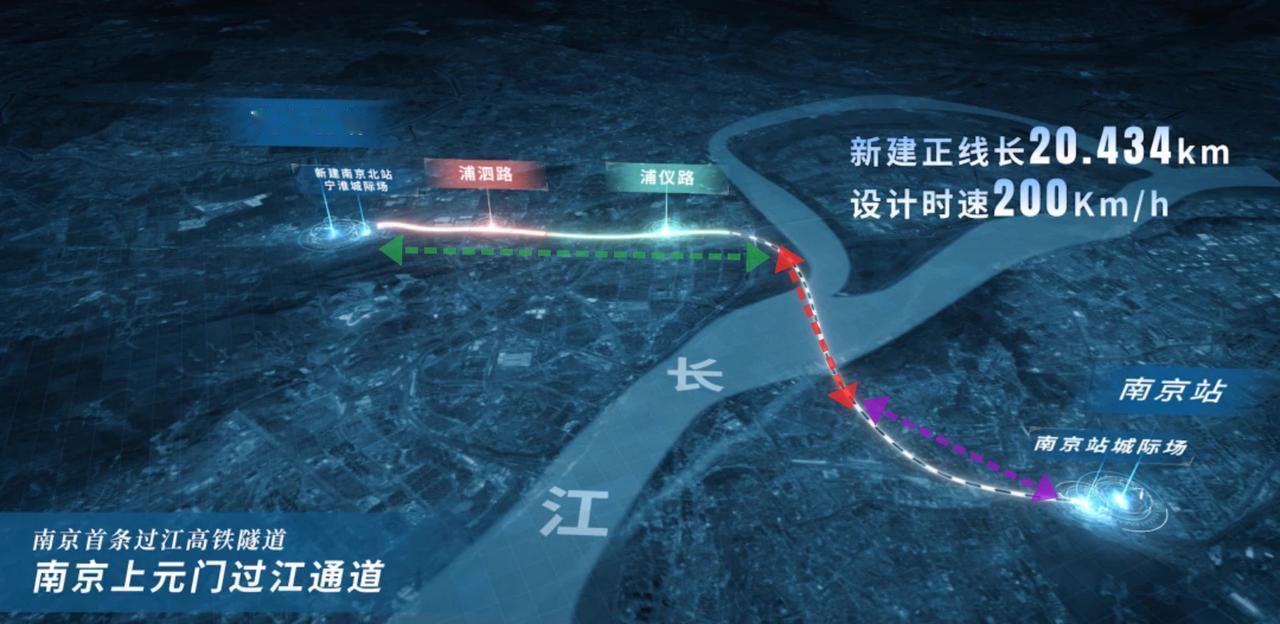1937年,南京,七八名被剥光上衣的青年跪成一排。2个日兵用刺 刀疯狂戳杀。突然,17岁的左润德站立起来,迅速冲向后门。 1937年的南京冬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硝烟与血腥的呛鼻焦味,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对于17岁的左润德来说,生与死往往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皮肤,或者是那一瞬间的呼吸屏障,就在几个小时前,浓烟像是某种窒息的布匹紧紧裹住了视线,背后的热浪灼烧着后背。 那种滚烫的痛感让左润德的泪腺几乎失控,泪水冲刷着满脸的烟灰,根本分不清是为了这一刻肉体上的煎熬,还是为了那一堆堆无辜死去的生命,这是日军罪恶的现场,他们在用大火企图掩盖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 但也就是这灼热的烈焰,强行唤醒了本来在尸堆中因为失血和极度恐惧而濒临昏厥的少年意志,他知道,这把火虽然是为了毁灭罪证,却成了他绝处逢生的最后警钟,如果现在不动,自己就真的会变成这灰烬中的一部分,永远消失在这段黑暗的历史里。 命运似乎总爱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开着残酷的玩笑,在此刻的灼热之前,仅仅是几天里,他先是经历过足以冻碎骨髓的冰寒,时间倒回到他第一次决定“拿命去赌”的那一刻,为了引开像饿狼一样扑向家里的日本兵,给爹娘争取那一线生机,他孤身冲进了复杂的巷弄。 那一刻他甚至在心里悲壮地默念着老话:“没关系,大不了就是一死,三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娃,这一片片交错的巷子和城外的护城河,是他童年记忆里最亲切的地图。 那些曾经在五六岁时光屁股摸鱼抓蟹的河水,却在那个晚上变成了阻断生死的寒冰炼狱,日本人虽然很快识破了他的逃跑路线,但仗着对地形的绝对熟悉,他利用巷子的缺口和死角,暂时甩开了后面叽里呱啦喊着“抓住他”的追兵。 前无去路,唯一的生门就是那条连通城外的河,左润德根本没有犹豫的资本,纵身一跃,四天滴水未进而早已虚脱的身体,被瞬间像蛇一样滑腻阴冷的河水紧紧缠绕,那是一种刺进毛孔的痛,像是无数根针扎进皮肤,冷风一吹,整个人都不住地打战。 熟悉水性救了他一命,但也几乎耗尽了他仅存的热量,当他全凭本能机械地划动手脚爬上岸时,意识早就模糊了,连确定周围安全与否的力气都没有,便一头栽倒在黑暗中,当再次醒来,身上的冰冷变成了一种奇异的干爽。 这一刻的温暖几乎让他产生幻觉,一位陌生的老大爷正守在板车旁,原来是一对同样在逃难的老年夫妇,不仅救起了这个半只脚踏进鬼门关的少年,甚至好心给他换下了那身足以冻死人的湿衣裳。 这短暂的人性光辉,在这个残酷的世道下显得格外耀眼,他们商量着搭伙一起逃,指望着人多有个照应,能在这乱世里偷回几条命,可日本人没给他们这个机会,这种温情的泡沫迅速破裂,三个人连同大批流离失所的百姓再次落入魔掌。 河滩边,人群黑压压地跪着,年轻的、年老的、甚至是还在襁褓中的孩子,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恐,这次没有人能跑,刺刀和枪口构成了绝对的死亡围栏,有些年轻人的上衣被强行剥去,日军像是戏弄猎物一般用刺刀戳刺,逼迫他们跪下。 那是一种无声的绝望,只有粗重的呼吸在冰冷的空气中化作一团团白雾,左润德再次感到了那种熟悉的不祥预感,这种预感伴随着远处架起的机关枪变成了现实,并没有过多的审判或言语,日军那让人毛骨悚然的欢呼尖叫声,成了死神降临的前奏。 这群暴徒仿佛从杀戮中获取了某种变态的兴奋,机关枪喷吐着火舌,扫射而过,人群像割麦子一样成片倒下,鲜血瞬间把曾经抓鱼摸虾的河水染成了触目惊心的红,在枪响的瞬间,左润德本能地顺势倒下,身边的百姓一个个在他身上堆叠。 温热粘稠的液体很快浸透了他刚换上的干衣,他的心脏狂跳,快要撞破胸膛,但他死死咬着牙,在尸堆中伪装成一具没有生气的躯壳,直到那把毁尸灭迹的大火烧起,罪恶之所以被称为罪恶,是因为无论施暴者如何掩饰,总会有人活下来审判这一切。 左润德心里那个关于爹娘是否安全的念头,那个要活下去揭露这一切的念头,在烈火逼近时给了他惊人的力量,他愤恨,这么多的生命,明明应该有属于他们的生活,却在短短几分钟内化为乌有。 在日军撤离后的间隙,左润德忍着剧痛和呛咳,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拖着受惊受冻的身体,从这片还在燃烧的修罗场中一点点爬了出来,身后是渐渐化为灰烬的过去,前方是未知的漫漫逃亡路,但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是从地狱里抢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