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一次宴会上,一个歌伎走到狄青面前敬酒,嘲笑道:“敬斑儿一杯。”引得哄堂大笑。对此,狄青敢怒不敢言。 1057年,汴京城里,枢密使狄青的灵柩已停在相国寺。 四十九岁的他,从罪卒到权臣,用了三十年。 从权臣到孤魂,却只用了三年。 狄青的命,从十六岁就被刻上了“贱籍”。 山西汾阳的穷巷里,他跟着哥哥狄素种地。 那时候的日子简直太苦了,家里揭不开锅的日子简直太多了。 十八岁那年,狄素与人斗殴致死,按宋律当刺配充军。 狄青跪在公堂上,把“罪”字顶在自己头上:“我替兄受刑。” 于是,他的脸上被刺了“贼配军”三个字,押去延州戍边。 边地的风比汾阳更烈。 狄青没怨过天,只在训练时比别人多跑十里,在作战时比别人多冲半里。 他总戴副铜面具,遮住脸上的刺青。 不是怕羞,是怕敌人看清他的脸,再给宋军多留个笑柄。 二十五场西夏战役,他从没败过。 士兵们看他戴着面具冲锋,喊他“面涅将军”,敌军听他马蹄声近,先怕那副面具后的狠劲。 宋仁宗不是没见过狠将,但狄青的狠,狠得让他心痒。 西夏战场上,狄青的部队纪律严得像铁块。 他们从不抢民粮,不杀降卒,连营火都只点三堆,怕暴露目标。 庆历四年,仁宗见他递来的捷报,没犹豫就下笔写下了赏赐:“擢延州指挥使。” 后来又升枢密副使,管全国兵符。 皇祐四年,侬智高叛乱,狄青主动请缨,仁宗连夜批了“宣徽南院使”,命他平南。 侬智高在广西自立“南天国”,宋军连吃败仗。 狄青带兵到桂州,先闭城三日,把扰乱民生的士兵全斩了。 再派细作混进叛军,摸清粮道。 决战那日,他穿素甲骑白马,号令“击鼓三通,四面围杀”。 箭雨裹着喊杀声砸向叛军,侬智高的弟弟侬建中当场被砍,黄师宓的首级挂了三天。 叛军跑,狄青追,叛军躲,狄青烧。 最后侬智高逃到大理,脑袋被挂在邕州城门,这场仗,狄青用三千人,灭了五万人。 凯旋那日,仁宗在垂拱殿摆宴。 他握着狄青的手:“卿的刺青,是朕的荣耀。” 说着递过药膏:“朕命太医配的,能消些字迹。” 狄青跪下来:“陛下提拔臣,因臣的战功,臣的战功,因这刺青。留着吧,能让将士们知道,臣的每一刀,都为大宋而砍。” 仁宗红了眼眶,他知道,这面具下的,是颗比金子还硬的忠心。 可文官的刀,比西夏的箭还密。 韩琦是出了名的“文臣标杆”,最恨武将掌权。 狄青的好友焦用,本是陕西驻泊都监,因替狄青说过几句公道话,被韩琦扣上“通敌”罪名,一刀砍了。 狄青想闯韩府讨说法,门房啐他一脸:“枢密使又怎样?武官的命,比狗贱!” 他站在韩府门前,终于明白了,皇帝能保他官,保不了他命。 更扎心的是日常的羞辱。 朝堂上,文官们总拿他的刺青说笑:“狄相公脸上的‘贼’字,该用朱砂描描,更显威风。” 私下里,连武将家的歌伎都敢凑趣。 有次狄青去韩琦府赴宴,歌伎白牡丹舞罢,端着酒盏走到他面前:“敬斑儿一杯。” “斑儿”是刺青的俗称,顿时,满座哄笑。 狄青端着酒,想起焦用的血,想起自己替兄受的刑,可还是没敢泼回去。 他怕,怕这一泼,连最后一点体面都没了。 皇祐五年,狄青被罢枢密使,贬去陈州。 仁宗不是没挣扎过。 文官们联名上书:“武人掌枢密,国朝未有!” 韩琦跪在殿上哭:“陛下忘了太祖杯酒释兵权了?” 连欧阳修都写文章,说“狄青有雄才,恐非社稷之福”。 仁宗苦苦硬熬了三个月,到底松了口。 陈州的宅子漏雨,狄青在屋里翻旧物。 他找出当年仁宗赐的药膏,盒子都霉了,又摸出焦用送他的玉坠,绳结早断了。 夜里他常梦到焦用,梦到两人在延州校场比刀,梦到焦用说:“青哥,等我升了官,给你摆酒庆功。”惊醒时,枕头湿了一片。 1057年,狄青病重。 他让人把灵柩停在相国寺,棺木上不刻铭文,只写“狄青”二字。 临终前,他望着窗外的桃花,轻声说:“我这一辈子,替大宋砍了无数敌人,最后,被大宋砍了自己。” 狄青走后,汴京城里有人说他“功高震主”,有人说他“不懂收敛”。 可更痛的是,一个能平南蛮、败西夏的将军,竟活不过一群舞文弄墨的文官。 宋朝的重文轻武,从太祖杯酒释兵权开始,就成了刻在骨血里的规矩。 文官要控军权,武将要保性命,中间哪有活路? 狄青的面涅未消,可大宋的武备,早随着他的死,慢慢锈了。 后来靖康之耻,金兵破城时,没人再喊“面涅将军”。 那些曾为狄青喝彩的士兵,早死在了文官的偏见里。 再锋利的刀,若总怕它割到手,终会被自己磨钝!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北宋名将脱颖而出于渭州 揭秘你所不知道的狄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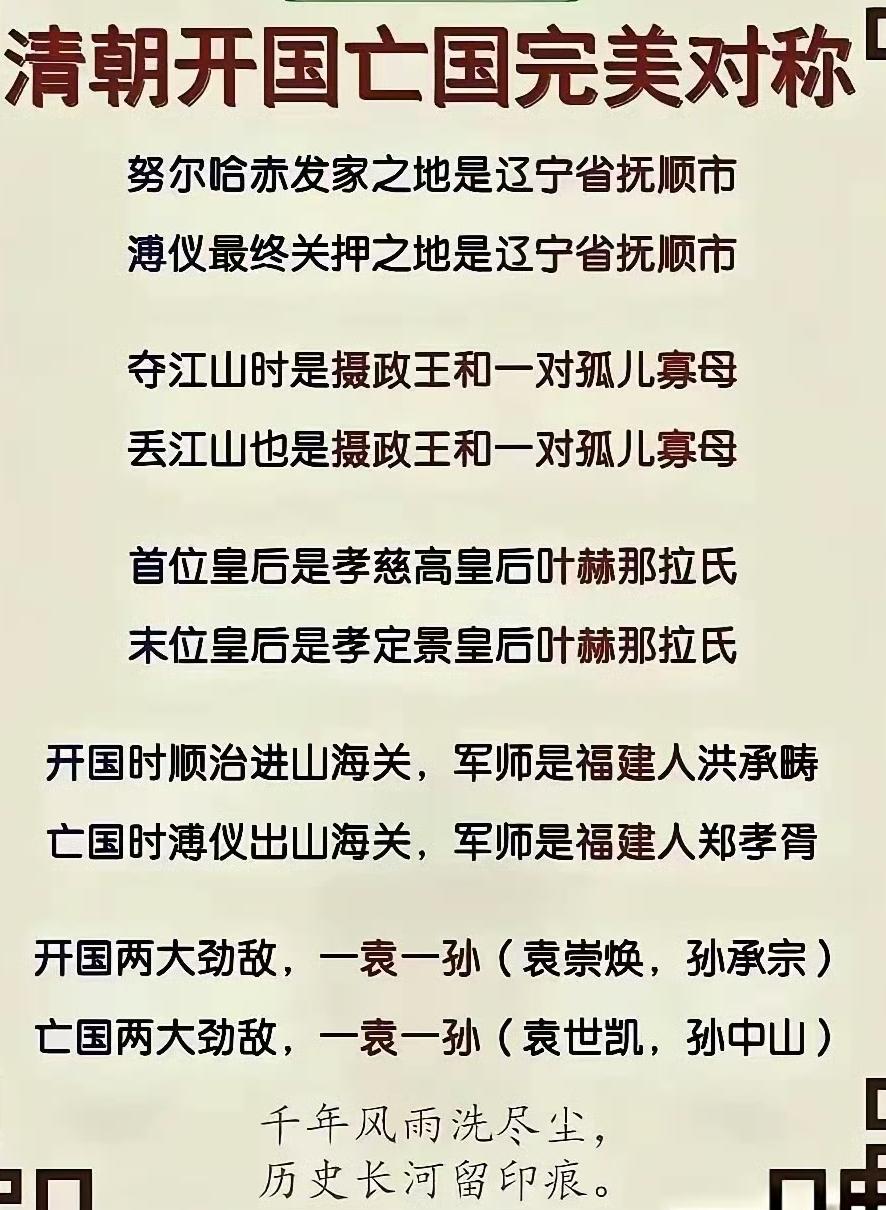
![历史上真正的奸贼是北宋六贼,高俅在这里连号都排不上[吃瓜]](http://image.uczzd.cn/10592004370560617785.jpg?id=0)

![司马懿要是死前说这种话的话,手下人应该会怀疑他是诈死,边上埋伏了刀斧手。[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943140111545882896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