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8年,南宋科举考试结束,赵构发现探花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便问道:“你多大了,有孩子吗?”谁料,对方直言:“草民73岁,并未娶妻生子。”结果,赵构笑道:“30岁的宫女,赏给你了!” 大殿里的几位阅卷官都评审过这位老考生完成的策论文章,却没人能想到,对方竟然是一个连家室都没有的七十多岁老人。 陈修家里珍藏着几十张准考证。从建炎二年到绍兴八年,每一次科举考试的文书,都被他用油纸仔细地包裹好。以至于同乡曾打趣他:“你这哪里是赶考,分明就是一场奔赴科举的朝圣之旅。” 确实,他的青春、壮年乃至老年,都消耗在了临安与福州之间的那条驿路上。最开始还能骑马,后来只能骑驴,科举考场里的小树苗都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看守考场的士兵也换了一拨又一拨。 绍兴六年那次落榜后,他在钱塘江边租了一间漏雨的简陋房子。每到月初和月中的夜晚,都能望见对岸府邸夜宴的灯火通明。某个中秋夜晚,他更是对着江心的明月写下诗句:“岂不念旧乡,终期奏凯还。” 直到他七十三岁那年的春天,主考官在殿试的考卷里读到一段关于漕运改革的论述,拍着桌子连声称赞。皇帝赵构亲自用朱笔在“陈修”两个字上画了圈,并写下批示:“见解老练成熟,善于谋划国事。” 发榜公布名次的时候,有人看见这位老进士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块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干粮,那是他母亲临终前塞进他行李的,早已发霉变质,认不出原本的样子了。 施氏是在宣和七年进宫的,那一年金兵南下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汴京。她作为苏州织造官员的女儿被选拔入宫,原本被分配在贵妃的院子里伺候笔墨。靖康二年的冬天,虽然她跟随当时的康王(即后来的赵构)南渡长江侥幸躲过了灾难,但却跟她的家人失去了联系。 “娘子真是好福气啊,”内侍太监送来赐婚的诏书时,脸上堆着恰到好处的笑容,“陈探花是陛下亲自选拔的人才。” 她安静地磕头感谢皇恩,转过身开始收拾梳妆匣,里面躺着一枚羊脂玉佩,是她在十五岁行成人礼时祖母送给她的,说是能保佑婚姻美满。她在深宫里待了十八年,看惯了红颜在等待中悄悄老去、白发不断新生的景象,没想到最终要托付终身的人,是个年纪比自己父亲还要大的老者。 成婚那天,百姓都挤在路边争看热闹,有个年幼的孩子大声问:“新娘子怎么藏在轿子里不出来呀?”母亲急忙捂住孩子的嘴:“别乱说!那是去给老状元冲喜的!” 这些议论声传不进施氏的耳朵里。她坐在轻轻摇晃的喜庆花轿里,忽然想起去年清明节,在慈宁宫走廊下遇见一位白了头发的宫女。那个人痴痴地望着墙外飞过的风筝,哼唱着没有人能听懂的江南小调。 洞房花烛夜,施氏看着镜中自己依然年轻的容颜,想起下午听到喜婆的私下议论:“老爷子连交杯酒都端不稳呢……” 可谁能想到,第二年重阳节,陈府就喜得贵子。后来,陈修对自己的学生说:“知道吗?我二十岁的时候总是害怕来不及,现在反倒觉得,人生无论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学生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看见施氏正在陪着儿子玩耍。 其实,陈修的故事之所以能被记载进史书,离不开宋朝特殊的“特奏名”制度。这个从太祖皇帝时期创立的制度,本质上是给那些多次参加科举却始终没有考中的读书人最后的一份体面,就像现代社会的补偿机制,让那些在科举道路上耗尽了青春年华的读书人,至少能戴着官帽安葬于故乡。 只不过,赵构自己可能都没想到,他这次带着补偿性质的赐婚,竟然真的成就了一段姻缘。 信源:《宋史》 文│一阳 编辑│史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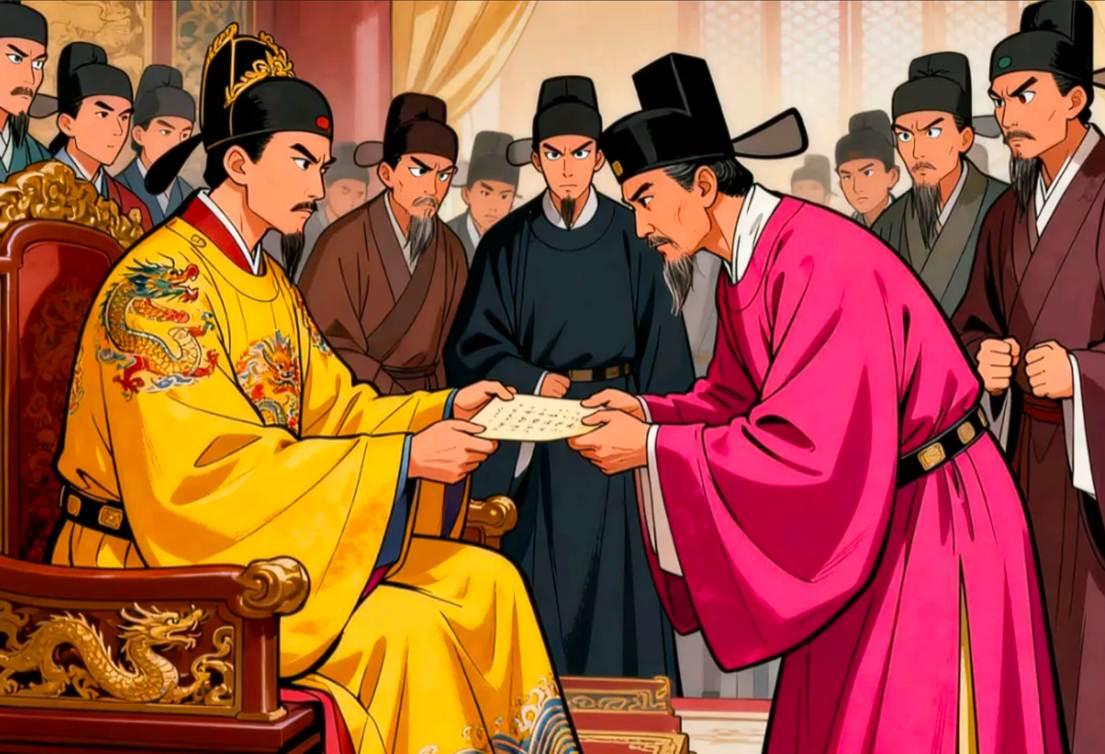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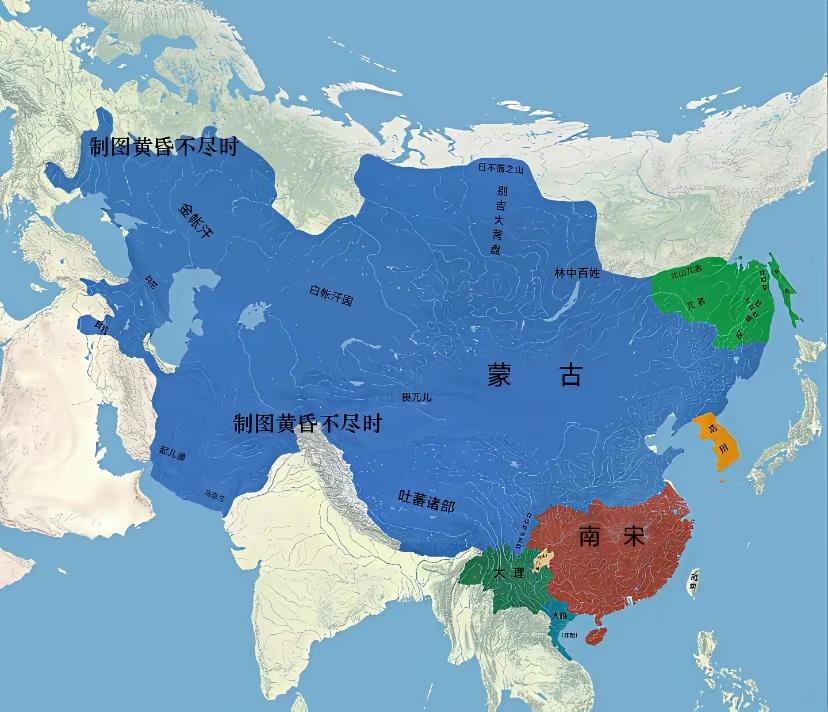




火山
探花是不可能授于一个73岁老人的,一甲前三名中,探花必选长的最好看的那个。
相逢一笑
三鼎甲中状元榜眼好像没特殊要求,但探花要求必须是英俊帅气,七十多岁的人怕是不沾边吧?
用户10xxx84
前三名是通过殿试,经过皇帝亲钦点的。怎么中了探花皇帝还不知道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可知道探花是全国的第二名
厚德载物 回复 10-21 20:24
榜眼是第二
相逢一笑 回复 10-21 22:25
第三
用户10xxx07
纯属扯淡。
王鸿超
古时七十三岁母亲仍然健在?
君子博学而日省已身 回复 10-25 15:35
仔细看,看仔细
大师 回复 10-22 14:57
小说情节
用户10xxx78
南宋陈修七十三岁考中探花,赵构赐一位30岁宫女为妻,此宫女是官家的女儿,结婚后,第二年重阳喜得贵子,而且还收留了三个孤儿,最后都考起了功名,陈修一直活到九十四岁任上死的!
达伍
肯定法院不会判全退完了,至少说这大爷舒服了N多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