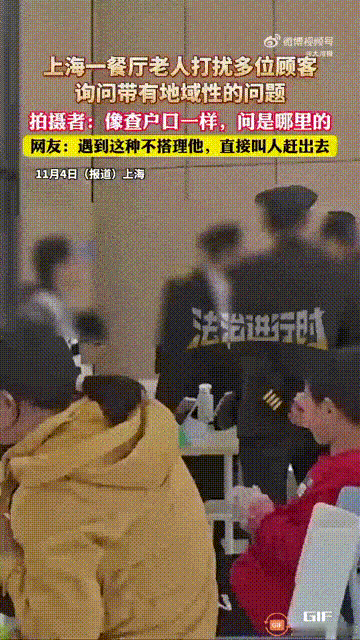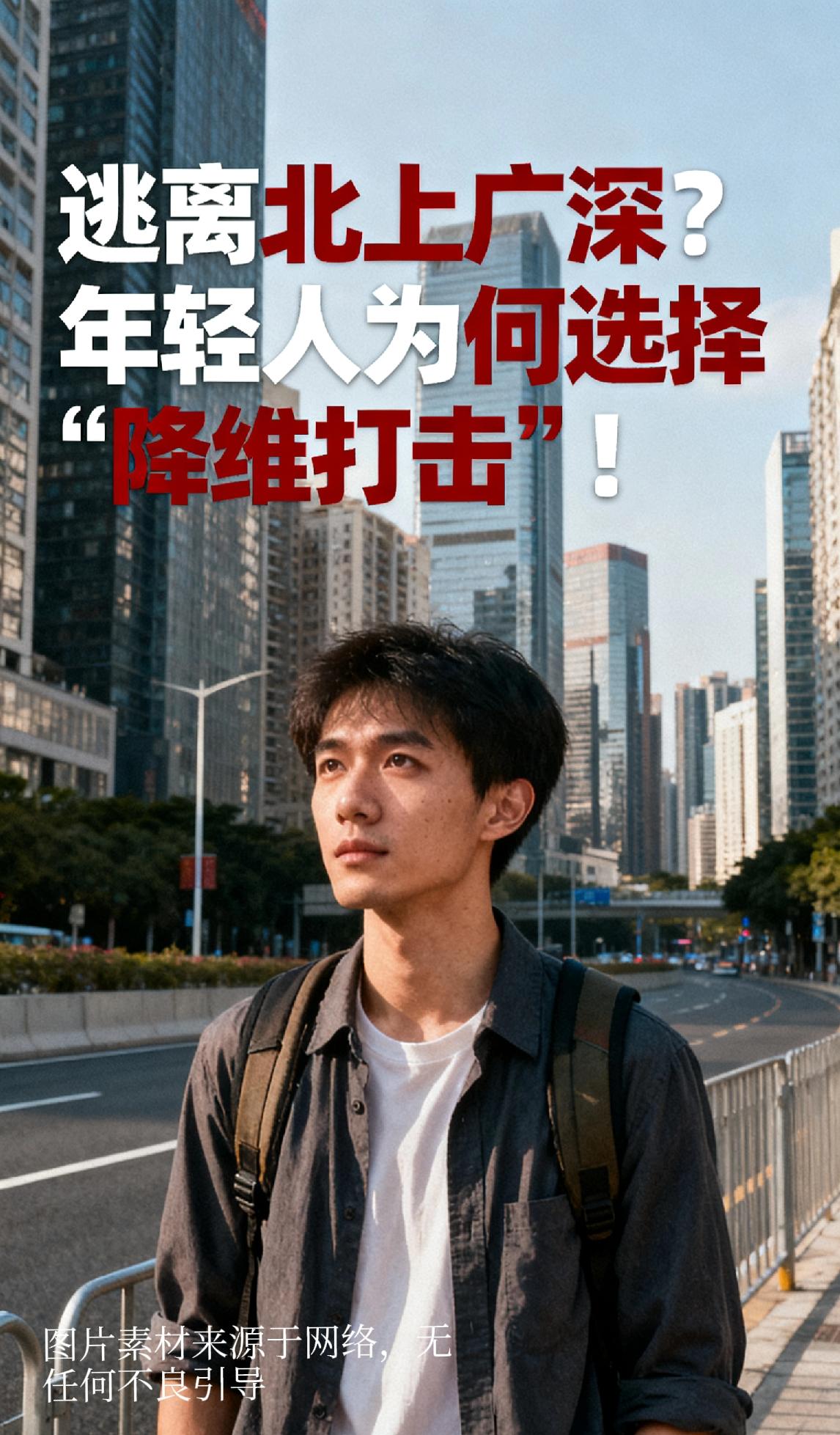一位殡葬公司经理说: “现在的年轻人,良心都被狗给吃了。我们根据相关部门要求,建造了一些价格低廉的墓地,比如壁葬价格2000元,花葬99元,树葬免费,在一些地势低洼的地方墓地9999元,这些墓地我们公司没有任何利润,甚至还有亏钱。我们主体墓地的价格有30多万的,20多万的,也有七八万的,是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父母去世之后,他们都不愿意给父母买一个好一点的墓地,刻意选择那些价格最便宜的地方,也不在乎地势低不低,风水好不好,墓地那里有电线杆,有铁塔,也完全不在乎了。甚至还有人完全选择是树葬,到树林子里面随便挖个坑就把父母的骨灰盒给埋了,没有墓碑,也不起一个小坟包,以后供坟都找不到地儿!” 孔子:“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孔子的诘问穿越千年,直指核心:孝道的根本在于“敬”,而非仅仅是物质上的“养”。 殡葬经理看重的是物质的价位,而年轻人可能更注重自己内心对父母的“敬”,并认为这与墓地的价格无关。 《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传统的孝道观,强调的是对自身生命的珍爱和建功立业。它将孝道贯穿于生者的行为之中,而非仅仅体现在逝后的丧葬规格上。 现代年轻人的选择,或许是将重点从“葬之奢”回归到了“生之孝”。 庄子:“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庄子认为生死是自然过程的安排,死亡是一种安息。如果秉持此念,那么树葬、花葬让生命回归自然,恰是最尊贵的“息”,为何非要一个昂贵的人工建筑来禁锢灵魂呢? 孔子(人问禘之说):“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 孔子认为,理解礼仪真谛的人,治理天下都易如反掌。礼仪的本质在于内心的仁与敬,而非外在的繁文缛节和排场。 当昂贵的墓地脱离了“敬”的内核,而沦为一种攀比的商品时,它是否还符合“礼”的本意? 亚当·斯密:“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这位经理将低价墓地描述为“无利润”甚至“亏钱”的公益行为,但其商业模式的本质,依然是希望通过低价产品引流,或反衬出高价主墓地的“价值”,最终目的仍是追求主体墓地的利润。 用“孝道”来批判市场选择,本身也是一种商业话术。 泰勒斯(古希腊哲学家):“生死并无区别。因此有人问他:‘那你为何不去死?’他答道:‘因为并无区别。’” 执着于坟墓的规格,在某种程度上是生者无法正视死亡、无法放下对物质形式执念的表现。 凡勃伦:“炫耀性消费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博取荣誉。” 高价墓地,在很多情况下,已不仅仅是安葬行为,更是一种“炫耀性消费”。它是做给活人看的“荣誉纪念碑”,用以彰显子女的经济实力和“孝心”。 当年轻人不再认同这种价值观时,这种消费就失去了其核心吸引力。 “孝心货币化”,价格等于心意吗?其实,未必。 将孝心与墓地价格直接挂钩,是商业社会对传统伦理最成功的“异化”之一。 它巧妙地构建了一套“价格越高,孝心越诚”的评判体系。 何为对生命的尊重? 经理代表着一种“入土为安、讲究风水、世代祭扫”的传统生死观。坟墓是连接生者与逝者的物理纽带,是家族记忆的地理坐标。因此,“找不到地儿”供坟,是不可接受的。 而许多现代年轻人,成长于一个更城市化、流动化和原子化的社会。他们的生死观更倾向于 “精神纪念”与“生态回归”。 精神纪念: 记忆存放在心里和云端,而非固定在一块无法带走的墓碑上。 生态回归: 认为树葬、花葬让生命以另一种形式滋养世界,是更高级、更浪漫的永恒。 他们不是在随意“挖个坑”,而是在为父母选择一种“向死而生”的哲学。 要知道,现实生活中,对于很多并不富裕的年轻人来说,动辄数十万的墓地,是一笔沉重的、甚至需要负债的支出。 他们可能面临着自身的房贷、子女的教育、生活的压力。 在“为逝者购买一个符号”和“为生者保障一份现实”之间,他们被迫做出了一个功利但务实的选择。 这并非不孝,而是在高昂的生活成本下,一种充满无奈的“生存优先级”排序。 父母当年倾其所有,是为了子女的“生”;子女今天精打细算,或许是为了自己和下一代的“生”。 这其中的伦理困境,远非一句“孝道沦丧”可以简单概括。 因为,孝道在于生前点滴的关爱与尊重,而非逝后铺张的排场。与父母在生前达成对身后事的共识,是比任何昂贵的墓地都更高级的孝行。 当孝道从价格标签上解放出来,它或许才能在人性的深处,找到它最真实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