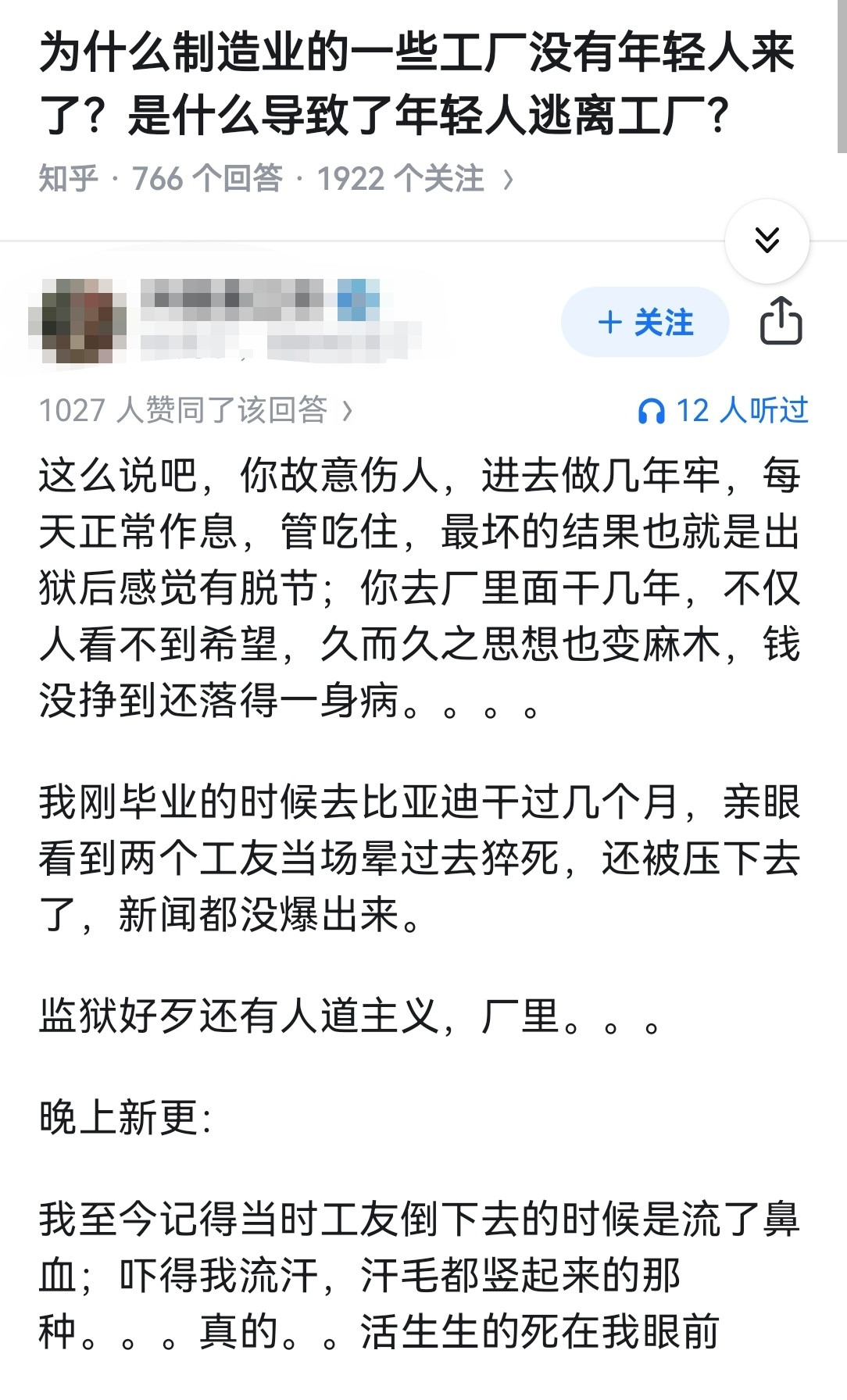我爸第一次打我妈,我妈拿刀砍了他胳膊一刀,缝了好多针。我妈砍我爸,又拿刀去砍我那挑拨离间的奶奶,我奶吓得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这事是我十岁那年发生的,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天傍晚我在院子里写作业,突然听见屋里传来摔东西的声音,紧接着是我妈的哭喊和我爸的怒吼。 十岁那年的傍晚,光线把院子里的老槐树影子拉得老长,我趴在石桌上写作业,算术本第73页的“鸡兔同笼”,铅笔尖在“兔腿”那栏戳出第三个小坑时,西厢房的玻璃窗突然“哐当”一声炸响。 是我爸的搪瓷缸子摔在地上,碎瓷片溅到墙角的酸菜坛子,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紧接着是我妈的声音,不是平时哄我吃药时的软和调,是被捏住脖子似的哭喊:“你凭什么打我?!” 然后是我爸的怒吼,像开春解冻时炸冰的闷响:“我打你怎么了?翅膀硬了是不是!” 我攥着铅笔僵在原地,看见我妈披头散发地从屋里冲出来,右手举着把豁了口的菜刀——那是她早上切萝卜干用的,刀刃上还沾着点橙黄的萝卜屑——左手死死抓着我爸的胳膊,指甲掐进他肘弯的肉里。 我爸想甩开她,她却突然松了手,菜刀“唰”地往下落,又猛地往上一挑。 血一下子涌出来,顺着我爸的胳膊流到手腕,滴在他蓝布褂子上,洇出一朵深色的花。我妈站在那儿喘气,胸口一起一伏,眼睛亮得吓人,像是把星星揉碎了塞进去。 “你再动我一下试试。”她声音很轻,却比刚才的哭喊更让人发颤。 我爸没敢动,只是捂着胳膊,血从指缝里往外冒,他看我妈的眼神,有惊,有恨,还有点说不清的怕。 可我妈没停,她把沾血的菜刀扔在地上,转身进了厨房,又拎出另一把刀——那把新磨的,切肉用的,刀刃在夕阳下晃得我睁不开眼。 “还有你!”她突然转向东厢房,声音像淬了冰,“天天在他耳边嚼舌根,说我藏私房钱,说我对老的不好,现在满意了?” 东厢房的门“吱呀”开了条缝,我奶奶探出头,看见我妈举着刀冲过来,嘴里“哎呀”一声,转身就跑。她穿着那件灰布棉袄,头发被风吹得像团乱麻,顺着院外的土路往南跑,后来听邻居说,她一口气跑过了王家屯,跑过了铁路桥,跑到二十多里外的姨婆家时,鞋底子都磨穿了。 我爸这才反应过来,捂着胳膊往村卫生所跑,血滴了一路,像一条歪歪扭扭的红绳子。我妈站在院子中央,手里的刀“哐当”掉在地上,她突然蹲下去,抱着头哭起来,肩膀抖得像秋风里的玉米杆。 那天的算术本,我再也没写完。铅笔尖断了,我蹲在地上捡碎瓷片,摸到一片带着萝卜屑的,突然想起早上我妈切萝卜干时,还哼着歌给我剥橘子,橘子皮的水溅到她手背上,她笑着说“真甜”。 那时我不懂,为什么平时连踩死蚂蚁都要念叨半天“罪过”的人,会突然变成握刀的模样?为什么我爸平时给我买糖葫芦时那么温柔的手,会挥向那个给他缝补袜子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我奶奶总在我爸喝了酒之后,凑到他耳边说“你媳妇今天又偷懒”“她藏私房钱给娘家”,那些话像小石子,一天天扔进我爸心里的水坑,直到那天傍晚,水坑终于炸了。而我妈心里的堤坝,也在那声怒吼里,彻底塌了——她不是突然变成“疯婆子”的,她是被揉皱的手帕,被磨破的围裙,是无数个夜里咬着嘴唇没哭出声的忍耐,终于在那天傍晚,烧着了。 那天晚上,我爸在卫生所缝了十五针,护士说再偏半寸就到动脉了。我妈在院子里坐了一夜,怀里抱着我那件掉了纽扣的旧毛衣,天快亮时,她轻轻说:“以后不打你爸了,也不追你奶了。” 可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就像那扇被搪瓷缸子砸裂的玻璃窗,后来用胶带粘了又粘,可下雨时,风还是会从裂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 现在我偶尔回老院子,夕阳还是会把西厢房的玻璃窗照得发亮,石桌上的算术本早就不见了,只有我妈当年掉在地上的那把菜刀,被她收在厨房最底层的柜子里,刀鞘上的红漆,掉了一大块。
我爸第一次打我妈,我妈拿刀砍了他胳膊一刀,缝了好多针。我妈砍我爸,又拿刀去砍我那
好小鱼
2025-12-14 15:50:07
0
阅读: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