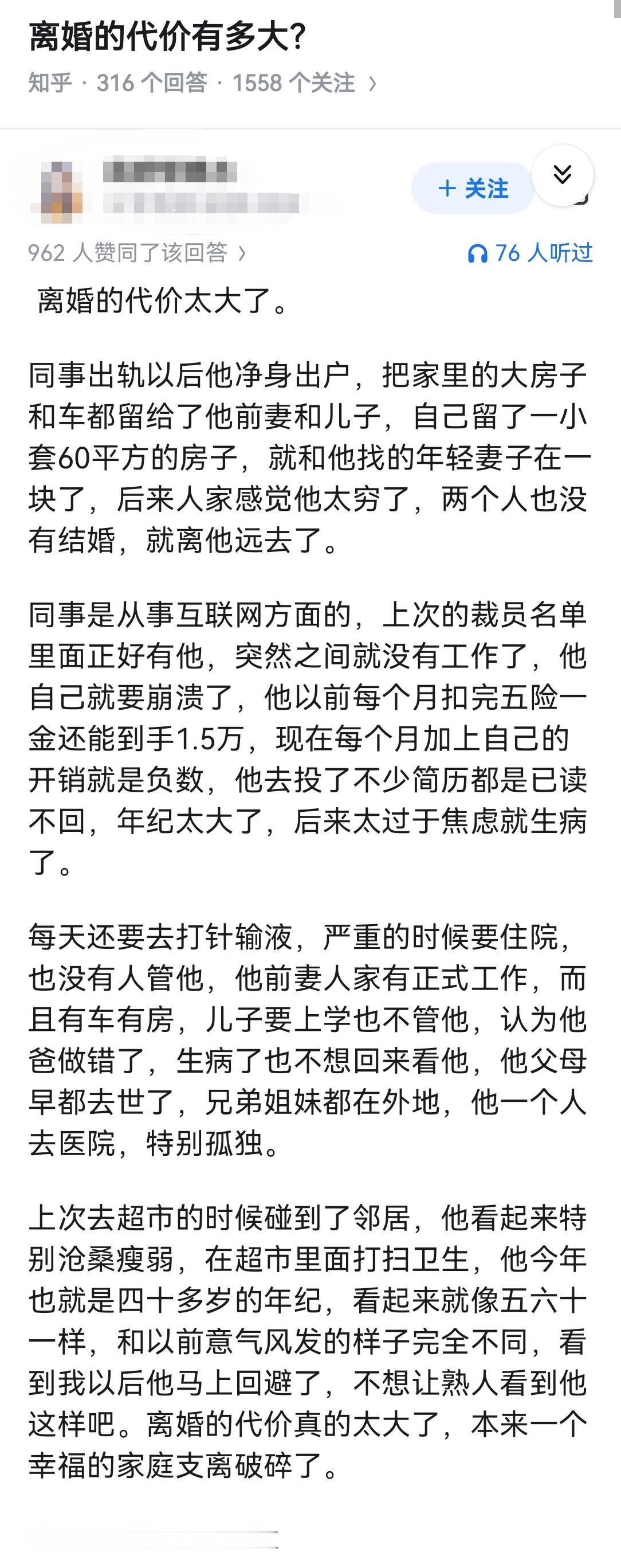我4婚了,头婚给人家生了两个女儿,离婚了孩子给前夫,二婚给人家生了一个女儿,离婚又是孩子给前夫抚养。三婚给人家生一龙凤胎,离婚还是给前夫抚养,现在这第四次婚姻,心理矛盾极了。 傍晚六点半,厨房的抽油烟机嗡嗡转着,锅里的排骨汤咕嘟冒泡。老张站在旁边剥蒜,手指关节上有道旧疤——去年我切菜走神,他伸手挡了一下,到现在还留着印子。我握着汤勺的手有点抖,无名指上的婚戒硌得指骨生疼,这是第四枚了。 第一次戴婚戒时,我才十九岁,彩礼是两头猪,前夫说“给我生个儿子,保你一辈子吃香喝辣”。后来生了大妞,又生了二妞,他妈的脸一天比一天黑,直到有天把我的行李扔到院里,说“不会下蛋的鸡,滚”。我走的时候,大妞扯着我衣角哭,二妞在襁褓里咂嘴,我没敢回头,怕一回头就舍不得。 第二次是在东莞打工时认识的,他说“我不重男轻女,女儿也好”。我信了,孕期给他织了件毛衣,针脚歪歪扭扭的。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儿,他抱着看了一眼,递给护士就走了。后来才知道,他早有家室,我不过是他老乡口中“临时搭伙的”。离婚那天,他塞给我五千块,说“孩子跟我,城里上学方便”,我捏着钱站在民政局门口,风把眼泪吹得满脸都是。 第三次是在老家相亲,男人比我大十岁,带着个儿子,说“你给我生个,不管男女,咱俩好好过”。我想着,这次总该稳当了吧?怀龙凤胎的时候,他每天给我炖鸡汤,我摸着肚子笑,觉得苦日子到头了。可孩子刚满百天,他儿子偷偷跟我说“爸跟奶奶说,等你坐完月子就离婚,龙凤胎是他家的种,不能给你”。那天夜里,我抱着两个软软的小团子,亲了又亲,天亮还是把他们放在了婴儿床里——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带两个孩子? 现在老张把剥好的蒜放进锅里,汤香混着蒜味飘过来。他突然说:“明天去医院做个检查吧?我妈问了,说咱们该要个孩子了。”我手里的汤勺“哐当”掉在锅里,溅了点汤在手上,烫得我一哆嗦。 他赶紧拉我到水龙头下冲,问“怎么了?”我张了张嘴,眼泪先掉了下来:“老张,你说,一个女人,到底要把心掏出来多少次,才算够?” 头婚那年冬天,我抱着刚满月的老二坐在冰冷的台阶上,前夫他妈在屋里摔碗,说“丫头片子没用,我们老李家不能断了根”,我哭到天亮,眼睛肿得像桃子,最后是前夫蹲下来,声音冷得像冰,“你走,孩子留下,不然我让你见不到第二天太阳”;二婚时,我在出租屋里发高烧,他打来电话说“孩子我带着呢,你别来了,影响我再婚”;三婚龙凤胎周岁那天,我买了两套小衣服,站在他家楼下,看见他抱着儿子,他新娶的老婆抱着女儿,一家人笑得那么热闹,我把衣服放在门卫室,转身就跑,生怕被认出来——原来不是我不要孩子,是那些年我连站在他们身边的资格都没有。 老张关了抽油烟机,厨房突然安静下来。他从背后抱住我,下巴抵在我发顶,旧疤蹭着我的手背:“我知道你怕。”他顿了顿,声音有点哑,“但你看,这疤快一年了,还没消呢,我都没嫌它丑。” 我转过身,看见他眼里的自己,头发白了几根,眼角有细纹,可他伸手擦我眼泪的动作,跟第一次见面时一样——那天我在菜市场捡别人扔掉的菜叶,他开车经过,摇下车窗问“大姐,要不要搭车?”,我以为是骗子,他却从后备箱搬下来一袋土豆,说“我妈种的,吃不完”。 汤还在咕嘟,老张盛了一碗,放了点葱花递过来:“先喝汤,凉了该腥了。”我接过碗,婚戒在他掌心蹭得温热,突然想起昨天整理衣柜,翻出一个旧铁盒,里面是四个孩子的照片——大妞扎着羊角辫,二妞穿着小红袄,龙凤胎裹着同一条抱被,笑得没心没肺。 以前总觉得,把孩子留给前夫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罪,午夜梦回总听见他们哭着喊“妈妈”。可现在老张握着我的手说“要不咱们先养只猫吧?你要是喜欢,再养条狗”,我突然明白,有些失去不是因为我狠心,是因为那时候的我,只能用“放手”换他们一条更容易走的路。 汤喝到一半,老张手机响了,是他女儿打来的,小姑娘在那头喊“爸,周末我带男朋友回家吃饭”,老张笑着应“好啊,让你阿姨给你做糖醋排骨”。我看着他眼里的光,突然不抖了——原来婚姻不是非要生个孩子才算圆满,是有人看见你的疤,还愿意陪你把日子过成一碗热汤,烫嘴,却暖心。 窗外的天暗下来,路灯亮了,老张把我的碗添满,婚戒在灯光下闪了一下。我想,也许这次不用急着做决定,先把这碗汤喝完,把明天的菜买好,把日子一天一天过下去——孩子也好,猫狗也罢,只要身边这个人,愿意等我慢慢来,就够了。
离婚后男的后悔多还是女的后悔多?
【27评论】【10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