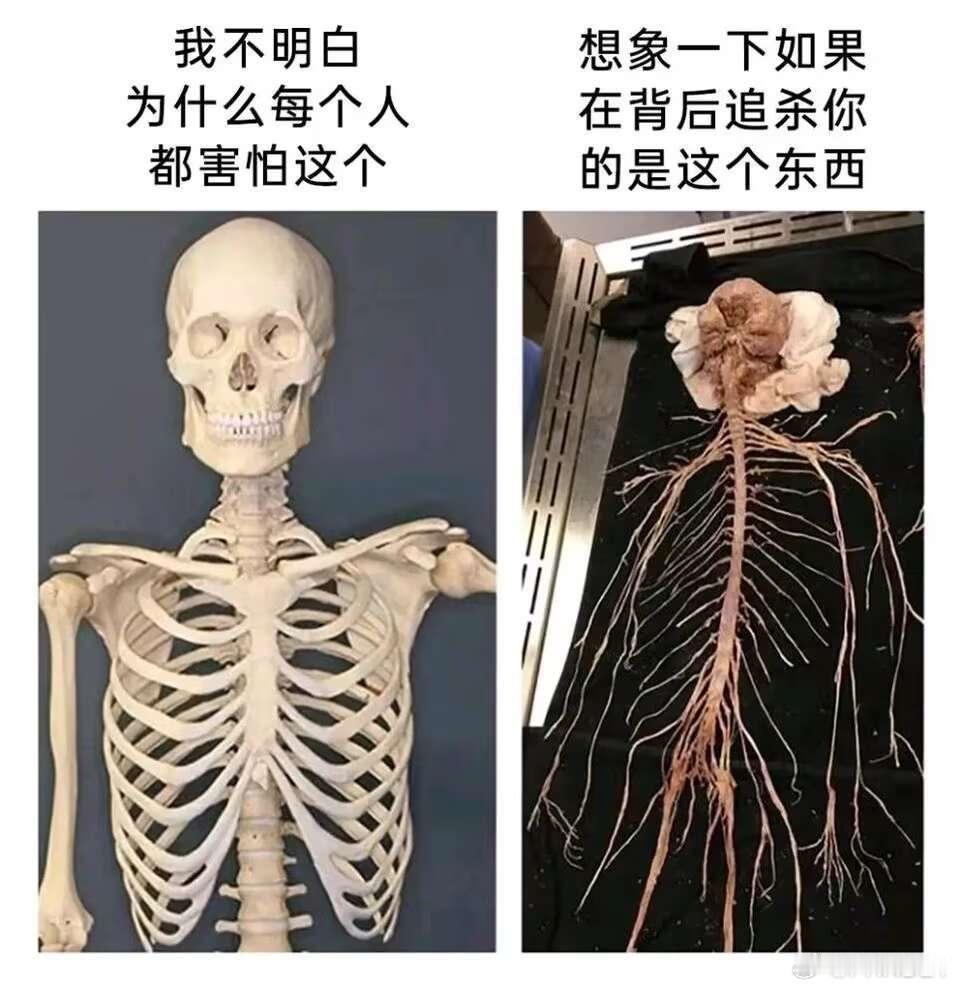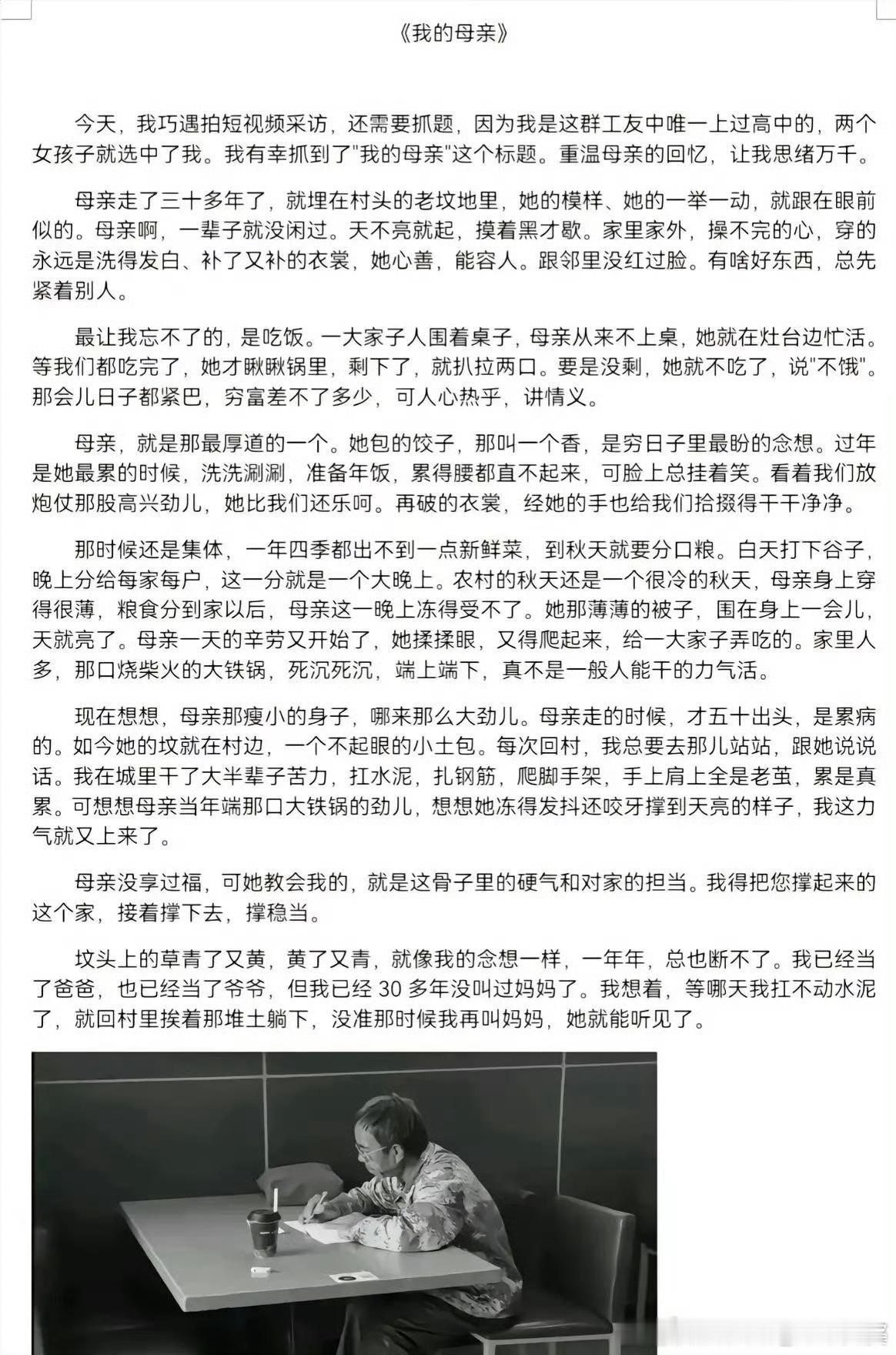1963年,陈广胜当了师长,听说老家那个拜过堂的媳妇秀兰还在,一个人拉扯着他走时还没出世的儿子,日子快过不下去了。 事情是从一份转过来的公函开始的。 1963年秋天,山东寿光县民政部门向部队发来一份协助核查优抚对象情况的公函。在名单里,有这样一行字:“刘秀兰,女,系你部陈广胜同志(1945年春外出参加革命)之妻,失联至今。现抚养一子,生活存在困难,未曾改嫁。” 陈广胜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到这份公函摘抄件的。 他当时刚开完作战训练会议,身上还带着训练场上的尘土。读完那几行字,他沉默了几分钟,对干部科的同志说:“情况属实。我写个报告。” 报告当晚就写好了,很简短,不超过一页纸。他陈述了1945年春天在家乡与刘秀兰按旧俗结婚,后因部队紧急转移失散的历史事实。也说明了1952年,经组织批准,与现任妻子(某军医)结婚,育有一女的现状。报告的最后,他写道:“关于原配刘秀兰及其子生活困难问题,我完全服从组织的调查与处理决定。” 组织上的调查是严谨而迅速的。 干部科通过军区,向地方发了正式的调查函。回函证实了刘秀兰的情况:她一直住在村里,靠种几亩薄田为生,独自抚养儿子陈寿光,生活贫困。村里和公社的证明都提到,她多次表示“男人是出去干革命的,我得等着”。 材料汇总到了师党委。王副政委代表组织找陈广胜谈了话。“老陈,要负责安置好刘秀兰母子的生活,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革命军人家属负责。”他话锋一转,“但前提是,你必须和你现在的爱人沟通好,取得她的理解和同意。家庭内部不能出问题,这也是组织原则。” 陈广胜的妻子是师医院的医生,当他把组织的公函、地方的证明和自己写的报告,都放在了她面前。 妻子沉默地看着那页纸,看了很久。她是知识分子,比很多人更明白那段历史的重量。 “你怎么想?”妻子问。 “人得接出来,不能让她再这么过。”陈广胜回答得很直接。 “接出来以后呢?”妻子的问题也很直接。 “按政策,由组织安置工作,生活上我会负责。孩子该上学上学,该工作工作。”陈广胜说,“我们……还是我们。” 这句话他说得很慢,但很清晰。 妻子又沉默了一会,最后说:“那就按政策和你的良心办吧。需要我这边出什么手续,我配合。” 事情在程序上开始推进。陈广胜打了正式报告,妻子写了情况说明。师里派了一名干事,带着路费和介绍信,去了山东寿光。 就这样,母子俩跟着干事,坐汽车,倒火车,辗转到了部队驻地。 陈广胜没有去车站接。他让后勤安排了临时宿舍,自己照常处理工作。直到晚上,他才过去。 宿舍里灯光有点暗,秀兰正在用一个小煤油炉下面条,儿子在一旁劈柴。看到他进来,两个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秀兰的衣服很旧,但干净,头发梳得整齐,只是脸上的皱纹又深又密。儿子长得确实像他,尤其是眉毛和鼻梁。 “路上辛苦了。”陈广胜先开口。 “哎,不辛苦,组织上照顾得好。”秀兰应了一句,声音有点干涩。她推了推儿子:“寿光,叫……叫首长。” 寿光憋红了脸,喉咙里咕噜了一下,最终也没发出声音,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后来,秀兰被安排到军办的一个被服厂工作,有了正式的工人身份和工资。寿光被送到部队的子弟中学插班,吃住都在学校。 厂里的女工们起初好奇,后来也习惯了。大家都知道刘秀兰是陈师长老家的亲人,具体什么关系,没人深究。秀兰干活勤快,从不提任何要求。寿光学习刻苦,后来考上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去了外地工厂。 陈广胜的家里,日子照旧。女儿慢慢长大,妻子工作忙碌。那张老家县里来的公函,和后续的安置报告,一起被锁进了他的档案袋。档案里“家庭成员”一栏,后来被谨慎地增加了两行。 1985年,陈广胜离休。整理办公室时,他从一堆旧文件中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就是当年那份关于安置刘秀兰母子的批复件。纸已经发黄变脆。他看了几秒,没有带走,把它和其他需要销毁的过期文件放在了一起。 这件事在当时师一级干部中,并非孤例。 战争造成的离散太多了,所以,责任和道义,在特殊的年代里,有时会呈现出非常具体甚至略显笨拙的模样,但那或许正是普通人面对历史尘埃时,所能抓住的最实在的东西。 文|灰度场 编辑|南风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