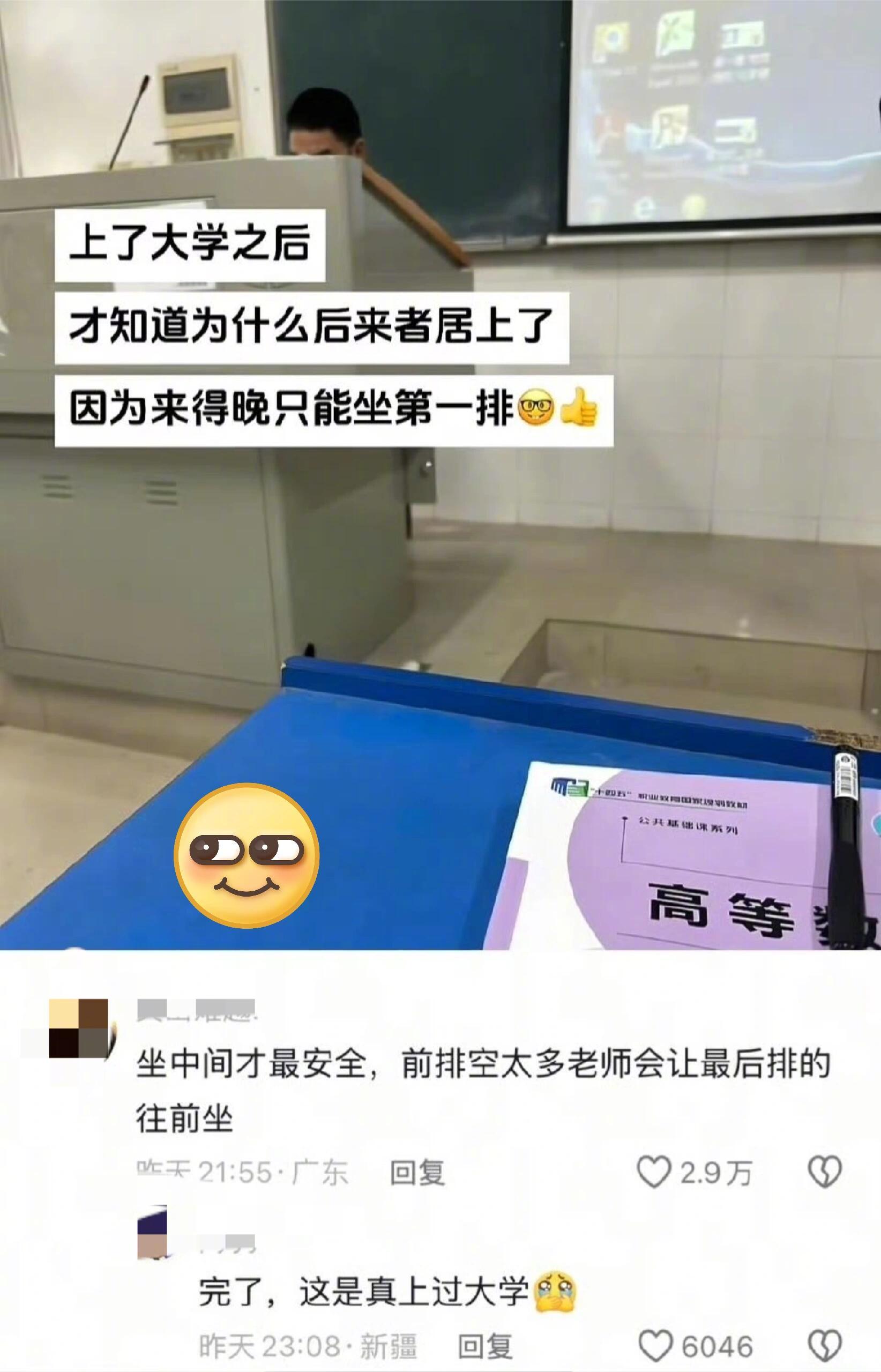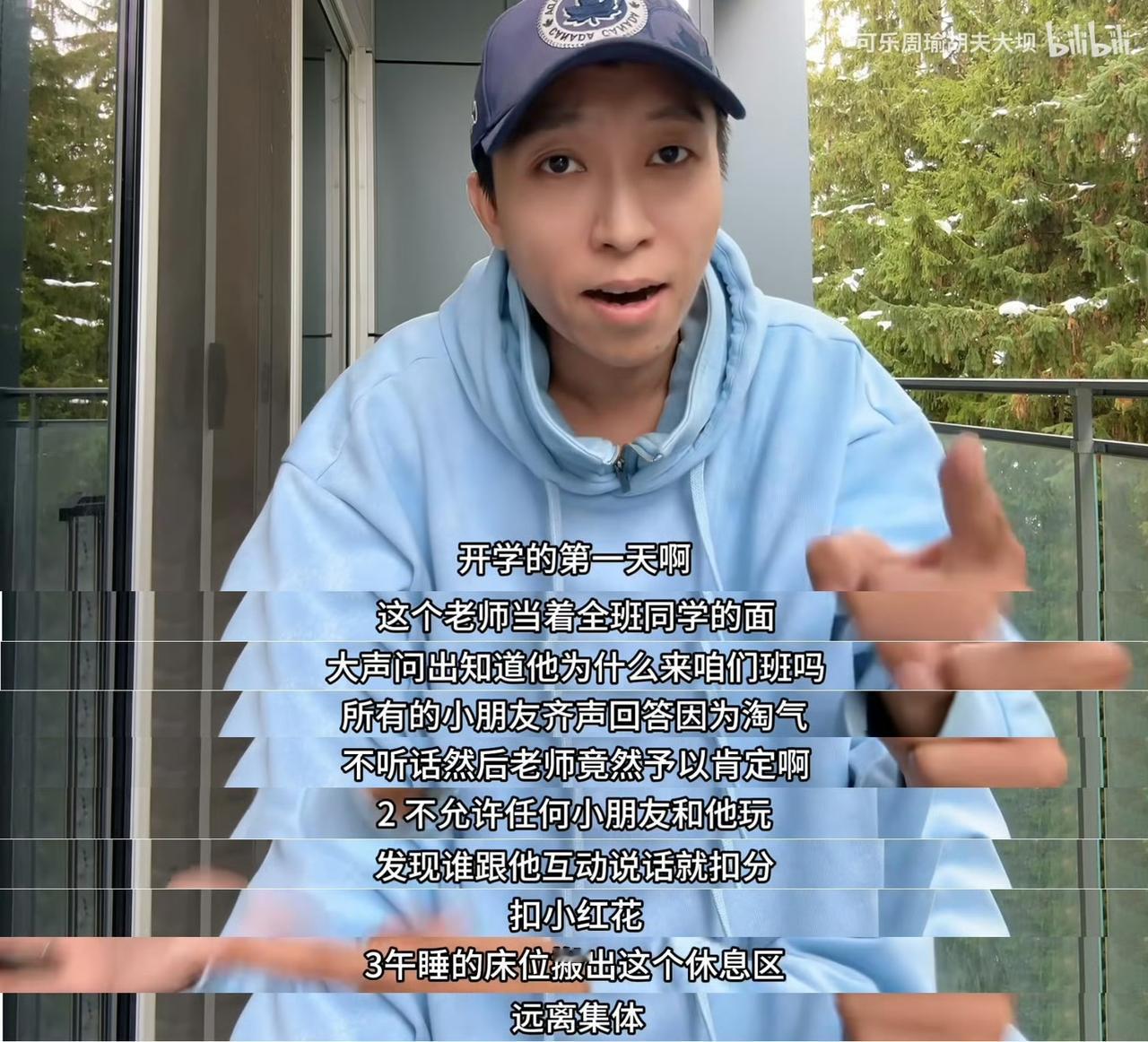非常现实扎心的话: “体制内有同病相怜的两个群体,那就是教师和医生。教师和医生处于体制内的底层或者基层,是典型的技术型人员。几乎就没有升职做官的空间,即便努力到了极限,也不过是一个学校的校长或者医院的院长。在体制的高墙内,教师与医生这两个群体,如同被困在精致围城里的匠人。他们手握专业知识,却常常在现实的重压下举步维艰。” 放学铃响过很久了,我还在办公室里批改作文。窗外下着雨,就像我此刻的心情。今天又被家长投诉了,因为我在课堂上讲了《红楼梦》里的爱情描写。"教坏孩子"这个罪名,像永远撕不掉的标签。 手机震动,是林医生发来的消息:"老地方?" "杏林茶馆"的老板娘已经认识我们。每周五晚上,我和林医生都会在这里碰面,像两个互相舔舐伤口的困兽。 林医生脱下白大褂,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今天又被投诉了,"他苦笑着,"就因为让家属多等了一会儿。" 我们同时叹气。他是县医院的内科主治医师,我是县一中的语文老师。在别人眼里,我们是体面的公职人员;实际上,我们都是戴着镣铐的舞者。 上周,林医生接诊了一个发烧的孩子。检查后确认是普通感冒,建议回家观察。孩子父亲当场拍桌子:"等了两个小时,就这?信不信我投诉你!" 第二天,投诉信就到了院长办公室。理由很奇葩:"医生不负责任,耽误病情。"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班上一个学生月考作弊,我按校规处理。家长直接冲进校长室:"我儿子从来不作弊!肯定是老师针对他!" 校长找我谈话:"家长是某局的科长,你处理事情要灵活些。" 林医生曾经有个升职机会。科室副主任的位置空出来,所有人都觉得非他莫属。最后上位的,却是一个资历远不如他、但"有关系"的年轻医生。 "技术好有什么用?"他自嘲,"在体制内,技术永远不如关系。" 我也深有体会。评高级职称时,教学成果不如一份"特殊贡献"。所谓特殊贡献,不过是帮领导写了篇发言稿。 最让我们寒心的是社会的误解。 患者觉得医生都想赚黑心钱,家长认为老师都在偷懒耍滑。没人看见林医生连续值班36小时后的黑眼圈,没人知道我为了备好一堂课查阅了多少资料。 有一次,林医生救治了一个车祸伤员。家属来时第一句话是:"要是治不好,我跟你们没完!" 我班上有个学生考上重点大学,家长在谢师宴上说:"主要还是孩子自己努力。" 但我们也曾有过高光时刻。 林医生说起他治愈的一个老人,每年春节都会给他送自家做的腊肉。"就挂在诊室门口,油汪汪的。"他眼里有光。 我也有这样的时刻。毕业多年的学生寄来明信片:"老师,您教的《逍遥游》,我现在终于懂了。" 这些微小的温暖,像寒夜里的星光,支撑着我们继续前行。 今晚的谈话特别沉重。 林医生说他们科室又走了一个年轻医生:"去医药公司了,薪水翻倍,还不用受气。" 我也有同事辞职去了培训机构:"课时费是现在的三倍,家长还客客气气。" 我们沉默地对饮。不是没想过离开,只是放不下。 "我女儿说长大也要当医生。"林医生突然说,"我居然不知道要不要支持她。" 我懂这种矛盾。就像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学生,教师这个职业有多崇高,又有多卑微。 走出茶馆时,雨停了。 林医生还要回医院查房,我也要回家准备明天的公开课。我们像两个即将奔赴不同战场的士兵,互相拍拍肩膀。 "保重。" "你也是。"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起大学时的理想。我想当个好老师,他想当个好医生。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是体制内最普通的技术人员,没有权力,没有资源,却还在固执地守着最初的那点念想。 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宿命。误解中坚守,在委屈中前行。就像夜雨里的路灯,不够明亮,但始终在那里,为需要的人留一束光。 远处,县医院的霓虹灯在夜色中格外醒目。我知道,林医生又要在值班室度过一个不眠之夜。而我的背包里,还有五十本作文等着批改。 这,就是我们的双城记。在两个不同的围城里,过着相似的人生。 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当下医疗环境,常常要求医生必须"总是治愈"。当患者带着不切实际的期待就医,当医患关系变成消费关系,医学的人文精神就会逐渐流失。 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教师和医生是社会的脊梁,却也是"沉默的大多数"。在行政权力面前,专业技术往往显得无力;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专业尊严常常被轻易践踏。 然而,正是这些默默坚守的专业技术人员,支撑着教育和医疗这两大民生基石。 庄子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更需要重新审视专业技术人员的价值。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官位,没有丰厚的财富,但他们用专业知识和职业操守,守护着社会的良心底线。 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理解,不仅是对个体的关怀,更是对专业精神的礼赞,对社会价值的重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