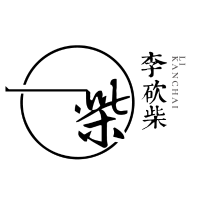时代的风向的确是变了。
北京时间,3月19日凌晨4点,一年一度的GTC盛会(GTC开发者大会)顺利召开。来自全球各地,近3万名前沿科技从业者,涌进加州圣何塞会议中心。
这是近年来死气沉沉的商海中,少有的盛况。
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黄仁勋,一身“千年不变”的皮衣登场。这一次,这个温和的东方面孔,怀揣宇宙最强GB200超级芯片,再次封神。
两年前,英伟达专为AI发布的H100,因性能强大被市场追逐到一“芯”难求。
如今这款由2080亿个晶体管组成,拥有每秒2亿次运算的双核4纳米芯片,运行能力是H100的30倍。它的出现,将AI的训练成本再度降低了75%。

AI飓风漫天刮起,GB200如大鹏之翼,将黄仁勋通往科技神坛的阶梯高高托起。
毫无疑问,黄仁勋已然成为乔布斯、马斯克之后,最耀眼的“超级符号”。GTC闭幕的当下,甚至有媒体称:
“全世界的CEO,都在争取一个见黄仁勋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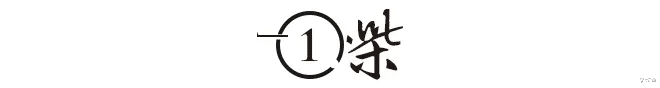
在此之前,圈外对这位美籍华裔的了解,更多来自财富值。
2月22日,英伟达发布了一份财报:
2024年首月,英伟达营收609亿美元,是2023总年收的近2.3倍。其中净收入298亿,同比增长581%。
发布当日,英伟达股价暴涨2770亿美元,创下华尔街历史最高单日涨幅。随后,世界半导体产业迎来了历史时刻。
2月23日,英伟达每股飙至800美元,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破2万亿美元的芯片公司。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10天后,英伟达又以2.13万亿美元市值,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公司,仅次于微软和苹果。3月7日,英伟达再度上涨4.47%,收于926.69美元,总市值高达2.32万亿。
有人做过不恰当的类比,如果把市值比作一个国家的GDP,英伟达排名仅次于美、中、德、日、印、英、法,位列全球第八。
截至2月底,黄仁勋个人身价也从一年前的140亿美元,瞬间飙至693亿。全球排名第21,已然站在山顶。
然而最初的黄仁勋并没有一个有迹可循的光明未来。

1963年,黄仁勋出生于台湾台南,父亲是一名化学工程师,母亲是小学教师。
那时,时局动荡。他先随父母搬到泰国,9岁时,又与哥哥一起被送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叔叔那里,开始了糟糕的童年生活。
叔叔马虎,给他们找了一所专为问题少年开办的寄宿学校。那里聚集着肯塔基州最底层的穷孩子,粗俗、暴躁、凶狠好斗。
留着长发,瘦弱矮小,又有着亚洲面孔的黄仁勋自然成了被欺负的对象。总有三五成群的小混蛋莫名冲过来,对他轮番羞辱,挨完揍,黄仁勋还要乖乖去打扫所有男厕所。
为了尽可能融入学校,他甚至学起了抽烟,但即便如此,日子也不好过。
好在刺头室友大字不识几个,黄仁勋想到一个办法,开始主动教他读书写字,校园生活才总算有了少许保障。
人生无数分岔口,直到父母到来,黄仁勋才终于安稳下来,并开始显露天赋。
喜爱乒乓球,他把自己打进全美排名。热爱计算机,就成了各种计算机和科学俱乐部成员。由于成绩优异,高中时他连跳两级,16岁进了俄勒冈州立大学电子工程系。

1984年,毕业后的黄仁勋先后去AMD和巨积(LSI Logic)做了工程师。但越做越觉得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于是,跑去斯坦福读电子工程硕士。
一直以来,黄仁勋毫不掩饰对巨积的喜爱。这家公司并不关心市场火热的CPU(中央处理器)开发,反而更专注当时无人看好的芯片图形处理。
在巨积做设计两年,黄仁勋主动要求调到销售部,很快成为部门总经理。
调动看似奇怪,对黄仁勋来说,却至关重要,跨职能的历练,重塑了他对行业的认知。
那时,计算机正快速发展,图形芯片才刚刚开始,黄仁勋阴差阳错的坐上了飞驰的列车,等待一个时机来临。

1993年,硅谷圣荷塞的一家名为丹尼的24小时连锁餐厅里,聚集了三个年轻人。
他们是来自斯坦福大学校园网的马拉科夫斯基(Chris Malachowsky)和普里姆(Curtis Priem),另一位则是黄仁勋。
自1992年开始,三个年轻人开始在这里频繁会面,讨论计算机的未来。
出于对游戏的喜爱,他们设想可以设计一种芯片,不但能加快游戏中图像处理速度,还能让效果更加逼真。
可是,当时CPU市场被AMD和微软牢牢控制,黄仁勋从来特立独行,他认为“世界不需再多一家CPU公司”。
于是,一个大胆的决定诞生——成立一家专门针对游戏主机的3D图形加速芯片开发公司。

为此,黄仁勋专门向专家请教,电话那头,对方皱着眉头回答:
“这个市场还没起步就已乱成一锅粥,市面上已经有二三十家同类公司,你最好别干这个。”
当时的圣荷塞,大半还是荒地。三人将丹尼餐厅作为办公室,一边喝着廉价咖啡,一边畅想着公司的未来,通常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
直到亲眼目睹隔壁银行被接连抢了好几次,几人这才意识到,这里可能不是理想的办公场所。连“NVIDIA”(英伟达)这个日后享誉业界的名字都来不及取,他们就搬了出去。

三人中黄仁勋年纪最小,却被任命为公司CEO,原因是他学得最快。
对于初创公司来说,第一件事是融资。好在前东家巨积的老板对黄仁勋赏识,于是,将好朋友红杉资本推荐给了这个年轻的CEO。
投资人耐着性子听完黄仁勋磕磕巴巴的讲解PPT,丢下200万美元,不耐烦地说:“虽然我并不想这么做,还是会给你钱。但如果你把我的钱赌输了,我会杀了你。”
那时,Windows尚属初代,电脑不能上网,CPU的处理速度也不是很快。市面上像样的游戏公司都没有几家,更别提游戏市场。
虽然是“0亿规模”,但目睹游戏成长,他坚信这个市场是一定存在的。他要做的,仅仅是创造最牛逼的产品,改变世界。

1995年,历经两年打磨,英伟达第一代3D图形芯片NV1终于上市。
这款产品独树一帜的采用了四边形成像技术,不但能处理图形,还能播放音乐,甚至插上操纵杆就是游戏机。
在当时,的确“前无古人”,相当出众。
只是,面对当时主流的三角形成像技术,他们独创的四边形显得格格不入,没人愿意为此付费。
来不及改变世界,英伟达刚迈出第一步,就因为资金消耗殆尽,站在了破产的边缘。
关键时刻,日本电玩公司世嘉看到了他们的潜力。他们正欲与老对头任天堂,掰一掰手腕。于是,揣着700万美元,让英伟达为他们量身打造一款秘密武器。
黎明在即,意外还是发生了。
当时,微软开发出了基于Windows 95的Direct 3D技术。他们宣称,这种技术将只支持三角形图形芯片接口。
这就意味着,坚持四边形的英伟达,注定要为自己的一意孤行付出代价。即便开发出产品,也注定与Windows不兼容。如果不开发,数十万片显卡,将变成废品。
“无论如何,都会面临倒闭的命运。”
黄仁勋只能硬着头皮去找世嘉,他坦诚因自己的错误,芯片已没有继续开发的必要,但还是希望对方能按合同付款。尽管,这个要求让他无比尴尬。
没想到,世嘉竟然答应了。

这件事成为黄仁勋创业路上最深刻的教训,一次“充满羞辱的失败”。
为了生存,黄仁勋将100多人的公司缩减至30多人。即便如此,手上的资金也只够英伟达再坚持六个月。
左右都是死,黄仁勋选择了一种更激进的应对方式。他把公司剩余资金全部押在了一款未经测试的芯片上。
“成功和失败的概率五五开,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倒闭了。”

1997年,就在英伟达账上只够再发一个月的工资时,Riva128诞生了。这款产品不但支持Windows最新标准,速度更是竞品的数倍。
上市四个月,Riva128一骑绝尘,卖掉100万片。
这一年,黄仁勋接到了张忠谋的电话,芯片业两颗明珠聚首,瞬间达成共识:往后英伟达尽可以专注于芯片设计,生产问题放心交给台积电。
之后,随着性能强大的TNT、TNT2陆续推出,竞争对手纷纷被挑落马下,英伟达终于在芯片市场站稳了脚跟。
1999年底,公司上市不久后,黄仁勋出人意料地推出了一款全新架构的显卡芯片——GeForce256,并将其称为GPU。
新世界的大门,“哗”一下打开。

GPU自问世以来,对处理器芯片的冲击就没停止过。
相比统治计算机世界多年的CPU,GPU最大的优势是速度。CPU一个接一个地串行处理任务,而GPU别具一格的并行架构,可以同时处理大量琐碎信息。
这就如同一条宽阔的单车道,和一面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的区别。
不仅如此,硬件层面上,GPU既能能显示更清晰的视频、更华丽逼真的游戏特效,还能处理复杂的3D计算问题。
简单来说,GPU彻底改变了计算机图形学,将处理器芯片,带进了加速计算时代。黄仁勋信心无比:
“创新无止境,有显示器和像素的地方,就有英伟达的增长机会。”
事实证明,黄仁勋还是低估了GPU的威力。
2000年,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图形学研究生Ian Buck,为了更好的体验游戏《雷神之锤》,将32块GeForce显卡连接在一起,动用8台投影仪,打造了世界上第一台8K分辨率游戏机。
GeForce显卡强大的性能,让Ian Buck非常吃惊。于是,他黑进了GeForce中带有原始编程功能的“着色器”,通过其特有的并行计算电路,组合出了一台低成本的超级计算机。
几个月后,Ian Buck成为英伟达的员工。

这让黄仁勋意识到,如此强大的芯片如果只用作显卡,就太浪费了。
2006年,在黄仁勋的主导下,CUDA架构应运而生。
简单来说,哪怕普通程序员,通过现有的编程语言,只需一台配备GPU的笔记本电脑,就能实现软件开发。
不但能处理图形,也能高效进行数据运算。
黄仁勋向来果决,他坚信世界即将改变,随即发出指令:“要让CUDA能在每一张GeForce上工作,让超级计算平民化。”

改变世界并不那么容易。
黄仁勋立志将超级计算机带给大众,5年用掉5.6亿美金,但大众对此毫无兴趣。
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很长一段时间,黄仁勋只能将他们卖给分子动力、天气模拟等,狭窄又不赚钱的科学计算领域。
为了寻求买家,他甚至找到通用磨坊,利用CUDA帮他们模拟冷冻披萨的热物理过程。
媒体时不时发出嘲讽:“花费数十亿美元、瞄准的却是学术和科学计算,这个不起眼的角落。”
市场的冷淡直接反应在股价上。那段时间,英伟达市值一直徘徊在10亿美元上下,到2008年底,股价暴跌70%。
投资人坐不住了,他们要求黄仁勋改变策略,赚钱才是硬道理。黄仁勋不为所动,他相信加速运算时代,终会到来。
只是没想到,他所主导的CUDA,日后竟成为一条宽广的护城河,引领英伟达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2009年,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写邮件给英伟达:
“听着,我刚刚告诉一千名机器学习研究人员应该去买英伟达显卡,你们能免费送我一块吗?”
英伟达给出答复:“NO 。”
如果,当时英伟达知道不久的将来辛顿将会被称为“Ai教父”,他们肯定会收回这个草率的回答。
原来,辛顿的科研小组一直在使用CUDA平台训练计算机神经网络(受人脑启发的计算结构),CUDA的强大,让他倍感惊讶。
虽然遭到拒绝,他仍继续带着两名学生亚历克斯和伊尔亚,坚持用两块GeForce训练模型。
三年后,亚历克斯带着他的神作——AlexNet(视觉识别神经网络),参加了当年的ImageNet大赛。随着AlexNet横扫一众计算机天才,拿下比赛冠军,深度学习卷积网络模型正式诞生。

事实上,早些时候,谷歌曾训练了一个神经网络,成功从1000万张图片中,成功识别出一只猫。
但耗资100万美元,集结1000台电脑、16000个CPU,并不被业界看好。
而AlexNet里程碑式的成果,仅用了2块GeForce。英伟达专用GPU,简直就是为训练神经网络量身打造的,速度是通用CPU的百倍不止。
多年近乎偏执的坚持,在这一刻得到验证,黄仁勋倍感欣喜:神经网络将彻底改变世界。
随即,他在公司内部邮件中宣布:
“一切都将进入深度学习阶段,从此之后,我们不再只是一家图形计算公司了。”
为此,他们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果断退出了诱惑巨大的手机移动硬件芯片市。
“因为我们知道,英伟达的使命,是创造出普通电脑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计算机。”
黄仁勋坚定的走在加速算法的道路上,等待一场变革到来。
这一年,黄仁勋亲自为成立不久的OpenAI,送去了世界上第一台DGX-1超级计算机。那里聚集着山姆·奥特曼、伊尔亚等大批AI领域的天才。
负责开箱的,正是时任董事长的马斯克。

2017年,谷歌推出了Transformer架构。这种可以“联系上下文”的技术,为AI的发展提供了跳板。次年,OpenAI使用它构建了第一个“生成式预训练Transformer”。
2020年的GTC大会上,英伟达发布了基于全新架构的DGX A100,一口气打破了16项性能纪录,速度是上一代产品的4.2倍。
这款“神器”,一经发布就引起轰动,各大公司纷纷抢夺,很快供不应求。

之后,黄仁勋特地搞了一场直播秀。他从自家烤箱中搬出一块超大个的DGX A100,顽皮地打趣:“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显卡!”
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
其强大的语言理解和文本生成能力,彻底颠覆了人类对人工智能的认知。随后,多模态、大模型等各种技术纷纷在全世界涌现。
所有人都明白,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启。而这个新世界,是用一颗芯片驱动的。

如今,在黄仁勋的带领下,英伟达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公司,高达90%的产品份额,几乎垄断了整个AI芯片市场。
进入2万亿市值,成为全球第三大公司的当下,所有人都在争相传颂英伟达的巨大成功。
而被黄仁勋反复提及的,却是那些曾经的“挣扎”。
面对充满确定性的手机移动市场,他选择转身而去,义无反顾地去死磕并前途并不明朗的AI技术;CUDA研发,公司利润大受打击,他扛下所有质疑;创业之初,那个将公司置于绝境的不兼容“三角形”,让他饱尝苦果。
或许是“胜利”太过苦涩,他将位于加州的总部大楼建成三角的形状,就连沙发、地毯,都是三角形的缩影。
时间走过30年,当初的磨难变得平淡。
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如果当时就知道英伟达会成为今天的样子,还会不会创办这家公司,黄仁勋大笑:
“开什么玩笑?我为此几乎牺牲掉了一切!”
-END-
参考资料:
阿尔法公社:《创业27年,黄仁勋终于打败了英特尔》
格上财富:《英伟达创业史》
新智元:《英伟达GPU一战成神:黄仁勋押注人工智能,建起万亿美元显卡帝国》
作者:后风
编辑:柳叶叨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