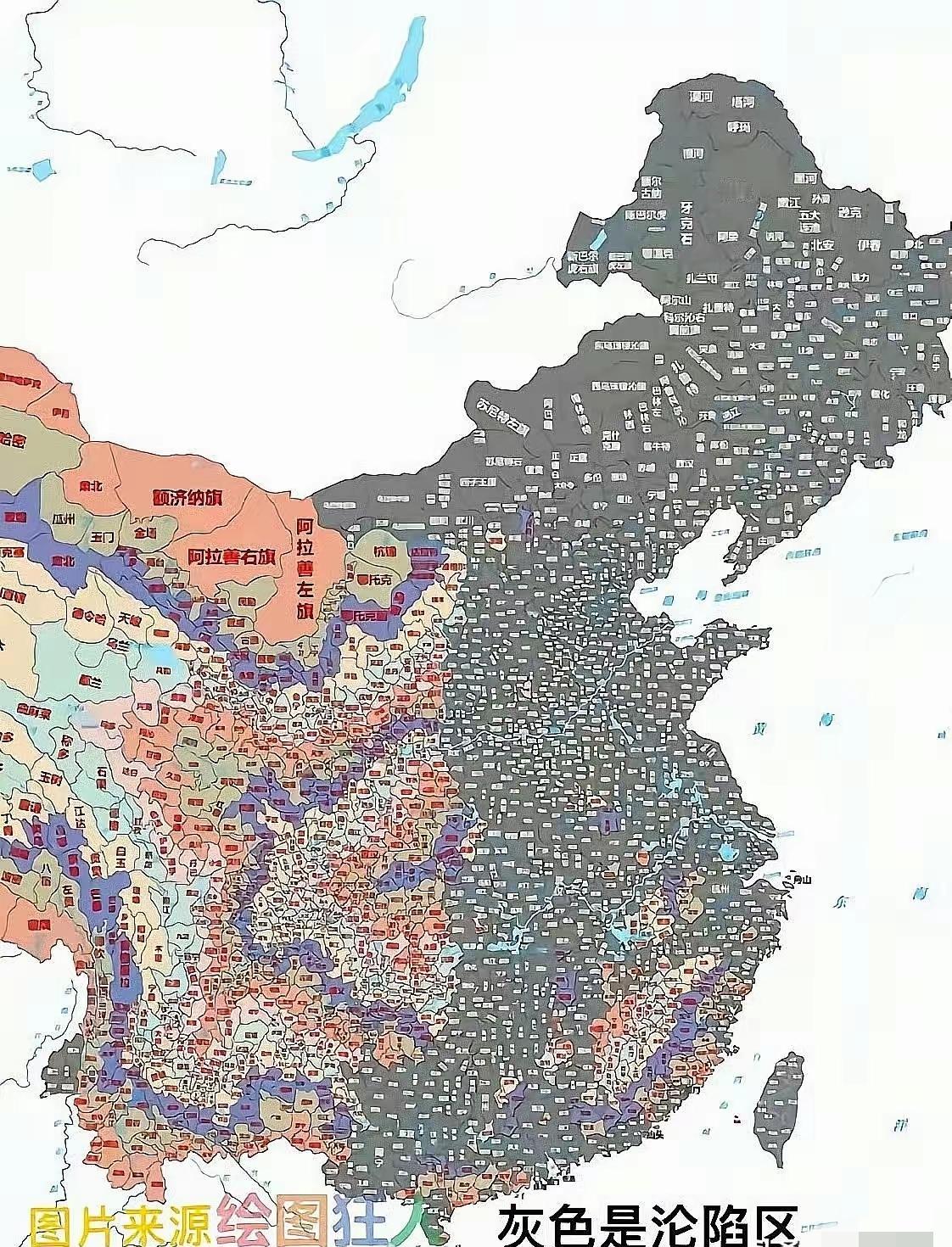1936年,刘亚楼的警卫员不慎落到了敌人手中,被敌人吊在树上打,一老汉瞅见后,黑着脸,上去就给了他一个耳光子:“兔崽子,竟敢偷我的钱!” 1934年10月的于都河畔,红军队伍正有序集结待渡,人群里,一抹亮眼的红格外醒目。 身着红衣衫的春秀拨开送行的人潮,脚步急促却又带着几分羞怯,逢着红军战士便问:“有没有见过刘亚楼政委的警卫员谢志坚?” 她要找的人,是后天就要和她拜堂成亲的未婚夫,可战火不等人,队伍马上就要开拔。 终于,在红军战士的指引下,她见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谢志坚正站在沙丘上张望,瞥见春秀的瞬间,他立刻跳下沙丘攥住她的手,语气里满是笃定:“放心,红军很快就回来,到时候咱们就结婚。” 春秀用力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双草鞋塞进他掌心,那是她连夜赶做的,针脚里缝着不舍与期盼。 谢志坚握紧草鞋踏上浮桥,回身挥了挥手,身影很快融入西进的队伍,成了春秀眼中望不穿的远方。 这一别,便是两年辗转,1936年9月,甘肃通渭、静宁一带的战场上,手雷的巨响划破天际,谢志坚被弹片击中,重伤昏迷了数日几夜。 刘亚楼守在他身边,看着昔日机敏的警卫员气息奄奄,心疼得红了眼眶。 他知道,再让谢志坚跟着部队长途跋涉,无异于送死,当即决定安排他留在静宁养伤。 临行前,刘亚楼拍着他的肩膀,语气带着命令也藏着牵挂:“你小子必须活下来,将来还得给我当警卫员。” 躺在担架上的谢志坚,泪水顺着眼角滑落,模糊了战友们远去的背影。 担架把谢志坚抬到了静宁的苟家村,一户姓苟的人家收留了他。 灯光下,苟大爷和女儿山花凑到跟前,二话不说就把他抬上炕,端汤喂药、擦洗换药,悉心照料着这个素不相识的红军战士。 日子一天天过去,谢志坚的身体渐渐好转,可心里的归队念头越来越强烈。 他对着苟大爷和山花深深鞠躬,哽咽着说:“我要去找队伍。” 苟家父女拗不过他,只好为他收拾行装,悄悄在他口袋里塞了个布团,里面是几块沉甸甸的银元。 没想到,刚走到山脚下,谢志坚就被一队国民党兵拦住,行装被翻查时,那几块银元露了出来,士兵们疑心更重,押着他往西边走。 瘸腿的士兵走得累了,指着前方的村子说要找口吃的,谢志坚抬头一看,竟然又回到了苟家村。 国民党兵闯进一户石院,屋里走出的壮汉看到被押的谢志坚,当即愣在原地,借口抓鸡悄悄溜了出去。 不一会儿,苟大爷搬着一坛酒,山花攥着一只大公鸡走进院子。 看到谢志坚的被敌人吊在树上打,苟大爷脸色一沉,放下酒坛上前就给了他一个耳光,对着国民党兵拱手说道: “老总,这是我女婿,没本事还想出去做生意,偷了我的袁大头跑了,幸亏你们把他带回来。” 山花也急着帮腔:“他是我男人,不是什么兵。”苟大爷又掏出几块大洋塞进士兵手里,大个子兵掂着银元笑了,连说误会,带着手下离开了村子。 危机刚过,党组织负责人就悄悄找上门,告诉谢志坚,国民党正在四处搜查掉队红军,县委要求大家就地参加革命,不能再外出找队伍。 苟大爷坐在炕头抽了半晌烟,突然哈哈一笑:“志坚,你就留下来吧,风声这么紧,落户结婚才安全,我把山花嫁给你。” 山花看着谢志坚,眼里满是柔情: “志坚哥,不能让你丢了性命,我听爹的。你给春秀姐写了好几封信都没回音,许是她已经嫁人了,要是往后她还等着你,你就别要我,我说话算话。” 就这样,江西老表谢志坚,成了大西北苟家村的女婿,把对春秀的思念藏进心底,在当地扎下根开展革命工作。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51年春日,山河早已换了人间,谢志坚带着一个沉甸甸的行囊回到家乡,行囊里,是那双珍藏了十七年的草鞋。 他迫不及待地赶到春秀家,春秀妈从屋里走出来,头发已经全白了,谢志坚快步上前握住老人的手,声音颤抖:“阿妈,我是谢志坚,我回来了。” 老人眯着眼睛端详了许久,突然老泪纵横,哽咽着说:“你回来了,可春秀没了,早就没了。” 这句话像重锤砸在谢志坚心上,他身子一歪差点跌倒。 老人哭着诉说:“你走后没多久,春秀就参加了革命,后来白狗子来了,杀了好多人,春秀临死前还一直喊着你的名字。” “她一直盼着你回来,不知道为你打了多少双黄麻草鞋,都整整齐齐收着,等着给你穿。” 谢志坚再也忍不住,抱着老人放声大哭,17年的期盼与牵挂,最终化作一场迟到的告别。 那双小小的草鞋,是这段烽火情缘最沉默也最有力的见证。 它起初是春秀与谢志坚未竟婚约的信物,仓促送别时的匆匆一塞,藏着少女最纯粹的爱恋与等待。 苟大爷父女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红军,主动促成婚事,那是百姓对红军的信任与支持。 烽火岁月里的爱情,以草鞋为证,以山河为媒。 【评论区聊聊】看到这样一段跨越山河与岁月的烽火情缘,你是什么感受? (信源:刘亚楼警卫员的爱情悲歌——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