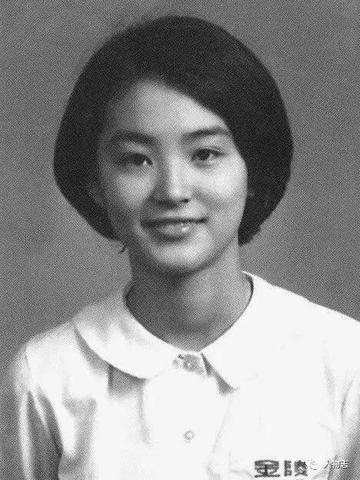1949年,全国解放后,廖汉生想把女儿女婿接进城,女婿进城前,同乡人却对他说:“不能去,你是穷农民,去了就把你杀了!” 这句话在村里传开时,没有人觉得奇怪,那是五十年代初的农村,很多人刚刚从长期的战乱中走出来,心里对“城里”这两个字既陌生又害怕。 对他们而言,城里人穿制服、讲政策、说话他们听不懂,有人说城里有规矩,进了城,穷人就活不下去,那种恐惧不是编出来的,而是长年贫困留下的印象。 在这样的认知下,当有人听说廖汉生要接女儿女婿进城时,村民们都在劝阻,他们觉得那样的生活不是他们能适应的,农民习惯了土地,习惯了靠双手吃饭,突然离开,反而像是去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 廖汉生出身桑植,家境贫苦,十六岁那年,他参加了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那时的桑植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核心之一,许多年轻人背上行囊离家,他也在其中。 从红军时期起,他跟随部队转战南北,长征路上,他多次负伤仍坚持行军,后来在陕北整编,他成为红二方面军的重要指挥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部奔赴华中,与日军多次交锋,解放战争时期,他又调任西北野战军,参与攻占兰州的战役,到1949年,他已是共和国的高级将领。 在那个年代,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却不知道他的家,他出身的那片山乡,依然贫穷,信息闭塞,村民们只在广播里听到他的事迹,对他们来说,这个走出大山的将军,已经离开了他们的世界。 战争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打碎了他的家庭,红军长征前夕,敌军反扑,廖汉生被命令随队转移,妻子肖艮艮和女儿廖春莲留在家乡。 部队走后,当地形势骤变,国民党军队进村搜捕,许多红军家属被抓,几个月后,他收到消息,说妻子遇害,女儿下落不明。 那一年,他还不到二十岁,消息传到部队,他没有哭,也没有再提家里的事,从那以后,他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战场,延安时期,他与白林成婚,开始新的生活。 多年后,当他已是共和国将军,忽然收到一封从湖南寄来的信,信是老乡写的,说有人在外地见过他的前妻,还提到一个名叫廖春莲的女子,自称是他的女儿。 那封信让他沉默许久,二十多年,他以为那段过往早已尘封,可现在,一切又被翻开,经过多方确认,他终于知道,妻子当年被人卖到外地改嫁,女儿则被留在桑植,在村里长大。 他没有怨恨,只想见女儿一面,他托地方政府帮忙联系,几个月后得到了女儿的消息,她已结婚,在村里务农,听说要被接进城,她没有答应。 村民劝她丈夫,说“进城会惹祸”,有人觉得那是政治陷阱,也有人觉得那是命不相配,廖汉生知道这些话,但没有责怪任何人。 他理解农民的顾虑,自己也是从那片土地走出来的,知道贫穷能让人多么谨慎,他只通过干部转达一句话:希望她来,他会照顾她。 女儿没有动身,她对这个父亲没有记忆,也没有信任,她的童年靠母亲和乡邻抚养,在最艰苦的年代,吃不饱、穿不暖,她知道“廖汉生”这个名字,却从没想过那是自己的父亲。 她觉得,他已经是国家的功臣,而自己只是个普通农妇,她害怕进城,也不想让丈夫被人看不起,她宁愿留在地里干活,也不愿去接受那种陌生的生活。 廖汉生得知后,没有再提这件事,他只是让人送去一些生活用品,叮嘱地方干部好好照顾他们一家。 多年过去,事情似乎被放下,直到1979年,他终于决定回乡,那时他已经退居二线,身体不好,地方政府得知消息,准备隆重接待,他却只提出一个要求:去女儿家。 那天,他带着白林,一行人来到桑植的山村,汽车停在村口,他亲自下车步行进去,女儿家门口很简陋,屋外晾着刚洗的衣服,廖汉生敲门,门被打开。 母女相认那年,他六十八岁,女儿已年过四十,她看到父亲,只愣了一下,没有说话,转身回屋,他没有追问,也没有强求,进屋后,他在木桌旁坐下,吃了女儿做的一顿饭。 他告诉随行的干部,不去县里开会,也不去参加宴席,就在女儿家吃饭,就是回家的意义, 那顿饭持续了很久,饭后,他叮嘱几句,离开了。 那次之后,父女之间没有再有更多往来,廖汉生回到北京,继续他的工作,女儿依旧在村里种田,她的丈夫仍旧不愿离开,说自己一辈子是农民,不懂城里的事。 他们的生活很普通,没因为亲属关系而改变,廖汉生也从未利用权力为他们谋私,他对外只说女儿身体健康,一切安好。 晚年时,他偶尔提起家乡,每次都说那里好,人淳朴,土地养人,他从不炫耀功勋,也不谈苦难,对他来说,最难启齿的不是战争的伤疤,而是家人的疏远。 去世前,他交代不举办隆重葬礼,也不要将骨灰带回家乡,他说,那里埋着太多战友,女儿后来仍然生活在村里,她的孩子长大后,外出读书,村里有人问起她父亲,她只说,他是打仗的人。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