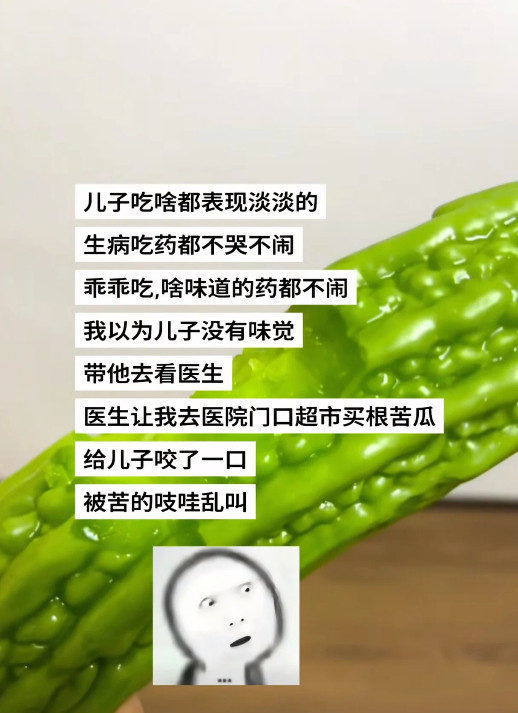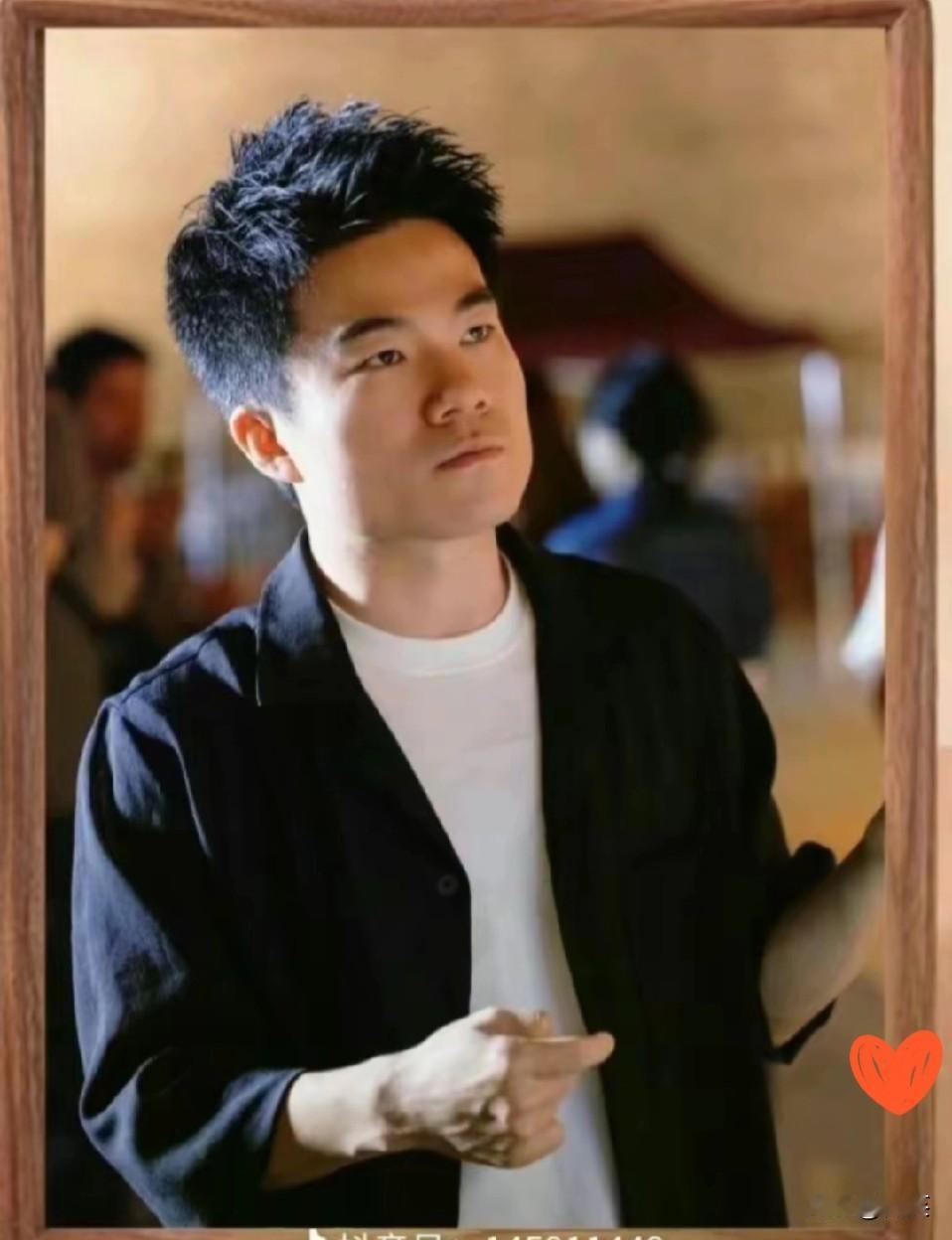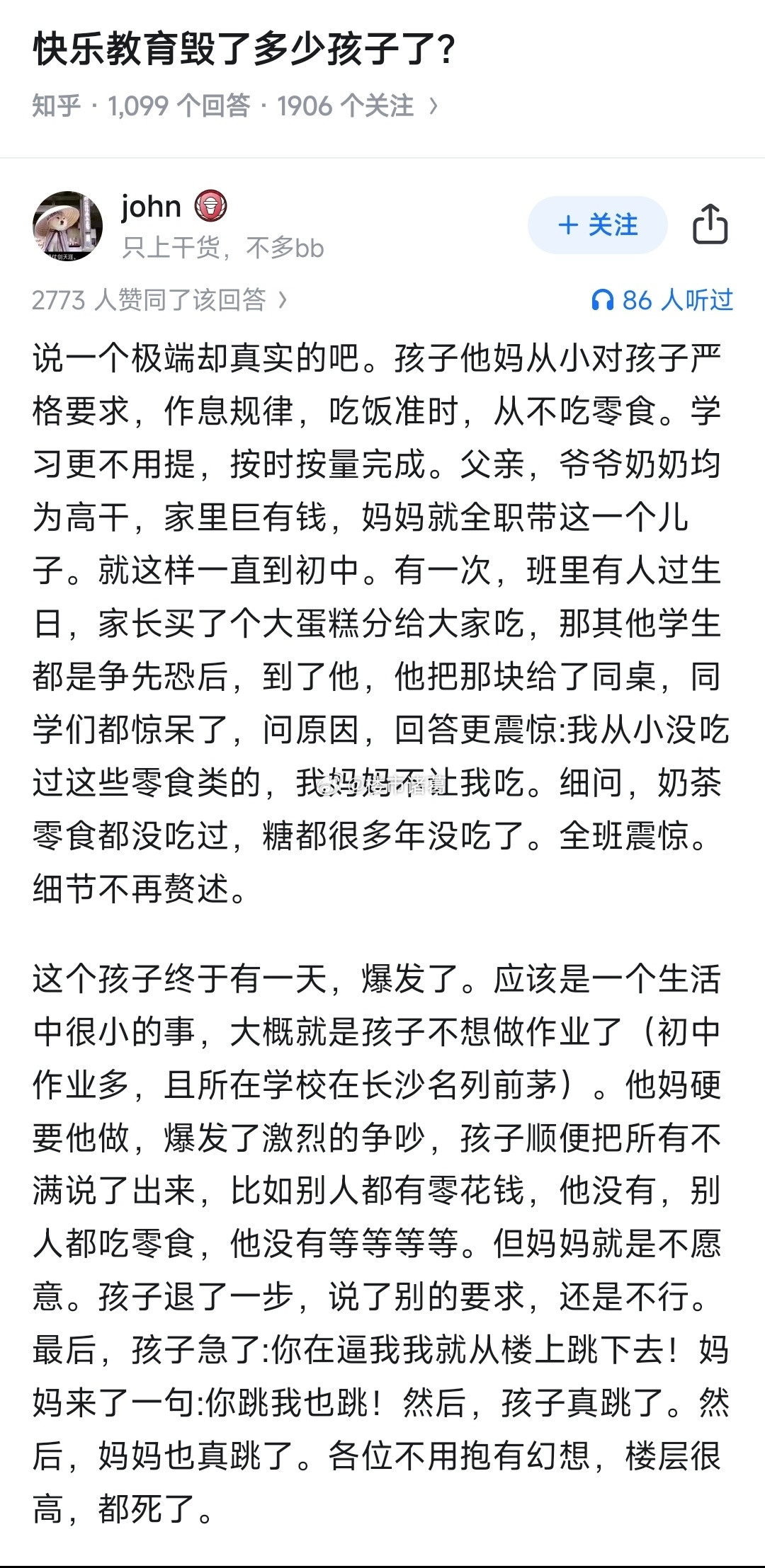永远不要过度操心你的孩子和你的父母,你所有的操心基本上都是徒劳。经营好自己,才是你一生的使命! 有次母亲摔伤了,我正为儿子填报高考志愿。医院、学校、家,三个坐标撕扯着我四十七岁的人生。凌晨三点,我在病房陪护床上修改儿子的志愿表,母亲在睡梦中呻吟,而我鬓角新生的白发在手机屏幕反光里格外刺眼。 “妈,你必须吃这个药。”我扶起母亲,把降压药递到她嘴边。她却固执地摇头,像极了我儿子拒绝穿秋裤时的样子。 “太苦了。”八十二岁的母亲嘟囔着。 “良药苦口。”我说着三十年前她对我说过的话。 这种角色的颠倒让我恍惚。曾几何时,我是那个被操心的人,现在却成了操心的主角。 儿子高三那年,我研究了全国所有985大学的优势专业,整理出三大本笔记。可他偷偷报考了美术学院,录取通知书寄到家时,我气得三天没和他说话。 “妈,你画的向日葵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七岁那年,他举着蜡笔画这样对我说。可我那时忙于比较哪个辅导班更能提高数学成绩,忽略了他眼里的光。 直到在他大二的个人画展上,我看到那幅《母亲的时光》——画里的我站在医院、厨房和学校门口,每一个我都眉头紧锁,身后是用日历纸拼成的翅膀。 “妈,”儿子扶着我的肩膀,“你看,你把日子过成了倒计时,可我的画展主题是‘无限’。” 医院走廊里,主治医生是我小学同学。他看着母亲的各种检查报告,轻轻说:“老人就像熟透的果子,你接不住她终将落下的宿命。” 这话让我想起父亲临终前,曾拉着我的手说:“丫头,风筝线抓得太紧,要么线断,要么风筝永远飞不高。” 母亲出院后,我减少了去她那里的次数。起初充满负罪感,直到发现她用我不在的时间学会了视频通话,还在老年大学交到了新棋友。 更让我惊讶的是儿子。当我停止每天三个问候电话后,他反而会在深夜发来消息:“妈,今天画廊签约了。”“妈,这幅画被收藏了。” 原来,我所谓的爱,成了他们的枷锁。 我开始把时间花在四十七岁才爱上的水彩画上。老师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她说:“姐姐,你总想把每片花瓣都画得完美,可你看,这些不小心滴落的蓝色,多像天空的眼泪。” 我在画室里认识了退休的舞蹈老师、改行的程序员、癌症康复的阿姨。我们不再是谁的母亲、谁的女儿,只是颜色的囚徒,在画布里寻找走失多年的自己。 上个月母亲生日,我送给她一本自己装订的画册。第一页是她坐在窗边梳头的背影,最后一页是儿子画展的请柬。 “这是什么?”母亲问。 “这是我的时间,”我说,“从前都给了别人,现在想留一点给自己。” 母亲戴上老花镜,一页页地翻。翻到中间时,她停下来,指着那幅《药》:“其实那个药,我是嫌贵。” 我愣住了。我一直以为她在无理取闹,却不知她是以自己的方式在替儿子操心。 昨天,儿子从威尼斯双年展寄来明信片,背面写着:“妈,这里的向日葵会跟着太阳转圈。” 我把它贴在画室墙上,旁边是母亲用毛笔写的四个字——儿孙自有儿孙福。 今天清晨,我在公园写生。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经过,车把上挂着手提电脑,她一边哄孩子一边接电话。我仿佛看见二十年前的自己。 我递给她一张速写:“送给你,今天的你。” 画里,她头顶开着三朵花——一朵含苞,一朵盛放,一朵已结成果实。 她看了很久,眼泪突然涌出:“我已经忘记自己长什么样了。” 夕阳西下时,我收拾画具。远处,母亲正和她的棋友道别,儿子发来布展现场的照片。而我在调色盘里调出了前所未有的颜色——既不是母亲喜欢的红色,也不是儿子喜欢的蓝色,是独属于我的,四十七岁的新生。 原来,最好的爱不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而是先成为自己的光。当你明亮,自然能照亮前路,也让同行的人看清他们的方向。 世间万物,各有时节。我终于懂得,我不是他们的摆渡人,我只是在渡他们的同时,渡我这一生的修行。 有句话说:“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首先你要成为那样的人。” 一个乐观、积极、不断成长的父母,本身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你活出了精彩,孩子便学到了“如何精彩地活”。 北大教授吴飞提到过一个观点: “过日子就是管理家庭,并在管理家庭的过程中,安顿自己的生活。只有自己所在的家庭整体过得好了,一个人才谈得上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过上好日子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 父母的使命,是成为孩子坚实的港湾,而不是他永远的舵手。 幸福是一种能力,而非结果。当你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充满热情和乐趣时,你就在潜移默化中,将这种最宝贵的能力传递给了孩子。 当你专注于经营自己,你便不再是孩子的“管理者”,而是成为了他的“灯塔”。你照亮的是他前行的方向,而不是替他走完每一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