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不知怎么的,都在悄悄断联,不走亲戚,不串门,连老朋友也懒得搭理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越来越仅存在于手机里。离了手机,关系就断了。现实冷酷,人情冷漠,不联系,真的会疏远;不沟通,真的会变淡。 我把家族群聊设置成了免打扰。上一次有消息,还是三个月前表妹发的孩子满月照,再往前翻,是堂哥转发的养生链接。手机屏幕像一口渐渐干涸的井,偶尔落下的石子,也激不起多少回声。 昨天母亲在电话里叹气:“你刘姨搬新家,请客只来了两桌人。”我握着话筒,想起小时候,刘姨家包一次饺子能喊来半条巷子的人。如今连道贺都变成了微信里那个千篇一律的“🎉”表情。 这种静默的告别,在我身上早有征兆。 去年冬天,发小阿杰驱车三小时从省城回来。我们坐在中学门口的奶茶店里,他兴奋地说着融资、上市,我低头搅拌那杯二十八元的杨枝甘露——这价钱够买我们当年喝一个月的汽水。他突然停下来,望着窗外崭新的教学楼:“还记得我们逃课去河边钓鱼吗?” 我记得。但我更记得,去年父亲住院我在朋友圈求助时,他点了赞,却忘了我们曾经滴血为盟说“有难同当”。 最让我心惊的是今年春节。按老家规矩,初二是“走舅家”的日子。我提着礼物站在大舅家门口,防盗门上的猫眼像一只冰冷的独眼。门开了,表嫂接过礼品袋时的客气,像酒店前台:“进来坐呀?”我看着玄关处摆放整齐的拖鞋,突然想起小时候我们直接穿着泥鞋冲进厨房偷吃炸带鱼。 那顿饭,大家围着圆桌,各自盯着手机。家族群里的红包,比桌上的菜更让人激动。大舅几次想说说家族旧事,刚起头就被表姐用“爸你又说这些”打断。临走时,表嫂把我们用过的茶杯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回家路上,母亲喃喃:“以前送客要送到村口,现在送到门口都嫌远。”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在城里996的我,早已耗尽了所有社交能量。每次回老家,亲戚们的“关心”像一场无形的考核:“一个月挣多少?”“什么时候买房?”“怎么还不要孩子?”他们不知道,我租的公寓隔壁,住着同样三年没回老家的湖南小伙。 上周整理旧物,翻出一本1998年的挂历。背面是父亲记的礼账:“三月初六,王二叔嫁女,送暖瓶一对。”“腊月二十,李婶添孙,送小米二十斤。”那些密密麻麻的人情往来,如今都变成了微信转账——方便,却也冰冷。 我们到底在忙什么?忙着在朋友圈营造“岁月静好”,却不愿推开一扇真实的家门;忙着给陌生人的自拍点赞,却忘了隔壁邻居姓什么。 今天黄昏,我鬼使神差地走到老同学大刘开的修车店。他满手油污地递给我一支烟,我们就在轮胎堆里坐着。他没问我工资,我没问他生意,只是看着夕阳把机油渍染成琥珀色。 “下个月,”他忽然说,“我闺女满周岁,就来家里吃个便饭。” 我点点头。没有“收到”,没有“一定到”,就像二十年前我们约着去河里摸鱼那样自然。 深夜,我点开一个久未联系的朋友的朋友圈,看见他昨天发的九宫格——精致的餐食,完美的构图,配文“相聚总是短暂”。而我知道,照片里那个坐在他对面的人,上周刚跟我抱怨过已经两年没见他了。 也许,断联不是无情,而是我们在人海里泅渡太久,终于学会了给感情戴上呼吸器。不是不想联系,是害怕那份亲密,早已承受不起现实的重量。 窗外,最后一盏灯也熄灭了。在这片越来越深的静默里,我突然明白:我们不是在告别彼此,而是在告别那个需要靠频繁走动才能证明亲密无间的时代。 夜风渐凉,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钟声。一下,两下,像在敲打一个正在隐去的世界。钟声过后,寂静会更沉,但总有人会在寂静里,打捞那些沉没的温情。 王志文:“人一旦历练到不想说话,不想争辩,不想巴结,不想讨好任何人......喜欢独来独往,那么你就悟透了人性,看透了人生。” 当一个人不再想维持某些关系,甚至对逢场作戏都感到厌倦,享受独处时,这可能是他对人生和人性有了更通透的认知。 现实生活中,其实,人都是害怕孤独和寂寞的,在各种社交场合,总是希望加更多的人进入自己的好友圈,得到更多人的电话号码存到自己的通讯录。 然而,随着年龄的渐长,走着走着,很多人就散了,很多人也淡了。即便通讯录里还有彼此的名字,还能看到朋友圈的动态,但是关系可能已经变了,再也回不到曾经的亲密无间,而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时代急躁,社会浮躁,人心多变,物欲横流,攀比嫉妒盛行,手机越来越抓住了人的眼球和内心,刷着短视频,一会功夫就过了好几个小时,也越来越没有想要与人沟通交流的欲望了。 现如今的时代,物质丰富了,条件好了,年轻人也都提前过上了中年人的生活状态,不愿意社交,不愿意串门,更不愿意走亲戚。 很多人,随着阅历的增加,看多了人情冷暖,就会失去主动交友的兴趣和动力。 正如有句话:“童年的朋友,因为时间的恩赐保持了友谊,但如果相遇在现在,可能不会成为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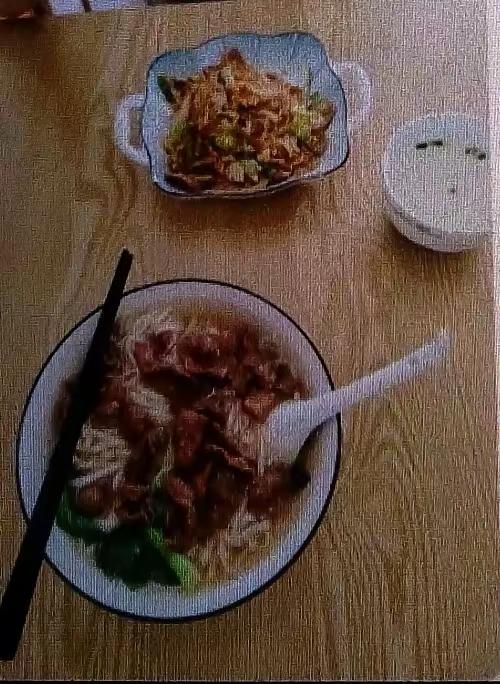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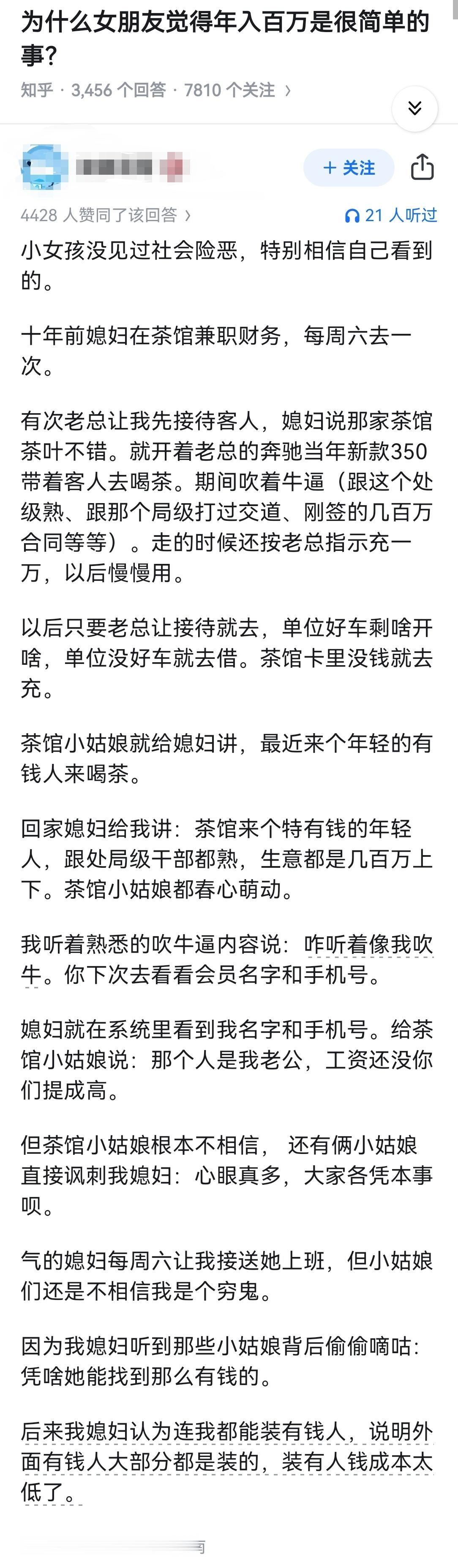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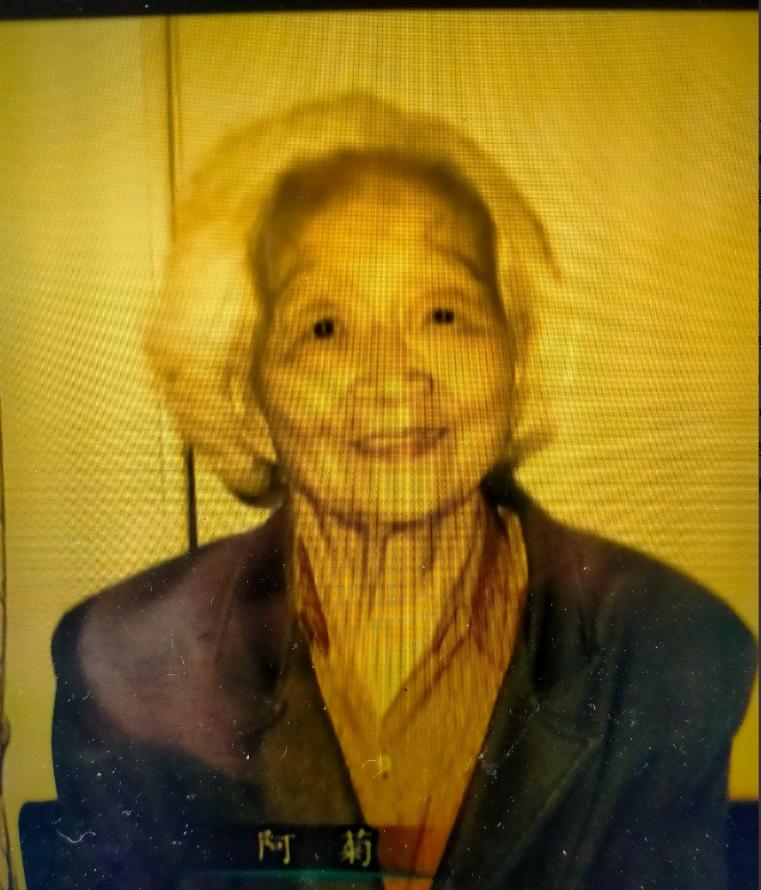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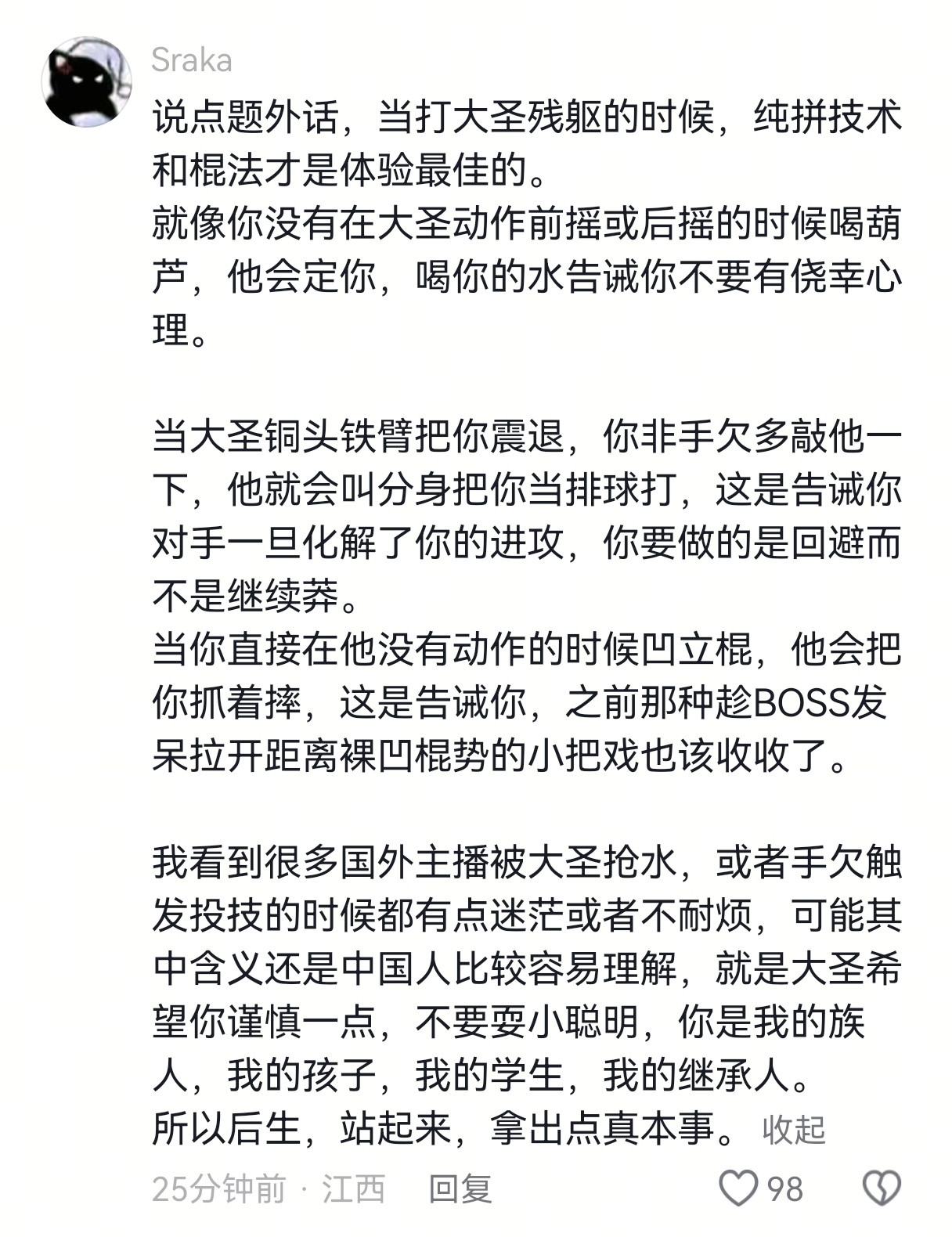
![咋还给自己加戏了呢你谁啊……谁认识你啊?怎么还跟我有孽缘呢[笑着哭]](http://image.uczzd.cn/1494067049118196486.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