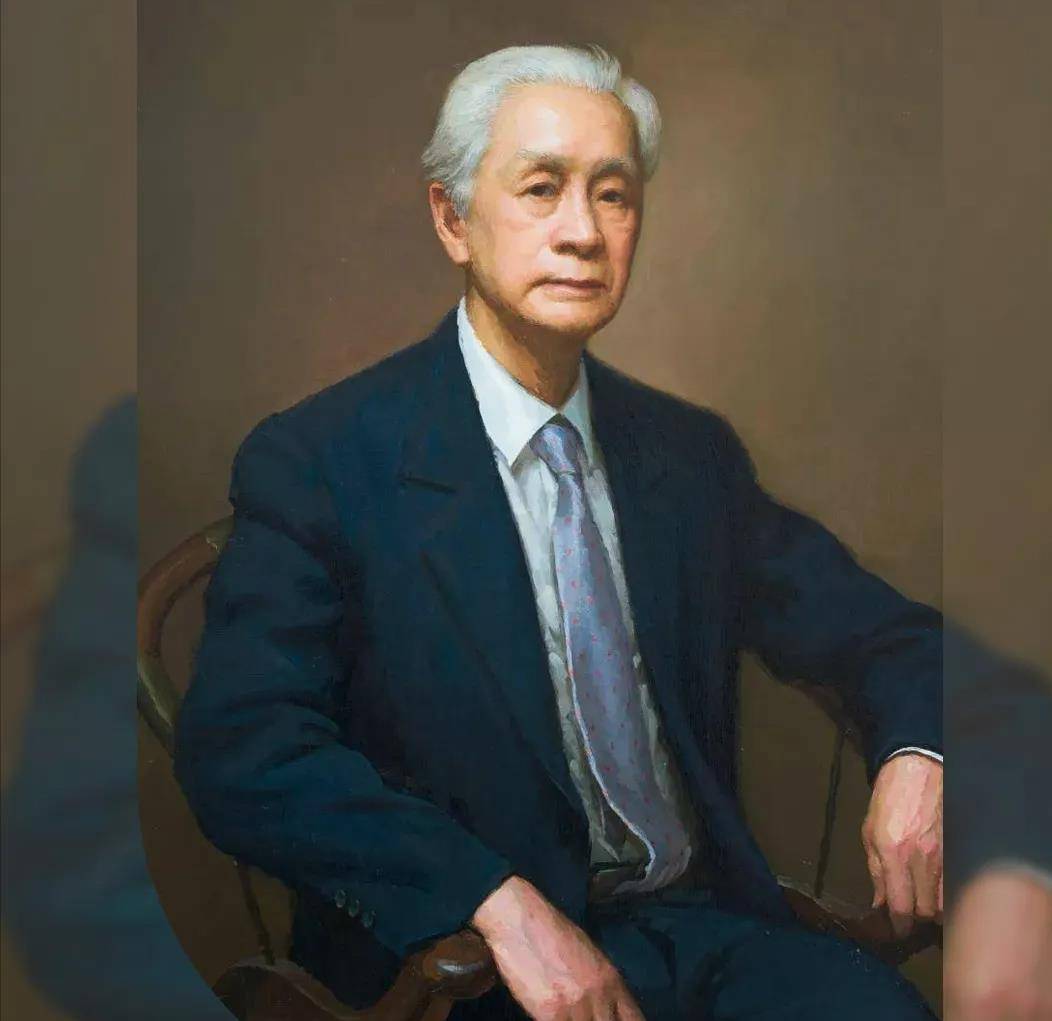1959年,顾方舟不顾众人反对,强行给不满一岁的儿子,灌下一管“非死即伤”的溶液,他哭着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但是为了亿万婴儿,我别无选择!” 顾方舟,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富裕的家庭。5岁时,父亲因感染了传染病去世。 那以后,他家道中落,幼小的他也因此备受冷眼和欺负。所以,他的母亲含辛茹苦抚养着几个孩子,一直教育他们一定要争气。 母亲还告诉他要他好好读书,长大了当一名医生。从此,顾方舟心里就种下了学医的种子。 1944年,顾方舟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医学院,也就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大学毕业时,同学都讨论毕业后做什么?有的说做内科医生,有的说做外科医生,可顾方舟却坚定地说:“我要从事公共卫生事业,治疗更多的人。” 能说出如此豪言壮志的人,必定是心怀国家之人。毕业后,他到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痢疾研究工作,抗美援朝战争中,被派去前线给战士治病。 后来,他又被派到苏联学习,这一学就是4年。 1955年,一种来势汹汹的传染病,悄然在江苏南通爆发,并且迅速传播到了全国各地。 病毒疯狂肆虐,通过唾液、粪便及不明原因的传播,一夜之间便能让活蹦乱跳的孩子,变成四肢瘫痪的状态,更可怕的是,这种病很难治疗,轻则终身残疾,重则危及性命。 这种疾病在医学上叫“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一旦感染上这种病,那种夸张的S型体态,将会陪伴他们一生。 就在各地陷入一片恐慌,家长们人心惶惶,不敢让孩子出门之际,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医学家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启了他与小儿麻痹症的战斗。 当时他迅速组建了一只专门研究脊髓灰质炎病毒的队伍。 虽然在当时国外已经有两种疫苗了,包括美国研发的死疫苗,可是这种疫苗虽说能杀死病毒,但是不能控制病毒的再次传播,并且打一针就要5美元,还要打3次才行。 如此昂贵的价格,大部分中国人当时都消费不起,所以即便知道有药,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在痛苦中死去。 当然,还有一种是苏联研究的活疫苗。虽然,它的生产成本是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是具体反应还要经过临床试验,也就是说它的疗效还不太确定。 不过,综合考虑下,顾方舟还是觉得适合我们国情的就是活疫苗。然而,在我们提出向苏联专家学习时,对方给的都是周边资料,独缺少核心资料。 这说明苏联专家并不想给予我们太多帮助,想着求人不如求己,所以顾方舟决定到云南成立实验基地,然后我们自己进行研究。 因为有了不成功不罢休的决心,所以他们的团队都是拖家带口的,没房子就自己盖,就这样,在大家的努力下,他们在短短九个月就盖好了19栋楼房。 就连实验室都是自己建的,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他们坚信一切阻碍疫苗研究的事都要战胜,也都能战胜。 终于在1959年底,第一批疫苗经过动物实验,可以进入人体实验了,此时大家却犯了难,找谁来试验呢? 此时的顾方舟毫不犹豫地将疫苗溶液用在了自己身上,漫长的一周过后,顾方舟安然无恙 但问题又来了,大人或许因为自身抵抗力的关系能够确保安全,可是孩子呢? 脊髓灰质炎的发病年龄大多是7岁以下儿童,顾方舟以身试药虽然成功了,但孩子未必。 怎么办?要想疫苗投入使用,必须用孩子来做实验。 这时顾方舟又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就是用自己不满一岁的儿子做临床试验。 要知道,如果失败了,孩子要么死亡,要么重伤,无论哪种结果,都是致命的。 但为了千千万万个儿童,顾方舟还是瞒着妻子,将溶液倒进了儿子口中。 接下来的一个月,是顾方舟身为父亲最“称职”的一个月,他不分白天黑夜地照顾儿子,观察儿子的体温等情况。 充满煎熬的一个月终于过去了,顾方舟的儿子没有任何异样,同事们被顾方舟的精神感动了,也纷纷给自己的孩子灌苏了溶液。 所有的孩子都没有异样,证明疫苗溶液临床成功了。 这个时候,一向坚强的顾方舟却反而哭了,和同事们抱在一起哭了…… 至此,顾方舟终于敢将疫苗大规模的投入使用。 1960年12月第一批500万人份的国产“灭活疫苗”生产完成。 并在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定点推广,大量人群使用后,证明了疫苗的防疫率高达93%。 全国流行的骨髓灰质病,也在顾方舟等科研团队的努力下获得了好转。 之后,顾方舟团队又针对疫苗不好储存,孩子不愿意吃的问题,决定把它制成糖衣外壳。 经过一年多的研发,1962年糖丸疫苗面世! 目前30岁以上人都吃过这样的糖丸,顾方舟的称呼也从“糖丸叔叔”变成了“糖丸爷爷”。 2000年,中国彻底消灭了小儿麻痹症。为了这一天,顾方舟整整奋斗了40多年。 2019年1月2日,糖丸爷爷顾方舟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留下了一个没有“脊髓灰质炎”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