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张之洞与妻子发生争吵。不料,他一怒之下,竟然将妻子活活踢死。他连夜写信给岳父道歉,没想到,岳父却说:“这不怪你…” 1849 年的北京城,春寒裹挟着报喜的鞭炮声。16 岁的张之洞站在顺天府贡院红榜前,手指颤抖着划过 “张之洞” 三个字。当围观人群爆发出惊叹,这个清秀少年知道,自己终于成为科举史上最年轻的举人之一。 张家老宅内,父亲张锳正摩挲着贵州知府石煦送来的贺礼。这位同僚的女儿石氏,与张之洞同岁,自幼饱读诗书,端庄娴静。张锳心中一动,立即修书一封,托媒人前往石府提亲。 消息传到贵州知府石煦耳中,他摩挲着门生张锳送来的谢帖,望着女儿石氏伏案习字的背影,心中已有盘算。石煦对张之洞的才华早有耳闻,两家门第相当,这桩婚事很快敲定。 1851 年,18 岁的张之洞与石氏在武昌老宅操办婚事。 红烛摇曳的新房里,石氏掀开盖头,露出比诗卷更动人的眉眼:“听闻郎君八岁便能诵《大学》,不知可否为妾身作新婚诗?” 张之洞提笔写下 “梅映寒窗月,卿伴砚边香”,从此书房多了红袖添香,科举路上有了最暖的牵挂。石氏不仅能为丈夫誊抄奏章,更会在深夜为他披上棉衣,绣着 “青云直上” 的荷包,始终挂在张之洞腰间。 1864 年的夏夜,31 岁的张之洞已是京官。当石氏带着 3 岁幼子来京团聚,他特意将书房布置成母子的卧房。然而仅仅月余,一场关于孩子前途的争执,将美满婚姻推向深渊。 “京城最好的私塾名额难得,孩子该启蒙了。” 张之洞将烫金的入学请柬拍在桌上。 石氏攥着儿子的小衣裳,声音发颤:“才三岁的孩子,离开母亲如何吃得消?” “妇人之仁!” 张之洞猛地起身,木椅在青砖上划出刺耳声响,“若想成大器,就该从小磨炼!” 石氏急得落泪:“你幼时读书,父亲可曾将你早早送出门?”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吵愈发激烈。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张之洞的怒火,他一脚踢向桌案,案上镇纸擦着石氏耳畔飞过,紧接着一脚正中她小腹。石氏踉跄倒地,顿时鼻孔血流如注,昏迷不醒。 看着妻子倒在血泊中,张之洞的世界轰然崩塌。张之洞惊慌失措,急忙请来郎中,但一切都太迟了。 当郎中摇头叹息时,他瘫坐在地,他颤抖着写下家书:“儿媳于昨夜因小儿事,与儿争执,儿一时愤怒,竟失足将媳妇踢倒……” 字里行间满是慌乱与自责。 消息传到石家,石氏的兄长石祥勃然大怒,扬言要将张之洞告上公堂。墨迹未干,就收到大舅哥石祥的口信:“杀人偿命,绝不姑息。” 张之洞惶恐万分,再次写信向父亲求救: “子祥内兄认为孩儿不应当将妻子踢死,扬言要提起诉讼。…… 此事不兴诉讼则已,如果兴讼,与儿前程殊多窒碍,即堂上官以儿为情有可原,百方回护,然至少亦必免去官职。二十载辛勤废于一旦,殊深痛悼。” 他苦苦哀求父亲出面调解,生怕自己的仕途就此终结。 惶恐中,张之洞连夜修书岳父:“婿罪该万死,愿以命相抵。唯念石氏临终前,仍紧攥着小儿虎头鞋……” 信笺上晕开片片泪痕。 张锳接到信后心急如焚,立刻启程前往石府。他见到石煦,老泪纵横:“是我教子无方,害了令爱。但犬子年少有为,若因此事前程尽毁,实在可惜。看在往日情分上,还望您劝劝令郎,莫要再追究。” 石煦沉默良久,长叹一声:“这不怪你,也怪我女儿命薄。年轻人一时冲动,若因此毁了前程,实在不值。” 三日后,张锳带着儿子跪在石府门前。石煦望着昔日意气风发的女婿,如今形容枯槁,长叹道:“你可知她为何阻拦?孩子前些日子咳血,她怕你忧心,独自请了三次大夫……” 这句话如惊雷炸响。张之洞猛地想起,儿子衣领上的确有暗红痕迹,而石氏总说 “只是风寒”。 他捶打着地面,泣不成声:“岳父,我愿自毁前程,只求石家饶恕!” 石煦扶起女婿,老泪纵横:“你若真悔,就替她把孩子教成栋梁。” 一旁的石祥握紧拳头,最终将状纸撕成碎片。 在石煦的劝说下,石祥最终放弃了诉讼。这场风波看似平息,却在张之洞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场风波后,张之洞将儿子送进江南最好的书院,自己则投身洋务运动。 此后,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事业中,先后担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要职,成为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 这他的后半生,经历了三段婚姻。 续弦唐氏出身书香门第,新婚夜为他研磨时,指着案头《劝学篇》轻声问:“这‘中体西用’,可否也用在夫妻之道?” 可惜红颜薄命,两年后染病离世。 第三任妻子王氏,是四川布政使千金。她接过管家钥匙那日,当着满院奴仆说:“老爷书房的灯,子时前不许灭。” 此后十年,每当张之洞伏案至深夜,案头总会出现一碗当归鸡汤。王氏还亲手教导石氏留下的儿子,将他培养成精通西学的栋梁。 最后的赵夫人,是在张之洞花甲之年相遇。她带来一匣子西洋望远镜,笑着说:“大人总看天下,也该看看星空。” 在她陪伴下,张之洞在湖北创办自强学堂,架起中国第一座钢铁厂。 每当夜深,汉阳铁厂的火光与星空交相辉映,恍惚间,他仿佛又看见石氏在烛火下微笑。1909 年,张之洞弥留之际,手中紧攥着半枚绣着 “青云” 的荷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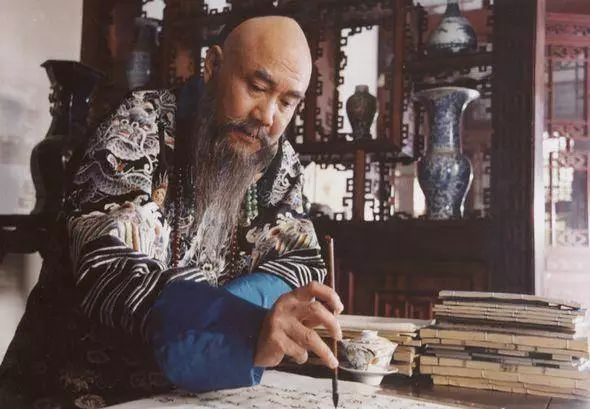

宇化贤
满清十大酷刑、闭关锁国、不思进取、文字狱、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剃发易服、驱使奴隶、鞑子一人管十家,银乱中国女子,欺男霸女、康熙乾隆六下江南挥霍奢靡、四库全书篡改禁毁15万册古籍、隐藏满清罪恶事实、抹黑明朝历史、禁锢思想、打断人民的脊梁骨、误人子弟,误导国人成为奴隶、阉割中华文明,使我国回到漆黑蒙昧的原始社会、凡有水旱,坐视不管、重徭役、纵贪官污吏,官以贿得邢以钱免,腐败,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国库空虚、圈地运动,百姓流离失所、民族压迫、宁与外邦不与家奴、割地赔款、不战而败、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百年屈辱、祸国殃民、扼杀维新、残暴专制、种族灭绝、赵州之屠、畿南之屠、潼关之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江阴八十一日、常熟之屠、四川大屠杀、金华之屠、南昌大屠杀、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汾州之屠、大同之屠、广州大屠杀、潮州之屠……几乎将明朝全境上下屠了个底朝天,整个华夏大地十室九空!中国文明领先世界几千年,直到满清统治时期才急剧衰落到世界贫穷国家。由于满清持续篡改两百多年的历史,很多罪恶都被掩盖!这些还只是已确认过的真实事件,不信的请自己先查一下有没有这些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