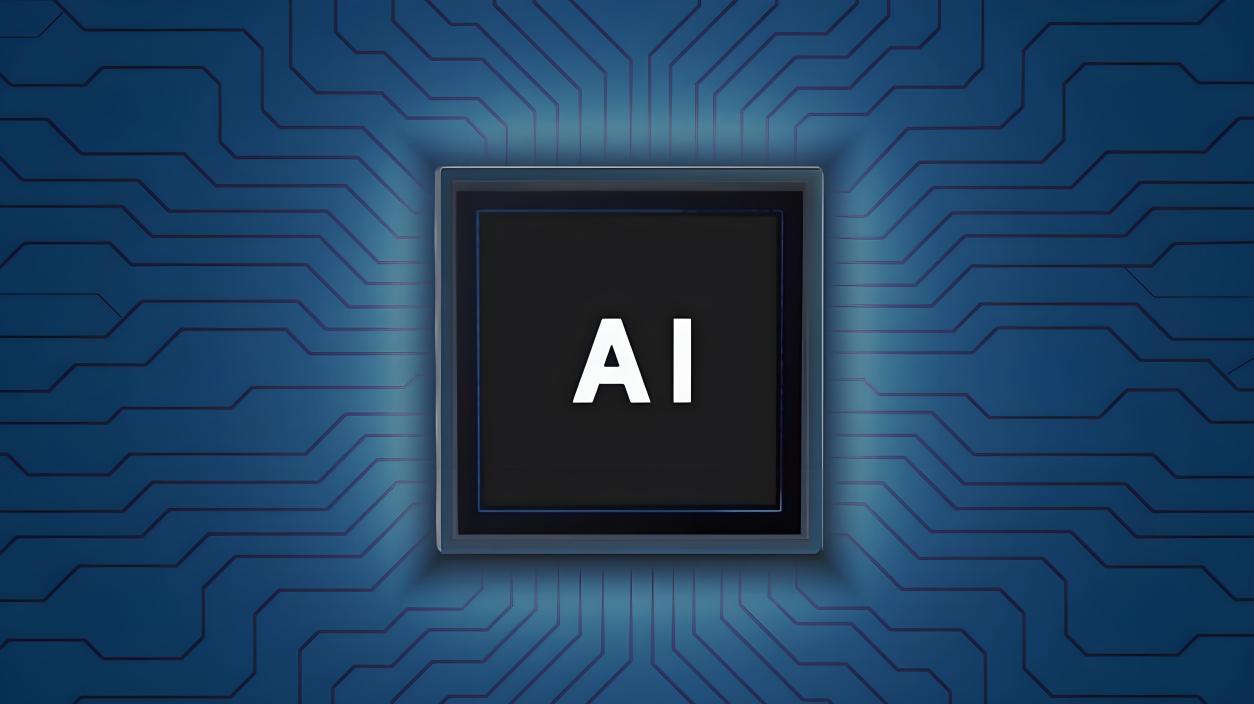昇腾弃ASIC投GPGPU,黄仁勋的“预言”成了催化剂? 两个月前,英伟达CEO黄仁勋一句“全球众多ASIC项目中,90%会失败”的点评,因英伟达与ASIC的竞争关系,被不少人解读为带有“诅咒”意味的宣言。未曾想,这一说法很快就与华为昇腾产生了关联——据外媒The Information报道,华为正计划将昇腾芯片的路线从ASIC全面转向GPGPU(GPU的子集)。作为国产芯片领域的巨头,华为如此突然的战略调整,在业内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时间拉回2018年,华为在上海全联接大会上首次公开昇腾系列IP及芯片产品,彼时,华为对其寄予了覆盖全栈全场景人工智能的厚望。然而,七年过去,昇腾却始终被困在ASIC专用级场景的“孤岛”中,未能完全实现华为的预期。 ASIC是一种为特定目的设计的芯片,《Info Tech》曾指出,其架构根据特定算法定制,在局部场景中算力表现突出,但通用计算能力受限。一旦算法改变,ASIC的算力性能会大幅下降,甚至需要重新定制。 昇腾目前年销量约70万片,主要面向大型客户。这些客户依赖昇腾团队的深度定制优化支持,落地成本很高。而用量小、场景复杂的客户难以获得同等技术支持,这严重制约了昇腾的规模化落地。 同时,昇腾芯片主要针对深度学习推理和训练特化,在图形渲染、并行计算、科学计算等领域表现乏力,既无法满足多元化场景的通用计算需求,又逐渐与主流生态脱节,陷入单一技术路线的孤岛困境。 黄仁勋曾直言:“ASIC虽在单一用途上效能与效率极高,但缺乏灵活性与扩展性。这种‘单点优化’策略,难以应对AI应用快速演进的现实。即便那些未失败的ASIC项目,也很难长期维持竞争力。”这番话精准点出了昇腾的问题。在“人工智能+”向各行业渗透的过程中,ASIC体系的局限与华为的战略诉求不符,因此,华为不得不重新规划昇腾的发展方向。 回顾国产AI芯片市场,昇腾并非首个在ASIC赛道遇挫的厂商。近三年来,国产ASIC领域衰退明显:2023年,比昇腾更早出现的芯锋宽泰因3代产品迭代失败和本土生态短板倒闭;去年,powerpc领域的合芯科技因技术路线缺乏长期潜力,资金链断裂,核心管理层失联;今年上半年,神顶科技因3d空间计算芯片产品落地不及预期,出现欠薪,上海与台湾团队解散;华夏芯曾宣称“填补国产异构处理器空白”,后因量产能力不足、无法覆盖研发成本而破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产GPGPU厂商正积极冲击IPO。近一个月,摩尔线程、沐曦向沪市科创板递交上市申请。摩尔线程以全功能GPU布局为特色,产品覆盖AI训练到图形渲染;沐曦专注通用计算芯片,在AI推理市场表现亮眼。据预测,摩尔线程上市估值将达800亿元,沐曦为390亿元。聚焦通用GPU的壁仞科技也在推进上市进程。 行业研报显示,GPGPU在传统GPU架构基础上,去掉部分加速硬件单元,增加专用向量、张量、矩阵运算指令,精度和性能更高,已成为智算芯片的首选。未来几年,中国GPGPU行业市场规模将以年均40%-50%的速度增长。由此可见,华为让昇腾从ASIC转向GPGPU,虽令人意外,却也合乎情理。但关键问题是,此时转型的昇腾,如何赶超其他国产GPGPU乃至英伟达? 在昇腾的市场化进程中,华为投入巨大。例如,在科大讯飞的大模型项目中,华为派遣数百人技术团队负责昇腾芯片的适配调优。市场开拓时,昇腾依托华为从芯到云的软硬件闭环,具备天然的捆绑销售优势。 凭借这些资源支持,昇腾在国产化市场一度占据优势,进入不少头部用户的业务场景。但可惜的是,华为在ASIC赛道竭尽全力,仍未将昇腾的“孤岛”变为“新大陆”。如今转向GPGPU领域,以往的策略还能否奏效? 业内认为,“时移事易”,昇腾面临的壁垒难以仅靠资源堆砌解决。“英伟达在CUDA平台与软件开发社群布局数十年,即便华为采用‘兼容+开源’双轮驱动,最乐观也要2-3年才能缩小差距。”这一差距并非外力能轻易改变。 此外,因ASIC应用场景限制,昇腾910的使用范围较窄。有消息称,“目前除了华为自己的研究所回购外,只有一些科研场景使用(昇腾910)。”同时,信创市场正整顿“发包配额制”采购方式,指定性及捆绑式销售策略逐渐失效,华为很难再为昇腾提供过多场外支持。 尽管昇腾及时从ASIC的岔路转向,但已失去较多容错空间。人们期待,摆脱额外加持的昇腾,能在GPGPU市场展现出真正的实力。毕竟,“人定胜天”的故事更能打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