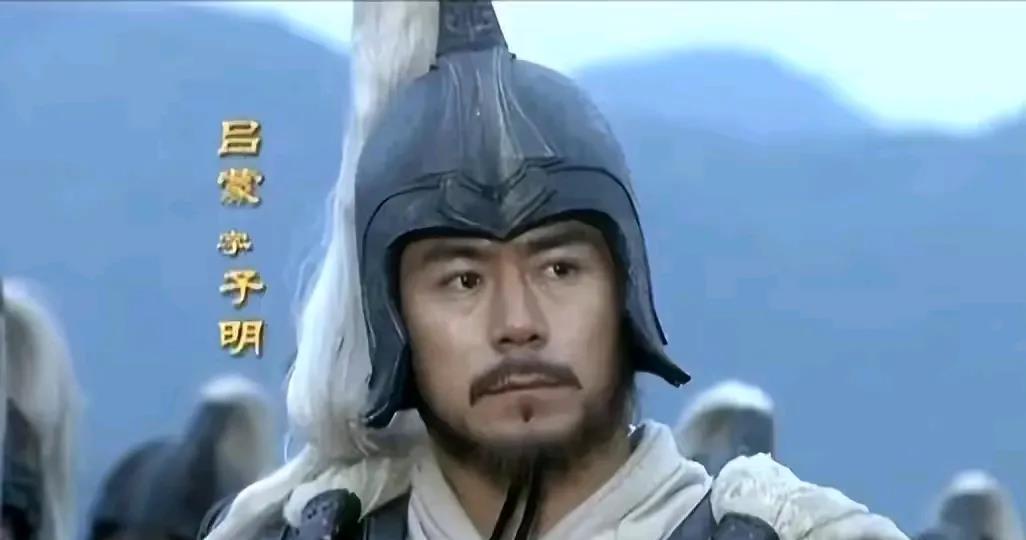公元217年,孙权在濡须口大宴诸将。喝到兴头上,他亲自端酒到大将周泰跟前,突然命令他:你把衣服脱了,给大家看一看。 帐内的喧闹声像被人掐住了喉咙,瞬间静了下来。周泰握着酒杯的手顿了顿,指腹上的老茧把陶杯磨出轻微的声响。他刚从濡须口的城楼上下来,甲胄还带着江风的潮气,听闻孙权设宴,连内衬的麻衣都没换——那上面还沾着今早巡查时蹭到的草屑。 “陛下这是……”坐在周泰旁边的朱桓刚要开口,就被孙权瞥了一眼。这位年轻的吴主今天穿了身常服,锦袍上绣着江涛纹,可眼神里的威严比穿龙袍时更盛。他把手里的酒壶往案上一放,酒液溅出来,在青铜盘里积成小小的水洼:“周将军照做便是。” 周泰没再多问。他解开腰间的玉带,褪下外袍时,左臂一道深可见骨的疤痕先露了出来——那是建安十三年在赤壁,为了护孙权突出重围,被曹营的长矛划的。帐内有人“嘶”了一声,那道疤像条僵死的蛇,盘踞在黝黑的皮肤上,连新长的皮肉都带着狰狞的凸起。 “这道伤,是在宣城替我挡的山贼。”孙权忽然开口,拿起案上的银匕,轻轻点了点周泰的左肩。那里的疤痕更旧些,边缘已经淡成了浅褐色,“当时你抱着我从城墙上跳下去,后背被箭射穿,血把我的衣袍都浸透了。” 周泰脱得只剩里衣时,满座的将领都看直了眼。他胸前、后背、胳膊上,新旧疤痕层层叠叠,有的是刀剑伤,边缘齐整;有的是箭伤,小圆洞周围还留着青紫的印记;最吓人的是腰侧一道月牙形的疤——那是去年在濡须口,被张辽的部将用短刀划的,差点伤到内脏。 “这处,是在建安十四年的豫章。”孙权的声音忽然低了些,他走到周泰面前,用手指轻轻抚过那道月牙疤,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你昏迷了七天,我守在帐外,听见军医说‘能不能活看天意’,攥碎了三支玉簪。” 周泰的喉结动了动,想说“臣份内之事”,却被孙权按住了肩膀。吴主转身看向满座将领,手里还端着那杯没送出去的酒:“你们总说周将军出身寒微,不该领濡须口督的职。今日我就让你们看看,他身上的每块疤,都是替我、替江东挨的。” 帐外的江风卷着雨丝打在帐帘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朱桓的脸涨得通红,他想起前几日还跟人抱怨,说周泰不过是个从巢湖来的水贼,凭什么压过士族出身的将领。可看着那些纵横交错的疤痕,他忽然觉得手里的酒杯沉得端不动——那些伤,换作是他,未必能撑下来。 “周将军,”孙权把酒杯递到周泰唇边,像当年在宣城,亲手给他喂药那样,“满饮此杯。” 周泰仰头喝干酒,喉结滚动时,胸前的疤痕跟着动了动。孙权拿起自己的锦袍,亲自披在他身上,系带时手指不经意碰到周泰后背的旧伤,对方下意识地缩了一下。吴主的动作顿了顿,忽然对帐外喊:“把我那柄青釭剑取来。” 等侍卫捧着剑进来,孙权抽出剑鞘,寒光瞬间照亮了帐内。他却没递剑,反而用剑鞘敲了敲周泰的肩膀:“从今日起,周泰佩我的剑巡营。谁再敢对他不敬,先问问这剑答不答应。” 宴席散时,江雨已经停了。周泰披着孙权的锦袍走在回营的路上,衣料上的龙涎香混着他身上的草药味,竟不觉得违和。朱桓追上来,手里拿着个药囊:“这是家传的金疮药,比军中的好用。”他没说对不起,可递药囊的手却很稳。 周泰接过药囊时,指尖碰到对方的手,两人都笑了。远处的濡须口城楼亮着灯火,像嵌在江岸上的星辰。他忽然想起刚才孙权替他披袍时,在他耳边说的话:“那些疤痕不是伤,是江东的根基。” 后来周泰在濡须口镇守了十年,每次新兵来营,他都会脱了衣服给他们看疤痕。不是孙权命令的,是他自己要讲——讲每道伤背后的战例,讲宣城的险、赤壁的烈、濡须口的急。那些年轻的士兵看着那些疤痕,就像看见江东的土地上,早已埋下了不会动摇的根。 孙权用最直白的方式,给了周泰最体面的尊重。在那个看重门第出身的年代,他没说多少大道理,只让所有人看见:能护着江东的,从来不是族谱上的姓氏,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