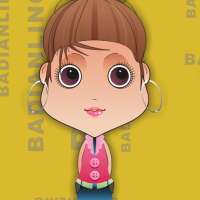1978年,兰州军区司令来到新疆,新疆军区司令亲自迎接,热情地说老战友好。他们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前排右四就是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上将,右二是新疆军区司令刘震上将。 1978年的一天,机场边风沙未歇,身着军装的迎接队伍早早等候着,带头的正是刘震上将,他亲自出面迎接的,是从兰州远道而来的韩先楚上将。 多年未见,两人相视而笑,那一声“老战友好”既朴实又深情,合影中,韩先楚站在前排右四,刘震紧挨着右二,一群老战友肩并肩站着,眉眼之间都写满了熟悉。 这场重逢,不是一段军礼那么简单,要说起这几位将军的渊源,还得翻回到几十年前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当年的红二十五军并不起眼,不像红一方面军那般名气大,但它是所有红军中唯一一支从鄂豫皖根据地一路坚持长征、最后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队伍。 就在那支队伍里,蹲过灶台、趟过雪地、挨过冻疮的一个班里,出了三位后来名震军界的高级将领:陈先瑞、韩先楚、刘震。 一次韩先楚临时走散,躲进树林里当起了“野人”,肚子饿得慌,头顶还响着敌人的枪声,就在他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一队红军从前头路过,正是刘震带队。 他一眼认出了这个躲在草堆里的“野人”,还没等韩先楚开口,刘震就扑过去拉他一把,嘴里喊着:“同志哥,同志哥!”那场面,韩先楚到老都记得。 也不是没有争执,韩先楚年轻气盛,见义勇为,早年曾因为擅自释放一位被怀疑是“奸细”的老百姓,被调离了作战岗位。 领导说他“心太软,不适合指挥作战”,转眼就把他丢去做司务长。 韩先楚心里窝火,却不敢反抗。可也正因为这次调整,他后来才和刘震“搭伙”了——刘震那时候可没放过他,专门指派他做伙夫,还美其名曰“考验一名战士的责任感”。 说是考验,其实是开玩笑的成分更多,韩先楚干厨务根本不专业,有次打土豪回来,摸黑进人家厨房找吃的,一伸手抓到马桶里,一手“臭鸡蛋”捞出来,吐得满院子都是,嘴里还念叨“吃不得,吃不得”。 旁边几个战士笑到肚子疼,刘震更是边学他语气边打滚,几十年后再提这事儿,屋里一群将军照样笑作一团。 这些糗事其实也早就传成了口口相传的“红军段子”,不像教科书里那样严肃刻板,更多的是血肉饱满的生活本色。 1984年的海军大院,一场名为《红二十五军战史》的编委会,成了将军班的再聚首,场子不大,坐下的都是一身伤疤、满脸皱纹的老战士。 会议室成了“揭短大会”,你一句“歪嘴子”,我一句“红花棉袄”,将军们笑得前仰后合,刘震当场模仿韩先楚当年“抓鸡蛋”的模样,说得眉飞色舞,韩先楚脸涨得通红,还不忘翻旧账,反咬刘震藏私盐,违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笑闹归笑闹,情分是真的,他们互相叫着小名、绰号,不叫军衔,也不提职务,哪怕韩先楚已经是副总参谋长、军区司令,刘震是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陈先瑞也担任过几个大军区政委,坐一起还是“老班长、歪嘴子、小韩”。 这些称呼,是在烽火连天的年代里熬出来的,哪怕身后写满军功章,也不如一句“老班长”来得亲。 更难得的是,他们仨后来走的路都不一样,韩先楚以“旋风司令”闻名,解放海南、指挥渡江、横扫中原,每一仗都打得干净利落,他的部队在国民党那边有外号,叫“疯子部队”,打哪儿哪儿塌,他是典型的前线型将领,不喜欢待在指挥部,老爱亲自侦查地形,跟着士兵一块摸黑钻沟。 刘震则是另一种将军,他打仗利索,但更擅长稳重指挥,打完仗最爱跳舞,哪怕是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战场,脱了棉衣也要摇一段,他喜欢西服、打领带、喷香水,老战士打趣说他是“军队里最像外交家的将军”。 他退下来以后,专门写了一篇《老同志要有点乐退精神》,说得清清楚楚:该退就退,别拖着不给年轻人腾地儿。 陈先瑞虽然不跳舞、不穿西装,但他用另一种方式“战斗”到最后,从1982年开始,他牵头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跑遍全国找材料,访老战士、查敌方档案,挑灯夜读改稿。 别人劝他休息,他摆摆手说:“写史不是写我自己,是替那些没名字的兄弟写点东西。”他常说他们那个班,只剩他们仨了,其他人,有的连个坟都没留下。 1986年,韩先楚去世,走得急,没有留下遗言,刘震在追悼会上沉默很久,最后只是轻轻地说:“老韩这人,一辈子没闲过。” 再后来,1992年,刘震也走了,那个老是跳舞、开玩笑、抹面霜的将军,连去世的方式都像谢幕。 1996年,陈先瑞也离开了,他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访问,有人问他对“将军班”怎么看,他摆了摆手,说:“有什么好吹的?活下来的就仨,还有啥班可讲。”话音不高,但屋子里一下就安静了。 这个世界上,终究没有不散的班会,他们仨,从一个锅里吃饭的泥腿子红军,一路打成共和国的脊梁,又陆续走向人生的终点,他们没留太多话,却用几十年时间,把战友情、将军魂、红军史,刻进了共和国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