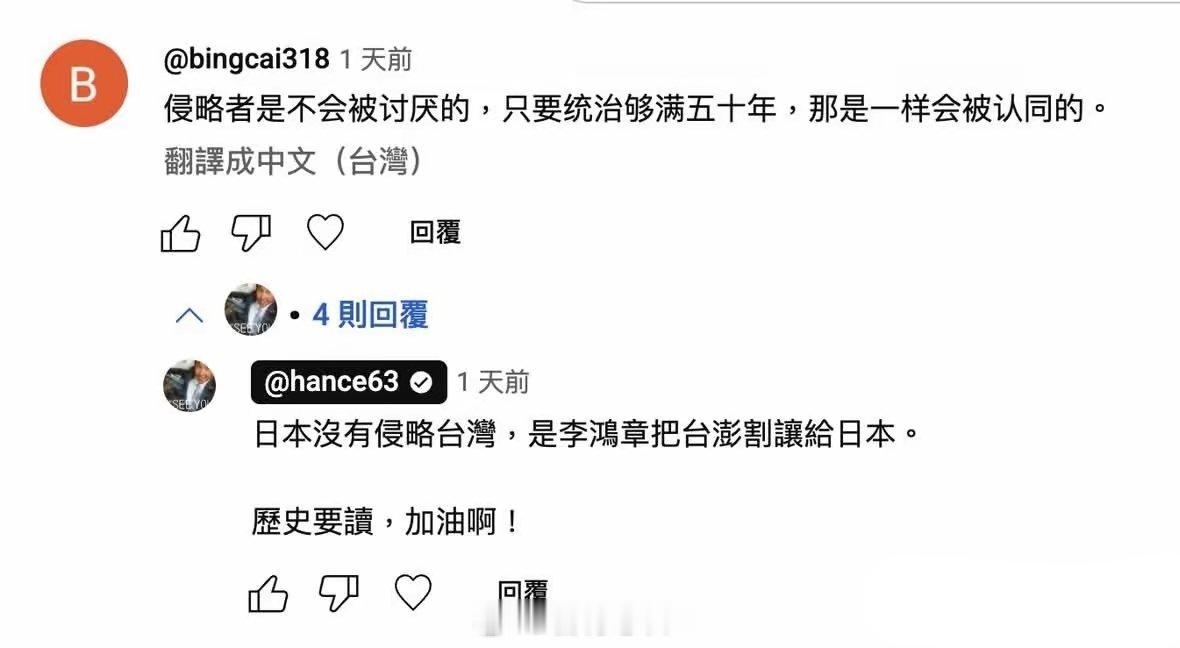那年1月19日的友谊关战俘遣返现场,一个佝偻的身影在晨雾中显得格外刺眼,汪斌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军装空荡荡挂在肩头,三十出头的人满头白发像落了一层霜。 人群里突然炸开一声吼:“叛徒还有脸回来!”他身子猛地一颤,枯瘦的手指死死攥紧,指甲深深陷进掌心。六年了,魂牵梦绕的故土近在眼前,迎接他的却是冰冷的唾弃。 战俘营的铁门哐当打开,越南看守粗暴地把他拖出来。镜子里的人形销骨立:颧骨高耸,肋骨根根分明地凸起,严重的风湿让双腿几乎无法打直,长期的折磨让他便血严重。体重秤的指针停在37公斤,比当年那个精壮的军人轻了整整60斤。 这37公斤,是1400多个日夜酷刑的见证。敌人想撬开他的嘴,电击、冷冻、强光照射轮番上阵,逼问部队机密。他咬紧牙关,一次次昏死过去,醒来后求死的念头从未停歇,甚至尝试过用鞋带结束生命。 他并非没有反抗。曾有一次,他趁着看守松懈,拖着伤腿挖通墙壁,逃出数里地,靠着野草充饥,拼命向祖国方向爬行。可惜最终仍被追上,皮带深深勒进浮肿的腰腹。 时间拉回1984年4月28日,老山收复战打响。汪斌所在的连队在穿插48号高地时,一头撞入越军精心布置的伏击圈。炮火覆盖之下,阵地瞬间化作修罗场。 连长、指导员相继牺牲,作为排长的汪斌抓起染血的指挥旗,嘶吼着带领剩余战士冲锋。刚冲出几步,左腿便被子弹击中。年轻的通讯员为掩护他扑上来,当场牺牲。弹尽粮绝之际,汪斌摸出仅剩的两颗手榴弹,拉开引信奋力掷向敌群。 就在他被敌人枪托砸中后脑、意识模糊的瞬间,他瞥见七十米外岩石后一张熟悉的脸6班长花国顺!用尽最后的力气,汪斌朝着战友的方向嘶喊:“朝我开枪!不能当俘虏啊!”花国顺的枪口剧烈颤抖,泪水模糊了视线,那扳机,终究没能扣下。这一瞬间的犹豫,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落入敌手,才是真正磨难的开始。河内的广播里,天天播放着伪造的“汪斌少校弃暗投明”的录音。敌人强迫他按手印拍下“投降书”,照片传回国内,不明真相的战友们悲愤交加,搪瓷缸摔得乒乓响:“当初就该让花国顺成全了他!” 遣返回国后,即使在医院,屈辱也如影随形。卫生员好心扶他喝粥,邻床的伤员猛地打翻饭碗,厉声指责:“叛徒送来的东西有毒!”汪斌蜷缩在病床上,彻夜难眠,审查的压力和铺天盖地的骂名,像巨石压在心头。 病房门被轻轻推开。40师副师长陈知建(开国大将陈赓之子)走了进来,没有丝毫犹豫,他伸出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了汪斌那双布满伤痕、枯槁的手腕。陈副师长的话斩钉截铁:“信你投敌?我第一个不信!安心养病,天塌不下来!” 组织的审查严谨而漫长。政工干部查阅了大量缴获的越方档案,发现了令人震撼的证据,汪斌在狱中曾五次尝试自杀,鞋带勒颈的淤痕、绝食抗争被强行插管灌食的创伤、电刑留下的焦黑烙印,每一份记录都是他不屈的证言。一年后,审查结论终于下达:“无变节行为,恢复党籍军籍!”这迟来的清白,让在场所有人无不潸然泪下。 1993年,汪斌转业到山东邹城电力局工作。报到那天,他把用鲜血和忠诚换来的军功章,默默锁进了铁盒。妻子搀扶着他,一步一挪地爬上单位宿舍的三楼,严重的风湿常让他疼得直抽冷气。那些战争的梦魇并未远去,他常在深夜惊醒,呼喊“向我开枪”。 生活的转机在平凡中孕育。女儿大学毕业,将一份“优秀党员”的证书捧到他面前时,这个饱经风霜的老兵,第一次咧开嘴笑了,眼泪无声地滚落。 在一次老战友的聚会上,当年的6班长花国顺,这个背负了多年自责的汉子,扑通一声跪倒在汪斌面前,痛哭失声:“老排长,当年我该帮你解脱啊……”汪斌用力把他拽起来,递过酒杯:“傻话!能活着回来,看着孩子长大成人,喊声爹,这辈子,值了!”窗台上,那盆五星花悄然绽放,鲜红的花朵在阳光下迸发着生机,像极了当年老山焦土上,战士们用生命守护的那抹希望之色。 真正的硬骨头,不是刀枪不入,而是在漫长的黑暗与屈辱中,死死护住心里那颗星火不灭。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可那脊梁,从未弯过一寸;那份信仰,从未裂过半分。 本文核心事实依据《解放军报》2022年“老山战役三十八周年”特别报道及权威军史资料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