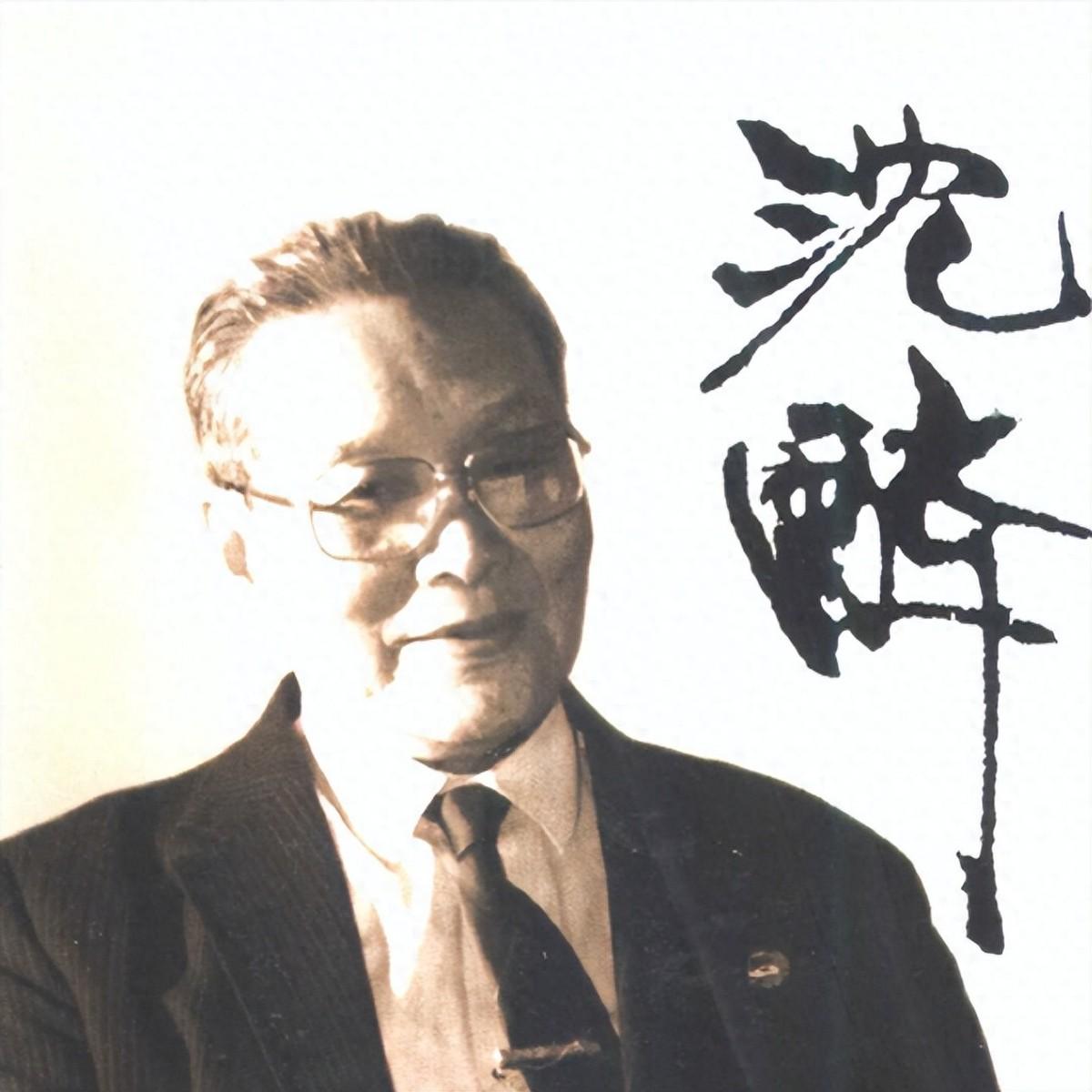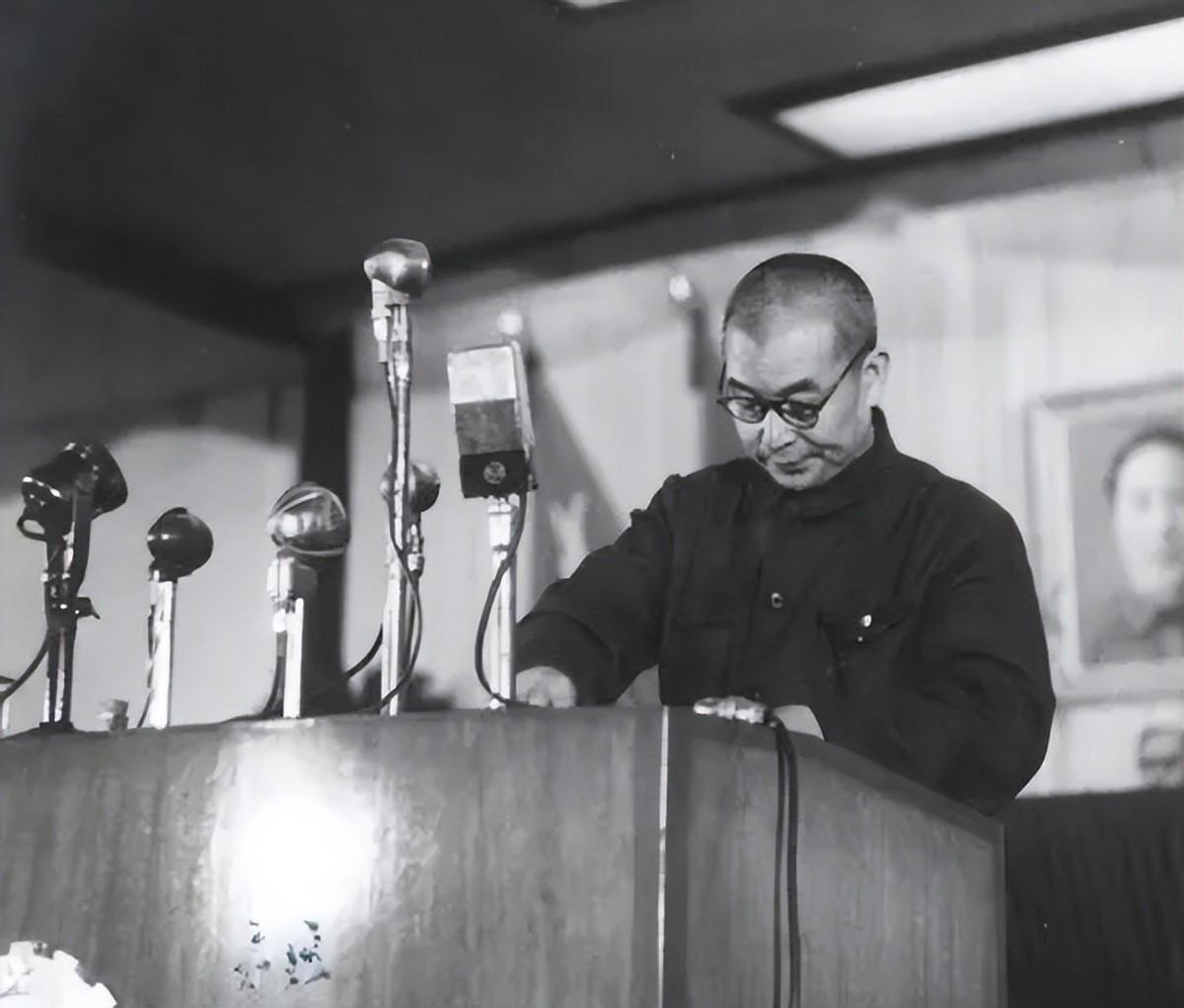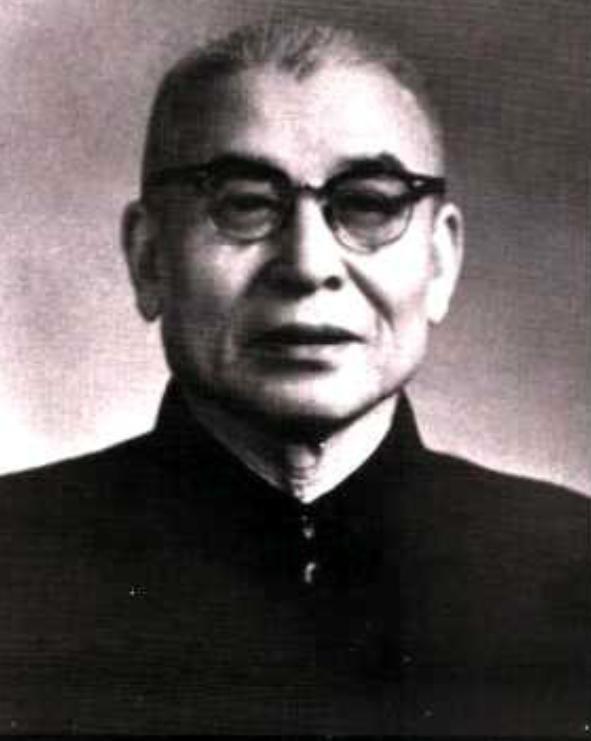1962年,沈醉等特赦战犯分配工作,结果顶头上司曾上过军统黑名单 1962年3月15日早晨,旧宫大会劳动营的大喇叭还在放着广播,“沈先生,名单贴出来了,你被调到全国政协!”看名单的传达员压低嗓子对沈醉说完便转身去忙其他事。那一刻,沈醉脑子里蹦出的第一句话是:果然躲不过去。 离开劳改农场已整整一年,第二批特赦人员的去向成了北京城里小范围的谈资。有人被安排到地方档案馆,有人去了出版社,更有几位获准返乡务农。沈醉原先打听到风声,觉得自己大概率也会像第一批那样,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待遇一百元。可心里还是存了几分侥幸——如果能够被分到北京市政协,顺便照顾在北京上学的外孙女,再好不过。 对“顺从”二字,他再熟悉不过。自1956年被送进功德林接受改造起,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组织让干的事,干;让说的话,说。可真的轮到分配,沈醉却忽然打起退堂鼓。原因很简单,全国政协里坐着不少当年的受害者,甚至好几位是他贴着名字亲自追踪过的“嫌疑人”。 临行前一晚,沈醉在旧宫简易宿舍里翻出那本早被汗水浸软的摘录本,上面写着他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不管遇到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主动认错,主动赔礼。字迹歪斜,却是一年多来无数次思想斗争的结晶。合上本子,他深呼吸,决定硬着头皮上路。 到政协报到的手续并不繁琐,填表、体检、照相、领到一张浅绿色的“文史专员医疗证”和一枚红色塑料壳的出入证。灯光下那张合影照片有些晃眼,他盯着自己的皱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四十七岁了。身后传来熟悉的笑声,回头一看,竟是范汉杰,俩人相视苦笑——同一条船上的人,谁也笑不出声。 第二天中午,沈醉从礼堂后门往餐厅走,迎面碰上了政协副主席高崇民和常委阎宝航。阎宝航性子直,“沈专员,来得挺快嘛!”一句半打趣半欢迎的话让沈醉有点局促。高崇民伸手相握,“听说你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很有料,多写,多留史料。”握手不到两秒,可沈醉手心已满是汗。 握完手,他转身就钻进小卖部,只买了两块苡仁糕。长方形的小食散发淡淡甜味,却压不住心口的苦涩。1941年,沈醉刚到重庆时,军统圈子里盛传过“戴笠给东北救亡总会高崇民送巨款”的秘闻。那年他还不懂戴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甚至跑去问戴:“要不要抓?”结果挨了一句“你懂个屁”,从此不敢再多嘴。 时隔二十年,昔日被监视的“目标人物”摇身一变成了自己的领导,不得不说命运的折返弯实在太急。更巧的是,他的直接顶头上司阎宝航,曾被军统列为“甲级黑名单”。沈醉记得清楚,1945年夏天,机要室每天都会收到“东北战场情报”,封面红笔批示“重点盯防阎宝航”。史料表明,阎当时已把一摞关于美械装备的秘密资料送到了延安,蒋介石怒不可遏,却始终找不到确凿证据。 “过去的不提了,干好现在的事就行。”阎宝航在办公桌旁替沈醉倒了杯热水,语气温和得像邻家长者。水汽升腾,沈醉低头说了句“谢谢”,心里却翻江倒海——如果当年抓捕行动成功,这杯水怕是再也喝不上。 忙碌的日子很快让尴尬淡化。政协文史委需要把民国档案、口述材料、报纸剪辑重新编目,还得组织笔谈、座谈。起初,沈醉只敢整理别人交来的稿件,后来在同事鼓励下,他动笔写改造前后的对照日记,一天三四百字,配上手绘草图,说不上文采飞扬,却真切。 有意思的是,许多民主人士对他并无刻意疏远。审稿间隙,高崇民偶尔会递来一截烟,笑说:“抽还是不抽,由你。”沈醉连连摆手,心想自己已经戒了,但那份体面让他心里暖了一下。他暗自琢磨:或许这就是党和政府常说的“改造”吧,不只是生产劳动,还有情感洗涤。 转年春天,《沈醉日记》在内部小范围印行。印数不多,却引起强烈反响。有人评价说:“字句粗陋,真诚可见。”又过了几个月,政协安排他外出采访老地下党员,出差路条上写着“主持人:沈醉”。那一刻,他才真切明白自己完成了身份转换——从“看守对象”到“请你来记录历史的人”。 诚然,过去的伤痕不会凭空蒸发。偶尔夜深,他仍会梦见戴笠在房间里踱步,嘴里念叨着“懂个屁”。可梦醒时分,他已不再惧怕那句呵斥,因为新生活给了另一种坐标:坦白、负责、不逃避。 1962年的那张分配名单,只是长卷的一段,却让许多人转过了身、也抻直了腰。沈醉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了一句简短的话:“若非宽待,哪有今日搁笔论旧事。”黑体字下,落款时间——1978年冬。纸微微泛黄,却挡不住字里行间透出的改变与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