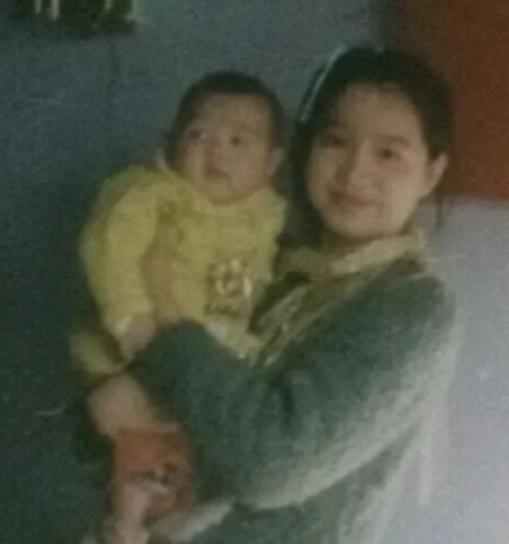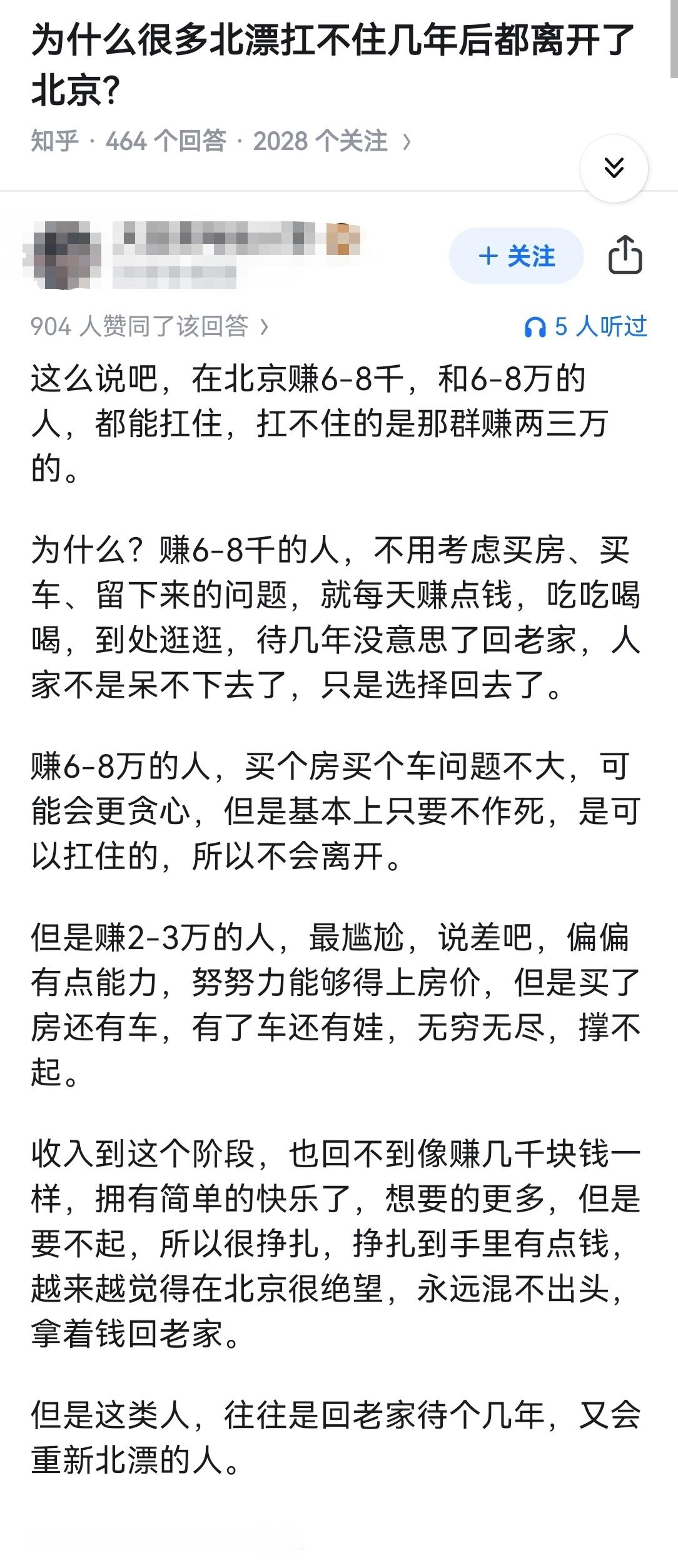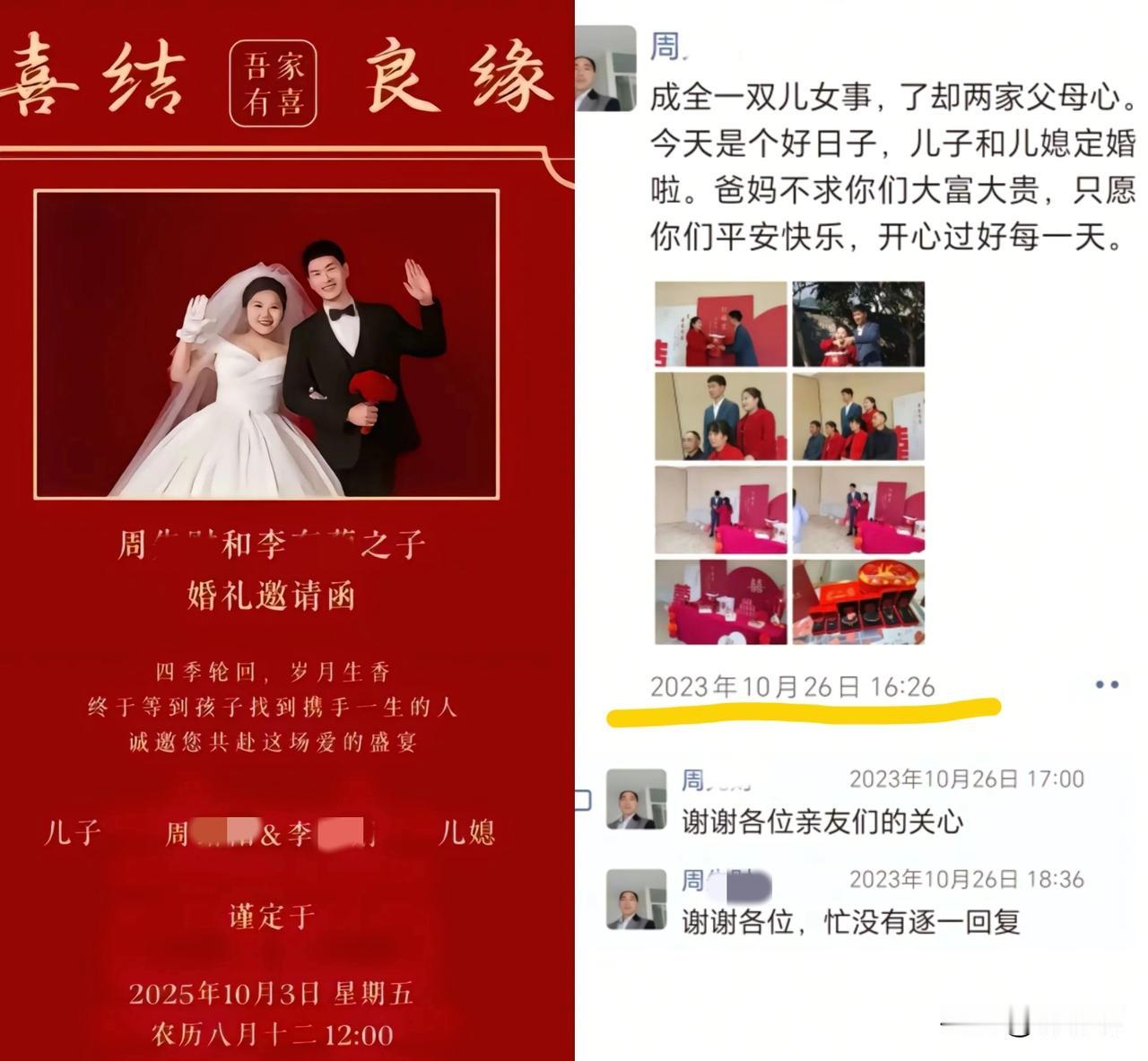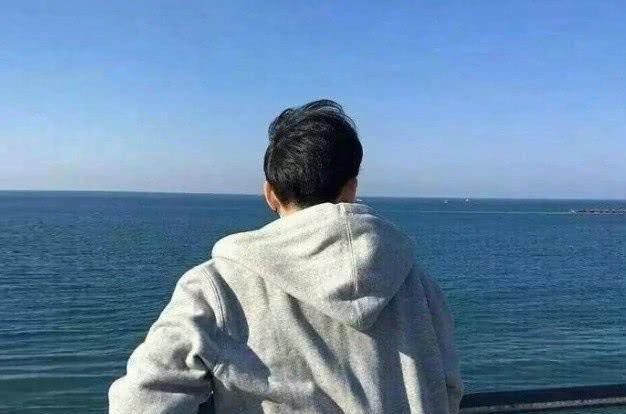1976年,女知青郭文婷抱着4岁的儿子回到了北京,母亲看着她怀里的孩子直接破口大骂:“你知不知道廉耻!”谁知道吃过晚饭后,母亲又抱起孩子说:“我们一起把孩子养大!” 四年前,1972年的陕北延川县,窑洞里煤油灯昏黄地摇晃,土炕边挤满了人。郭文婷咬紧牙关,汗水混着泥土味儿,湿透了她的军绿棉袄。 接生婆李婶儿手忙脚乱,锈迹斑斑的剪刀在灯上烤了又烤,嘴里念叨:“使劲儿,娃要出来了!” 窑洞外,暴雨砸得屋顶直漏水,瓦盆“滴答”接水的声音像催命符。文婷疼得几乎晕过去,脑子里却只有一个念头:孩子得活! 那晚,文婷拼了命生下玉强。接生婆用草木灰止住血,粗布襁褓裹住皱巴巴的小家伙。窑洞里,李强夫妇——文婷的房东,蹲在门槛上抹眼泪。 没人提孩子的爹是谁,大家心照不宣。文婷是个北京知青,18岁下乡到这黄土高坡,城里来的细皮嫩肉早被风沙磨得满手冻疮。 她没说,村里人也没问,只知道孩子的爹是个“去了的汉子”。陕北人厚道,村里人帮她把孩子养到一岁,玉强学会叫“娘”时,文婷抱着他哭了整整一宿。 1976年,知青返城政策松动,文婷终于等来了回北京的机会。她攥着公社开具的《随行证明》,抱着玉强,挤上延安到铜川的破旧大巴。 车厢里满是麻袋和鸡笼,玉强吓得哇哇哭,文婷哄他:“别怕,咱要回北京,见姥姥!” 36小时的绿皮火车,座位底下铺着麻袋当床,文婷搂着玉强,闻着车厢里混杂的汗臭和煤灰味儿,脑子里全是母亲李桂兰的影子。 她想起1968年下乡前,母亲在胡同口送她,塞给她一双尼龙手套,说:“城里闺女到乡下,别冻坏了手。” 可如今,她带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回去,母亲会怎么看她?火车摇晃,文婷低头看玉强,孩子穿着陕北的红布肚兜,绣着蝎子图案,小脸冻得通红。她摸摸孩子的开裆棉裤,心里酸得像灌了醋。返城路上,她翻来覆去想,该怎么跟母亲开口? 椿树胡同的冬夜,煤炉里烧着劈柴,豆汁味儿混着大白菜的霉味飘满院子。文婷推开家门,母亲李桂兰正蹲在水管边洗碗,藏蓝涤卡罩衫卷到手腕。她一抬头,看见文婷怀里的玉强,愣了三秒,抄起手边的蓝边瓷碗就摔在地上,碎片四溅。 “你个死丫头!知不知道廉耻?带个野孩子回来,街坊四邻咋看咱家!”文婷低着头,玉强吓得缩在她怀里,抓着她棉袄上的深蓝补丁不敢吭声。 文婷咬咬牙,鼓起勇气说:“妈,这是我儿子,玉强。他没爹,但我得把他养大。”李桂兰气得手指戳着文婷额头,骂得更凶:“你爹走得早,我拉扯你这么大,你就给我带个这回来?” 胡同里邻居探头探脑,文婷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像被刀刮。她抱着玉强回了屋,窑洞里带回的粗陶碗被她紧紧攥在手里,像在陕北熬过那些苦日子的见证。 可到了晚上,气氛却变了。文婷做好了鸡蛋打卤面——北京人接风的规矩。玉强小口吃着,眼睛盯着桌上的煤油灯,像在陕北窑洞里看惯了的那盏。李桂兰没说话,默默端起碗,夹了一筷子面给玉强。 吃完饭,她突然从兜里掏出一块陕北灶糖,塞到玉强手里,低声说:“吃吧,甜的。” 文婷愣住了,眼泪差点掉下来。她想起在陕北,李强夫妇每次过年都会给玉强塞灶糖,说是“甜了日子,娃就不苦了”。 那天夜里,玉强睡在炕上,裹着文婷从陕北带回的羊毛毯,呼呼大睡。李桂兰坐在煤炉边,盯着火苗,低声问:“孩子爹咋回事?”文婷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他是个好人,村里民兵,去年山洪没了。我没嫁他,但他留了这个娃给我。” 她没提那段感情的细节,只说孩子是她拼了命要护住的希望。李桂兰叹了口气,没再骂,起身拿了条旧毛巾,帮玉强擦了擦嘴角的灶糖屑。 第二天,胡同里公厕排队的人群里,玉强第一次见到抽水马桶,吓得哇哇大哭。邻居大妈笑着说:“城里娃,咋还怕这玩意儿?” 李桂兰没好气地瞪了邻居一眼,抱起玉强说:“我外孙,怕啥?慢慢学!”文婷站在一旁,看着母亲的背影,心里像卸下了一块大石。她知道,母亲嘴硬心软,这句“我们一起把孩子养大”,是她能给的最大宽容。 1976年的北京,胡同里依旧是煤炉烟和冬储白菜的气味,文婷却觉得比陕北的窑洞多了几分暖意。 玉强慢慢适应了城里生活,学会了用筷子夹卤面,也不再怕抽水马桶。文婷找到一份工厂的工作,母亲李桂兰每天早起给玉强做早饭,偶尔还念叨:“这娃长得俊,跟你小时候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