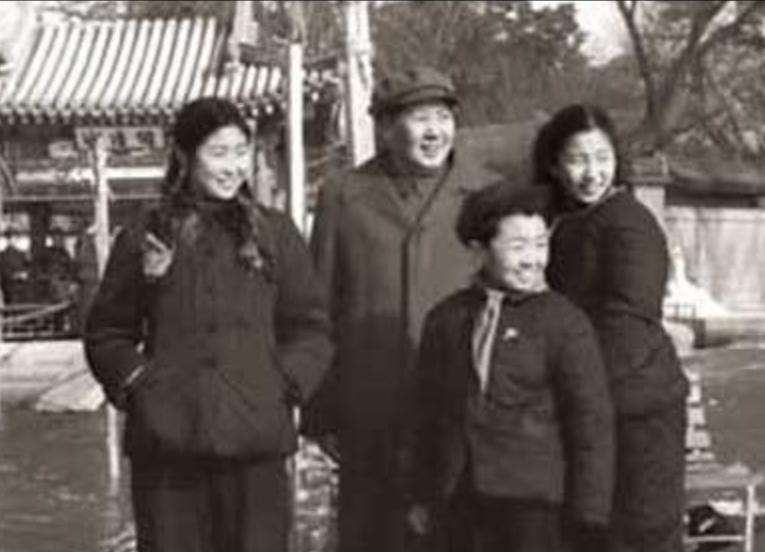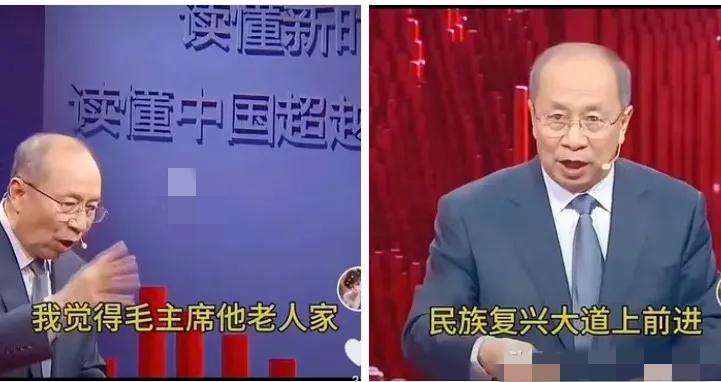1972年,李讷生娃后写信请求爸爸接济8000元,毛主席看罢来信后,心痛不已,指示张耀祠:“不用批什么条子了,直接给钱,你说说看,该给多少钱?” 1972年,李讷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她没有用官话,也没讲什么大道理,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了一件事:孩子出生了,手头紧,想问爸爸接济点钱。她没开口要多少,也没有讲得多凄惨,但字句间都是“没法熬”的那种生活气息。一个离了婚的母亲,一个在干校劳动三年、性子又倔又自尊的女人,愿意给父亲写这封信,其实已经是低头了。 毛主席收到信以后没马上表态。他坐着,一动不动,眼睛盯着那纸信,沉默了很久。屋子里没人敢出声,只有一旁的张耀祠在等着,看得出来,那封信不是普通的家信,也不是工作报告,是家事,也是心事。 沉默过后,毛主席开了口,说话还是老习惯:“不用批什么条子了,直接给钱。”然后又补了一句,“你说说看,该给多少钱?”他没问“她怎么搞成这样”“单位有没有照顾”,也没翻出那些过去讲过的家风。他那一刻就是一个心疼女儿的老人,语气轻得像怕惊着人。 张耀祠试探着说了句:“八千?”毛主席点头,就这么定了。 八千块,那时候是个天文数字。普通职工一个月工资也就五六十,一年也不过六七百,八千块,相当于十几年收入。而且这不是从什么公家款里拨的,是毛主席自己的稿费。他一辈子收入不多,生活节俭,日常开销少得可怜,稿费是他为数不多的私人资产。 更让人心里一动的是,这八千块的“审批过程”完全绕开了制度,毛主席一句话,钱就拨出去了。他没走条子、没过组织、没打报告,只一句话:“直接给钱。”这不是不守规矩,是在他心里,家事就该是家事,女儿的苦难,不需要太多程序。毛主席懂得规矩,但这一次,他选择放下规矩。 这封信、这笔钱,背后是毛主席与李讷几十年父女关系的缩影。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能心口如一地表达爱,更别说他这样一个习惯压抑情绪、处事一丝不苟的老人。他那一代人,特别是像他这样的政治人物,讲原则讲公私分明讲“干部子女不特殊”,但在晚年,情感总还是会跑出来。 李讷从小就在父亲身边长大,但并不被娇惯。她进军报做编辑,起初也算顺利,可有一次毛主席听说她在报社“主抓工作”,很多人见她还要敬礼,顿时警觉了。他问:“她现在是什么干部?”得到确认后,他直接决定调走李讷。 他的理由简单:一个年轻女孩,没基层经验,涉世未深,怎么能承担要职?哪怕是自己的女儿,也不能走捷径。 没过多久,李讷被安排去了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干校的校长是毛主席的亲戚曹全夫。虽然有亲戚照应,但那种地方,天寒地湿、劳动强度大,怎么都不算轻松。李讷没有叫苦,埋头干了三年,就是不回北京。 她不是不想家,是不好意思。她觉得自己那场草率的婚姻算是辜负了父亲的信任。那年她从干校写报告申请结婚,毛主席当时还挺高兴,追着身边人问那位小徐是个啥样人。小徐是服务员出身,人老实,毛主席本就希望女儿找个普通人,感情好,别被家庭背景裹住。 他在结婚申请上郑重写了“同意”两个字,那是对女儿信任的背书。但结果,婚后俩人矛盾重重,性格不合,终究离了。李讷怀着孩子,一个人过,面子上过不去,感情上也过不去,所以她不肯回北京,也不主动联系父亲。那封信,是她为数不多的低头,是生活逼得没退路了。 毛主席知道得也晚。还是江青告诉他的,说李讷离婚了,孩子出生了,一个人过得艰难。毛主席听了没发脾气,也没说“她自作自受”,只是说:“给远志、全夫打个招呼,让讷娃回家吧。”他说得平静,可那语气背后,是藏不住的心疼。 只是李讷太倔,还是不肯回。最终还是毛主席让张耀祠专门跑一趟江西去看她,张耀祠回来说了实情,才有了那封信和那八千块。 毛主席其实一直惦记她。1973年,他八十岁生日,一家人都到场了,李敏、毛岸青的孩子们都来了,热热闹闹。可毛主席坐在椅子上,忽然自言自语:“讷娃好久没回家了,还不知道能不能见到。”李敏听了吓一跳,赶紧安慰他:“爸爸,别说这种话,等妹妹回来了,咱们一起过生日。” 毛主席没再说话,端着杯子,眼睛看着远处。他可能在想,那封信寄出之后,李讷过得好不好?孩子吃得饱吗?晚上睡得暖吗?她一个人扛着,是不是太苦了? 等到1974年,毛主席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李讷听到消息,才急急忙忙赶回北京。一进屋,她就看见父亲瘦了很多,脸色苍白,气息也不稳。她扑上去抱住他,两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问:“娃娃,你怎么不回北京看看爸爸?你是不是恨爸爸,对爸爸有意见?赌气了?” 他不是责备,是自责。他知道自己这些年管得严,话说得硬,面子上不给女儿留情面。可现在,他只想知道,她是不是恨他。 李讷摇着头,眼泪一把一把地掉,说:“我不要离开爸爸了。” 毛主席听完,点点头,笑了,说:“爸爸再也不让讷娃离开了。” 那一刻,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没有政策,只有一个老父亲和他的女儿,像普通家庭一样,坐在床边拉着手,互相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