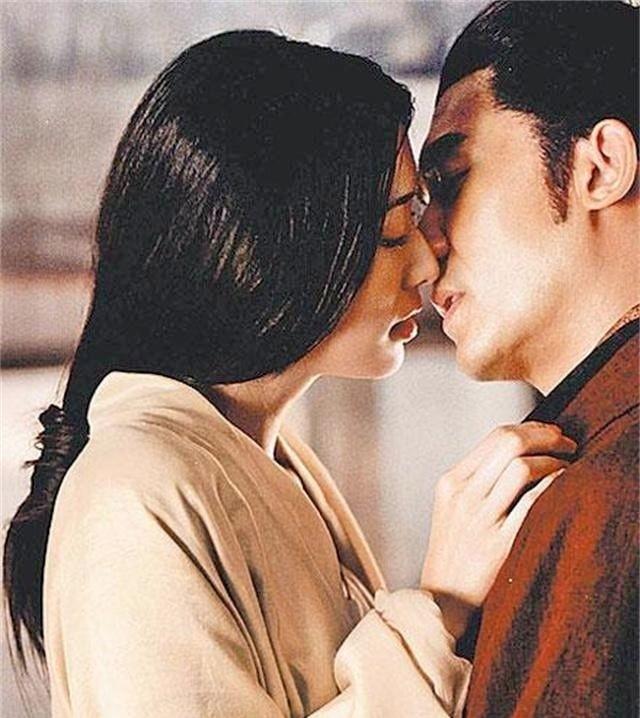公元200年,割据江东的将领孙策在丹徒遇刺身亡,时年二十五岁。其妻大乔(本姓桥)悲痛之下欲自尽相随。孙策之弟孙权(时年十八岁)立即上前制止,并提醒大乔孙策临终遗言是嘱咐他照料好嫂子。大乔因此放弃了自尽的念头。 孙策突然死亡,其政权面临严重危机。他虽已占据吴郡、会稽、丹阳、豫章、庐陵、庐江六郡,但根基未稳。丹阳郡的山越部族对孙氏统治时有反抗;庐江等郡的地方豪强大族并非完全归心;北方强敌曹操的势力虎视眈眈,其使者已出现在江东边境的柴桑。年仅十八岁的孙权继位后,首要任务是稳固内部。他深知,若大乔自尽的消息传开,会被内外敌人解读为孙氏集团人心离散、统治无力的信号,极易诱发山越起事、豪强离心甚至曹操趁虚南侵。因此,阻止大乔殉情是关乎政权存亡的关键政治决策。 数日后,孙权下令将大乔迁往远离权力中心的上虞县(今浙江上虞)居住。官方理由是给予清净环境。上虞的别院为孙策生前购置,临曹娥江。孙权安排众多侍女及护卫随行,名为侍奉保护,实则构成严密监管。此举的根本目的是消除“孙策遗孀”这一身份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防止任何内部反对势力或外部敌人利用其特殊身份制造事端,挑战孙权权威。大乔仅携少量个人物品移居,其中最重要的是她为孙策缝制的青铜护心镜和一件孙策带血迹和泥土的旧战袍,这泥土被认为来自其故乡皖县(今安徽潜山附近)。 孙权执掌江东后,面对内忧外患。他首先必须巩固自身地位,尤其是镇压丹阳郡山越(如公元203年建安八年的重大平叛行动),并慑服其他潜在的豪强反抗者。历经多年经营,他最终稳定了江东局势,于公元229年正式称帝,建立吴国。 在对兄长遗属的政策上,孙权存在双重性。他铭记孙策托付,故在物质上给予大乔远超规格的优厚俸禄,保障其富贵生活。然而,在政治上施加严格限制,始终禁止大乔返回权力中心建业(后为吴国都城)。当重要谋臣如张昭委婉建议安排大乔改嫁时,孙权以遵从兄命为由直接拒绝。其深层考虑是避免大乔再婚后,其夫家可能借助其身份涉足或影响孙氏权力核心,引发新的政治漩涡。 对于孙策唯一的儿子孙绍,孙权的安排更为微妙谨慎。孙权赐封孙绍为“吴侯”。这一爵位在名义上极为尊崇(与孙权称帝前爵位相同),但实质仅为空衔。孙绍未获得任何封地或实际权力(如担任郡守、将领等职务),继续留在上虞跟随儒生读书学习,完全被隔绝于军政事务之外。孙权此举意在最大限度降低风险——避免孙策之子天然的继承法理身份(作为奠基人嫡长子)被不满孙权的势力或野心家所利用,举其旗号挑起内乱或分裂。孙权以巨额财富供养侄子,却完全扼杀其参与政治的任何可能性。孙策生前曾筹划经海路远征辽东(今辽宁),将此视为重要战略目标,但未及实施。孙权虽在书房地图上标记辽东,但终因地理障碍与国力所限,吴国未能实现这一目标。 大乔在曹娥江边别院度过了漫长余生,约四十五年。她亲身经历了儿子孙绍的成长、婚姻、生养儿子孙奉等人生大事。孙权称帝后,曾循例派人送来贵重礼品如锦缎、名贵食物等。其中较为特殊的一次礼物是一尊白玉雕刻的孙策坐像,工艺精湛。大乔将此玉像置于居处常伴身边。其日常生活平淡,主要关注点在于院中桃树花果和孙辈孙奉的成长情况。 公元252年(吴太元二年),吴大帝孙权在都城建业病逝。临终前,他在病榻上对太子孙亮(后继位为吴少帝)郑重嘱托:“切记,江东基业,是你大伯(孙策)和朕(我)用性命换来的!” 这句遗言正式确认并公开强调了孙策作为江东基业共同创立者的历史地位,同时宣告统治权完全归属孙权一系子孙传承。 约半年后,孙权去世的消息传到上虞别院。时值寒冬,曹娥江水流冰冷。不久,大乔在别院去世。去世前,她将珍藏的孙策玉像及青铜护心镜放入自己的棺木中。据后来侍者称,她身着当初嫁与孙策时所穿的旧红嫁衣入殓。其遗物中发现一张墨迹淡 退的字条,上书:“皖县的桃花,该落了。” 这被认为是她对已逝故乡和故人的隐晦感慨。 孙策家族的血脉并未因其曾孙的出现而延续。其孙孙绍早逝。孙绍的儿子孙奉(孙策曾孙),在吴国后期(约在景帝孙休永安年间后期或末帝孙皓初年)的残酷政治斗争中,被人指控参与谋反。当时的统治者下令将其逮捕并处死(诛杀)。孙奉的死亡,标志着孙策的直系血脉后嗣至此彻底断绝,其家族谱系最终消亡于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