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5年,大唐朝廷准备削藩,却发现国库没钱了,唐武宗只好找西明寺借钱10万贯。事后,唐武宗越想越困惑,我堂堂朝廷,居然用天子的脸面和朝廷的税收做抵押,去找一座寺庙借钱,寺庙到底有多少钱?这样的寺庙,天下到底有多少座 搁在平时,天子借钱是天大的笑话。可那会儿的大唐,确实难到了这份上。藩镇割据多年,河北的几个节度使压根不向朝廷交赋税,江南的盐税、茶税又被贪官层层克扣,国库的存银连给边军发三个月军饷都不够。削藩要打仗,要买粮草,要赏将士,哪样都得花钱,宰相李德裕翻遍了账本,最后红着脸跟唐武宗说:“西明寺……或许有余钱。” 西明寺可不是普通的寺庙。它在长安朱雀大街旁,占了整整一坊地,寺里的大殿用的是紫檀木,佛像贴的金箔厚得能照见人影。更要紧的是,寺里的“长生库”(也就是寺庙的钱庄)比朝廷的国库还红火。长安城里的富商、官员,甚至皇亲国戚,都爱把钱存到这儿——一来寺庙有佛祖“护佑”,不怕被偷被抢;二来利息比官办的钱庄高,存一年能多拿两成利。 唐武宗派去借钱的宦官回来讲,寺里的和尚们却不慌不忙,住持指着库房里的架子说:“陛下要10万贯,现成的铜钱有8万,剩下的2万,拆两座银菩萨就够了。”这话传到宫里,唐武宗攥着茶杯的手都在抖——一座寺庙,居然能随手拆银菩萨凑钱,那藏在暗处的财富得有多少? 他睡不着了,连夜叫李德裕进宫,让他悄悄查天下寺庙的家底。这一查,查出的数让君臣俩都倒吸凉气。 就说土地吧。西明寺在关中就有良田千顷,租给百姓种,每年收的租子够养活五千人。五台山的寺庙更厉害,把周围的山林、煤矿都圈了起来,光是烧炭卖钱,一年就有30万贯进项。江南的阿育王寺更绝,占了宁波港一半的码头,南来北往的商船靠岸,都得给寺庙交“香火钱”,说是保佑平安,其实跟收税没两样。 除了土地,寺庙还做买卖。长安西市一半的绸缎铺、洛阳南市的瓷器行,背后都有寺庙的影子。和尚们不亲自抛头露面,找几个俗家弟子当掌柜,赚了钱就往“长生库”里存。更让人咋舌的是放贷,百姓家里急用钱,拿地契、农具做抵押,向寺庙借钱,利息比官府的“青苗钱”高两倍,到期还不上,家产就归了寺庙。有地方官上奏,说有些村子,十户里有八户都欠着寺庙的钱,日子比给藩镇当差还苦。 李德裕把各地报上来的册子堆在唐武宗面前:“陛下您看,天下像样的寺庙有3万多座,小的庵堂、佛龛更是不计其数。光是登记在册的僧尼就有26万人,这些人不用交税、不用服兵役,还占着全国十分之一的土地。” 唐武宗翻着册子,看到江南一座寺庙的账:“奴婢500人,战马30匹,商铺20间,铜钱百万贯……”他猛地把册子摔在桌上:“这哪是寺庙?分明是一个个小朝廷!” 他想起刚登基时,去法门寺拜佛,见寺里的和尚穿的丝绸比公主还好,用的茶具是金银打造的,当时只觉得佛门富贵,现在才明白,这些富贵都是从百姓和朝廷手里抢来的。百姓宁愿把地捐给寺庙当“香火田”,也不愿交给官府,因为寺庙不用交税;商人把钱存进“长生库”,朝廷收不到商税;连打仗急需的铁、铜,都被寺庙拿去铸佛像、造法器,市面上的铁器都快不够用了。 “难怪国库空,”唐武宗盯着李德裕,眼神冷得像冰,“钱都进了这些地方。朝廷要削藩,要保江山,总不能指望菩萨显灵吧?” 李德裕低着头,没说话,但心里清楚,陛下这是动了真格的。 没过多久,唐武宗下了道圣旨:清点天下寺庙财产,僧尼中凡无度牒(官方凭证)的,一律还俗;寺庙占有的土地,超过规定数额的,全部收回;“长生库”不得再放贷,存银由官府监管。 西明寺的住持接到圣旨时,手里还攥着给唐武宗的“借款利息单”,这下彻底傻了眼。各地的寺庙也慌了神,有的偷偷把金银埋进地下,有的赶紧把土地还给百姓,可大多为时已晚。 这场后来被称为“会昌灭佛”的运动,让朝廷一下子收回了良田数千万顷,还俗的僧尼成了纳税户,国库渐渐充盈起来。唐武宗站在城楼上,看着漕运的粮船源源不断开进长安,总算松了口气——他不是要跟佛祖作对,是要把本该属于朝廷和百姓的东西,拿回来。 出处:《旧唐书·武宗纪》《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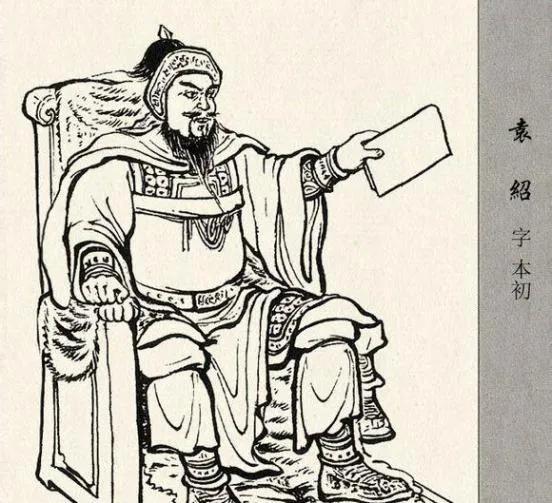








漫漫长路一路有你
少林寺交不交税
清水鸡 回复 08-15 23:10
交个毛税
大鱼 回复 09-30 05:44
你首先要明白一点:少林寺和少林寺管理处是两个概念!你的门票钱是管理处收的,旁边的产业,店铺租金也属管理处,与和尚没关系;香油钱才是和尚的(记住,协会还要收钱)!这也是释永信搞事业的初衷,他不搞事业,真要穷死!
东哥在三峡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庙多王八多!
沙漠雨 回复 08-10 16:25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雾中
用户10xxx05 回复 沙漠雨 08-17 15:50
烟雨中
仰望苍穹
寺庙的钱要管起来,也要收支2条线,70%做慈善,30%自己发展,多余的钱进入佛教协会的基金。
ZACH 郑 回复 08-12 23:22
国家宗教应该把功德箱取消掉,禁止寺庙收取香火钱,和尚想给佛祖搞金身可以打工做生意自己种田
小菜一碟 回复 08-14 10:42
阴阳帐簿见过吗
手持式喷筒
不劳而获假正经
四川印象
现在的喇嘛寺庙,一个比一个豪华,那些喇嘛开的豪华汽车,过着纸碎金迷的日子,信众把一生大部分积蓄都捐献出来,大部分信却过得紧巴巴的日子,国家真的该整治一下!
苍穹 回复 08-11 12:47
对,现在喇嘛庙收入才高呢!
木木 回复 08-12 12:04
什么现在,而是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用户99xxx87
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一般的只有“穷和尚”一说,但是变成“富和尚”那就只能饱暖思淫欲了。
云与山
香花钱不交税的!
乔与艳合 回复 平志雄 08-14 22:22
菩萨的钱大家拿点菩萨不会介意吧
平志雄 回复 08-13 07:58
菩萨的钱不能收税
用户10xxx93
这些寺庙难道不该统一清查吗
用户10xxx24
和尚交不交税?少林寺占地交不交
自由的风 回复 08-10 15:58
收的捐款是免税的。经营收入是交税的,不过也有优惠
今夕何夕 回复 08-10 12:33
上市公司必须缴税
朕的大好江山
大家可能不知道,香钱不用交税,香客不光捐钱,还有的捐地,这地也不用交税,于是就有一些地主乡绅和寺庙搞起了挂靠,还有一些通缉犯躲进寺庙里,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往不咎,于是乎成了护法金刚,所谓天下武功出少林,这天下武功就是侠以武犯禁的通缉犯带去的,这么一个组织,那个政权容得下[滑稽笑]
真的是我
一个发源地本土都被唾弃的宗教,倒是在这风生水起~
用户10xxx92 回复 08-11 08:41
近臭远香嘛,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鼓掌]
tb26384_44
可惜的是武宗短命,政策没几年,宣宗上台后又崇佛了,武宗做的不过是往炭火泼水,只刹那压下去,没灭干净,复燃后火更胜从前了。
用户10xxx14 回复 09-07 07:39
灭佛报应了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朝旭哥
暗藏春色,藏污纳垢之地!
山衔好月来
农夫与蛇,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螳捕蝉。
用户14xxx44
唐武宗也是一代人杰。可惜了,就是寿命太短。
用户10xxx14 回复 09-07 07:39
灭佛报应了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卫可孤
没几天武宗死于非命,佛爷说这是佛祖的惩罚
和平使者 回复 08-11 13:03
佛爷个毛线,佛教没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就没生老病死了?
荒岛星晴 回复 08-11 08:24
真的假的啊
上分
呵呵,我这边的寺庙,是这边最大的民间放贷机构,多少上市公司,不去银行借贷,就喜欢到寺庙借,历史总是不停在重演,,,
往事随风
人怕出名猪怕壮!
百事可乐
一帮该死的寄生虫
大爷
藏污纳垢,暗藏春色之所
一个老头
削减现在佛寺的规格。
招财猫
释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要做到全球连锁,世界五百强😎
辉煌
历史的规律,社会稳定富裕促寺庙更富裕,再发展下去就是社会越来越穷寺庙越来越富,然后是朝廷下令清算寺庙,如今的寺庙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能清理清理。六根清净就是一个笑话!!!
戬一
无本生意
风和日丽
少林寺的香油钱要交税吗?
yangmanzhong110
少林寺收人干活不纳税不交社保?这个不可忍受!先从社保交起!
用户33xxx36
从古至今寺庙就是最大的放贷机构!不事生产喝人血的!
用户10xxx07
寺庙到底是寺庙还是企业?
小蛋蛋的小白兔
释永信:缴税?什么叫缴税?
海阔天
可以考虑全国寺庙收归国有了
灰大狼 回复 09-25 08:38
现在都是国有的
启航贸易收服装鞋包布料
佛本来就是外来户,只会骗,还是道家好
琴心弦音
看古通今,寺庙就像现在的平台app,你不通过这些app难以和佛祖建立沟通。只有交了服务费(香火),才能乞求平台给派送服务。如果交的足够多,甚至还能办个会员(挂名)。一般情况是,想找佛祖办多大事,就交多大的服务费,而这些香火钱,最后却没到店铺(灵山)和快递员(菩萨)手里,都被平台(寺庙)留下了……。
用户10xxx20
战乱,道教出世,和平,道教归隐
用户10xxx96
不劳而获还不用交税,辛辛苦苦工作一分税都少不了[哭笑不得][哭笑不得][哭笑不得]
以后再说
应该规定无论什么宗教,一个省自治区只能保留一个寺庙
用户10xxx97 回复 08-11 05:16
且不允许收门票!
星河长老
佛门之地,成何体统!
司徒有虚名
封建王朝到后期都出现了财政危机
天朝理科生
唐武宗最可惜的就是只活了31岁,在位6年。
饥寒交迫的奴隶
现在的少林寺和尚,主持等一和尚就妻妾成千上万,真正的人民,却没钱娶老婆,断了子,绝了后!
往事如风
这就是古代神权从来没有干赢过俗世王权的原因。
元一
会昌法难不是寺庙有多有钱,而是寺庙争夺了人口资源,这在佛学界是有定论的,也被认为是必然的,是社会进益的一种表现
用户10xxx35
少林寺也要交税、纳税,和尚要交社保。(黑旋风)
喷毛子加钱喷乌鸡系统扣钱
佛曰四大皆空,佛曰自带香烛无福报
wangjyyh
,“钱都进了这些地方。朝廷要削藩,要保江山,总不能指望菩萨显灵吧?”他不是要跟佛祖作对,是要把本该属于朝廷和百姓的东西,拿回来。
墨雨狼烟
释:这关我啥事?小编:不要对座入号
芦苇
和尚已经是职业了
联合论坛
少林寺交睡!
用户16xxx14
想当和尚的没关系可不行!
花丛里的少侠
国家也应该约束下寺庙,看看人家道观就怎么就没有那么多事
柯力2008
如果拜佛有用的话,你都进不了门。
我爱钓鱼
呵呵,给寺庙佛像捐钱本身就是一种贿赂行为,捐钱给佛保佑自己实现心愿,
玄和
现在的寺庙一样有无数钱财,并且不纳税!
用户10xxx66
唐武宗英明!
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
和大得高僧永信方丈比还是略输几筹了
用户98xxx26
寺庙交个毛线税,社会蛀虫
ZACH 郑
宗教最恶心,无本生意,信徒过来就给钱,基督教收20%!佛教有多少要多少!重点是还不用交税
沙滩
所以这群和尚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好处?
我爱钓鱼
呵呵,给寺庙佛像捐钱本身就是一种贿赂行为,寺庙收钱办事,
用户18xxx30
严查相关信仰的教义,比如佛教,是不是有金钱戒,不食荤素的戒,如果有,严查,凡是违反相关教义的和尚,先依照相关的戒律来处罚,然后取消身份度牒,强制还俗,处置方式参考虚竹,先打五十板子,然后革除和尚的身份,这个事情相关的监管部门有在做吗?
言尔有信
少林寺 问一下释永信, 他应该有耐性回答你。
真彭
流氓借钱不还还杀对方全家,观众还都鼓掌叫好。
用户15xxx44
有的寺庙佛像要镀金身,为啥用金子呢?
A风雨无阻
看来寺庙的事情,自古有之
追梦人
所以富不漏财,低调做人
光良
寺庙收信徒税[哭笑不得]
用户10xxx92
寺庙好像确实有庄园的
我心飞翔
寺庙的钱,除了你日常伙食费和维修费外,应全部上缴
无所畏惧
简直胡说八道,唐代有宁波港?
琪乐融融
是应该把不良寺庙和贪官的钱财全部没收[开怀大笑][开怀大笑]
国友
可惜。武宗在位时间很短,就病逝了。
以后
普陀山去查查
用户10xxx21
所以寺庙要收归国有资产。
天也蓝了
禁止佛教吧!除非真的和尚!
用户14xxx25
佛看不上这些俗物,心诚就行了,没必要花钱
陈刚
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元甲
哪个文明哪个时代哪种寺庙,到最后不是把宗教信仰变成真金白银?说到底人这种动物,就是希望大多数人都被洗脑,然后他自己躺着赚钱!!!真正的人间清醒又有几人?除了熟读史书了然人性的!!!
看把你能的
可惜,中晚唐有几个有作为的皇帝偏偏就活不长,刚有好转局面又给中断了
paradise
宗教机构应该和ngo一样都要注册,机构和人员都要交税
大莫
宗教收入都不交税,也不监管,全凭以我修养。
用户10xxx37
寺庙应该收所得税,按照赠予收取,,人家继承爹妈都收,,光头凭什么不收
安然
所以唐武宗活不长了
万旺
和尚也是人啊,也有七情六欲的。
9772
人工智能判断事物只有对错,不存在别的
BOBO
佛教就是个山寨阿三的印度教,进寺庙拜佛等于拜阿三
混世牛魔王
关百姓什么事了吗?
梅吻画
只要跟铜臭沾上边的地方,就谈不上什么清净之地
爱吃鲶鱼
曹德旺不是搞了一座庙么,想想是什么流。
身未动心已远
所以大和尚被抓了
巨石灵王
唐武宗就是主持正义的佛!
红尘逍遥客
借钱的都是大爷[点赞]
注销此号求方法
寺庙买香火上香是要开发票的有记录,但是功德箱是自愿投的,投多少自愿这个一般不记账,不开票不收税。一天收多少,只有寺庙每天清点的自己知道。
jnsong
福建那边租寺庙发佛祖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