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19岁的女大学生,父亲去世,被继母卖给53岁的陈老爷,做四姨太。女学生没坐轿,走到陈家。晚上,女学生要侍寝,老嬷嬷给她捶脚,她不习惯,老爷说:“女人脚舒服了,才能把男人伺候好!” 民国时期,那叫一个乱啊,传统跟现代跟说相声似的,你来我往。在北平有那么一座大院,里头住着位19岁的女学生颂莲,原本家里挺有钱,老爹一死,家道中落,继母为了还债,干脆把她打包送给了53岁的陈老爷,做了四姨太。颂莲这姑娘有骨气,愣是没坐轿子,自己溜达进了陈府,这算是她对自由最后的倔强。 颂莲,读过洋学堂,课本里印着“天赋人权”“男女平等”,兜里还揣着半本《新青年》。她爹是前清秀才,后来开了家书局,教她念诗写字,说“我家姑娘不输男儿”。可老爹一蹬腿,继母看着账本上的窟窿,眼睛都红了,陈老爷托人来提亲,说给二十块大洋,继母当晚就把颂莲的课本捆成了破烂。 陈老爷呢,原是前清举人,后来靠倒腾鸦片和地产发了家,院里的青砖地都嵌着金线。他娶姨太跟集邮似的,大太太是结发妻,如今瘫在炕上念佛,见了谁都只说“阿弥陀佛”;二太太卓云,三十来岁,脸上总挂着笑,手里却常捻着根银簪子,据说前几年把个得宠的丫鬟推进了井里;三太太梅珊,原是戏班子的名角,身段软,性子烈,敢跟陈老爷摔茶杯,院里的灯笼,数她屋里亮得最勤。 颂莲进府那天,陈府的灯笼没全挂。按规矩,新姨太进门得亮三天全灯,可二太太说“四妹妹是读书人,怕是不爱这俗套”,陈老爷捋着胡子点头,颂莲心里冷笑,这哪是体谅,分明是给下马威。 头晚捶脚那出,颂莲攥着拳头忍了。老嬷嬷的手跟铁钳子似的,捏得她脚踝生疼,陈老爷坐在太师椅上抽着水烟,眼皮都没抬。等老嬷嬷出去,颂莲忍不住说:“老爷,我自己来就行,学堂里教过卫生,总麻烦别人不好。”陈老爷把烟锅往桌上一磕:“进了我陈家的门,就得守我陈家的规矩。脚是根,根舒坦了,身子才听话。” 往后的日子,颂莲才算明白“规矩”俩字有多沉。 早上天不亮就得去给大太太请安,二太太总拉着她说家长里短,话里话外打听她跟老爷昨晚“说啥体己话”;三太太梅珊见了她,有时会丢块糖,说“别学那些弯弯绕,男人嘛,哄着玩呗”,转头又在陈老爷面前说“四妹妹读的书多,怕是瞧不上我们这些没见识的”。 颂莲试着反抗过。陈老爷让她学打麻将,她偏捧起诗集;二太太送她绣花鞋,她搁在窗台上落灰;最绝的是有回陈老爷要她侍寝,她故意把墨水打翻在被褥上,说“手笨,写坏了字,弄脏了老爷的地方”。 可这反抗像打在棉花上。陈老爷不恼,只让管家把她的诗集锁进库房,说“女人家读那么多书,容易胡思乱想”;院里的灯笼,她屋里的亮得越来越少,有时整月都不亮,下人们见了她,也敢偷懒不请安了。 转折点在那年冬天。梅珊跟戏班的武生勾搭上,被二太太逮着了把柄。半夜里,颂莲听见梅珊的哭喊,还有陈老爷的怒骂,接着是重物落水的声响。第二天,井边围了好多人,二太太捂着嘴哭,说“三妹妹想不开,投井了”。 颂莲站在井边,看着那口黑沉沉的井,突然觉得脚底发凉。她想起头晚老嬷嬷捶脚的力道,想起陈老爷说“脚舒服了才能伺候好男人”,原来这规矩不是让你舒坦,是让你认命,认了命,才不会像梅珊那样,连反抗的资格都被沉进井里。 打那以后,颂莲变了。 她开始跟着二太太学打麻将,牌技越来越好;陈老爷让捶脚,她会笑着说“嬷嬷手法好,比学堂里的体操舒服”;她甚至主动给陈老爷绣了个烟荷包,上面绣着“福寿绵长”。 陈老爷挺满意,说“还是读书人心眼活,懂事了”。院里的灯笼,又开始常亮在她屋前。 可没人知道,颂莲夜里总做噩梦,梦见梅珊从井里爬出来,湿漉漉的手抓着她的脚踝,问“你咋不反抗了?”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啥不反抗了。或许是看着梅珊的下场怕了,或许是继母托人带信说“家里添了新家具,多亏四姑娘”,或许是某天早上照镜子,发现眼里的光,跟大太太念佛时一样,快灭了。 三年后,陈老爷又娶了五姨太,是个刚满十六的小姑娘,怯生生的,见了谁都躲。 颂莲看着那姑娘,就像看见三年前自己走进陈府的模样。 有天晚上,五姨太被老嬷嬷捶得直哭,颂莲正好路过,站在门口说:“忍忍吧,习惯了就不疼了。” 五姨太抬起头,眼里满是疑惑,像在问“为啥要习惯?” 颂莲没回答,转身走了。月光照在她脚上,那双曾经裹在学生布鞋里的脚,如今踩着精致的绣花鞋,走在青砖地上,悄无声息,像从没受过委屈,又像早就没了知觉。 这院里的规矩,就这么一代代传着。新进来的人总想着反抗,日子久了,要么像梅珊那样沉进井里,要么像颂莲这样,把棱角磨平,变成规矩的一部分。 信息来源:本文内容参考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及民国社会史料中关于旧式家族女性生存状态的记载,结合对民国初年新旧思想冲突下女性命运的研究整理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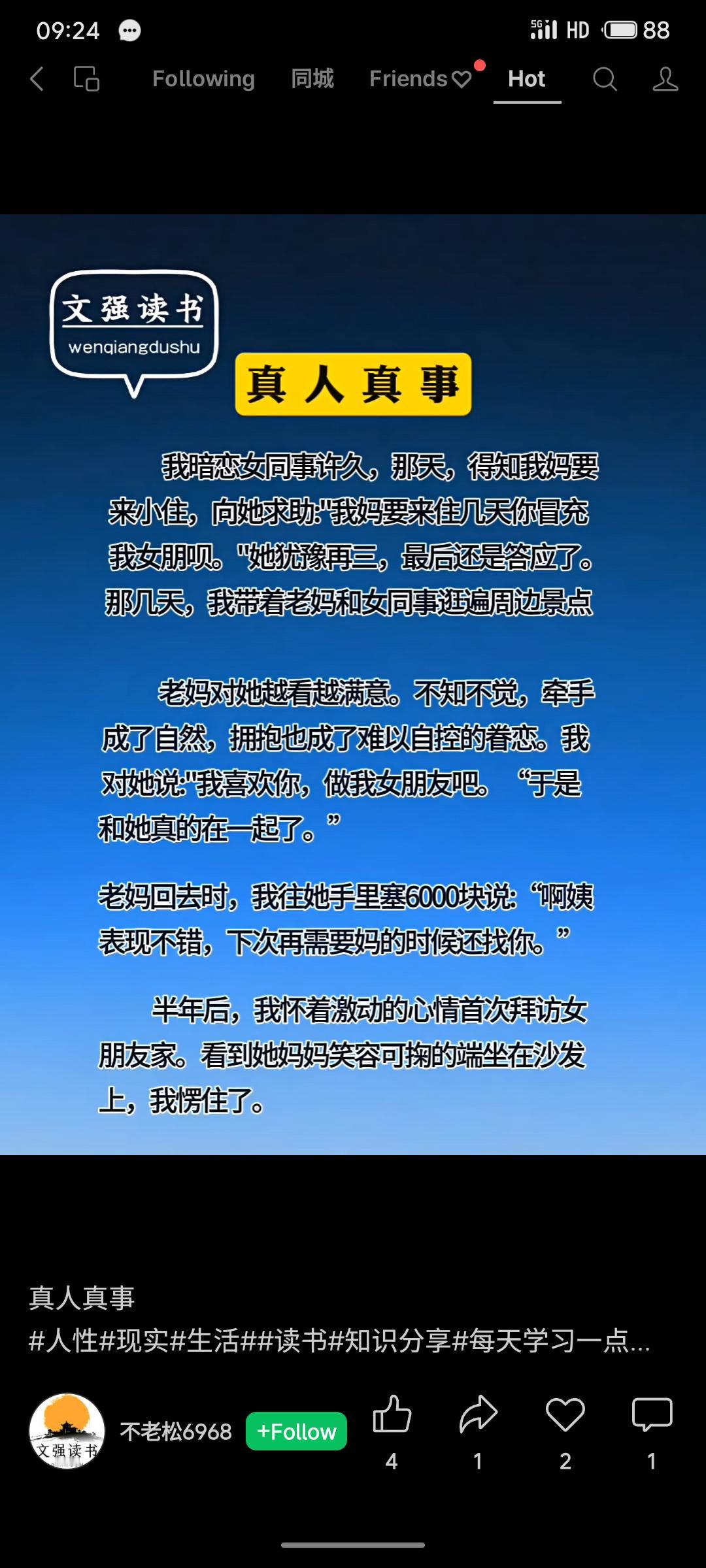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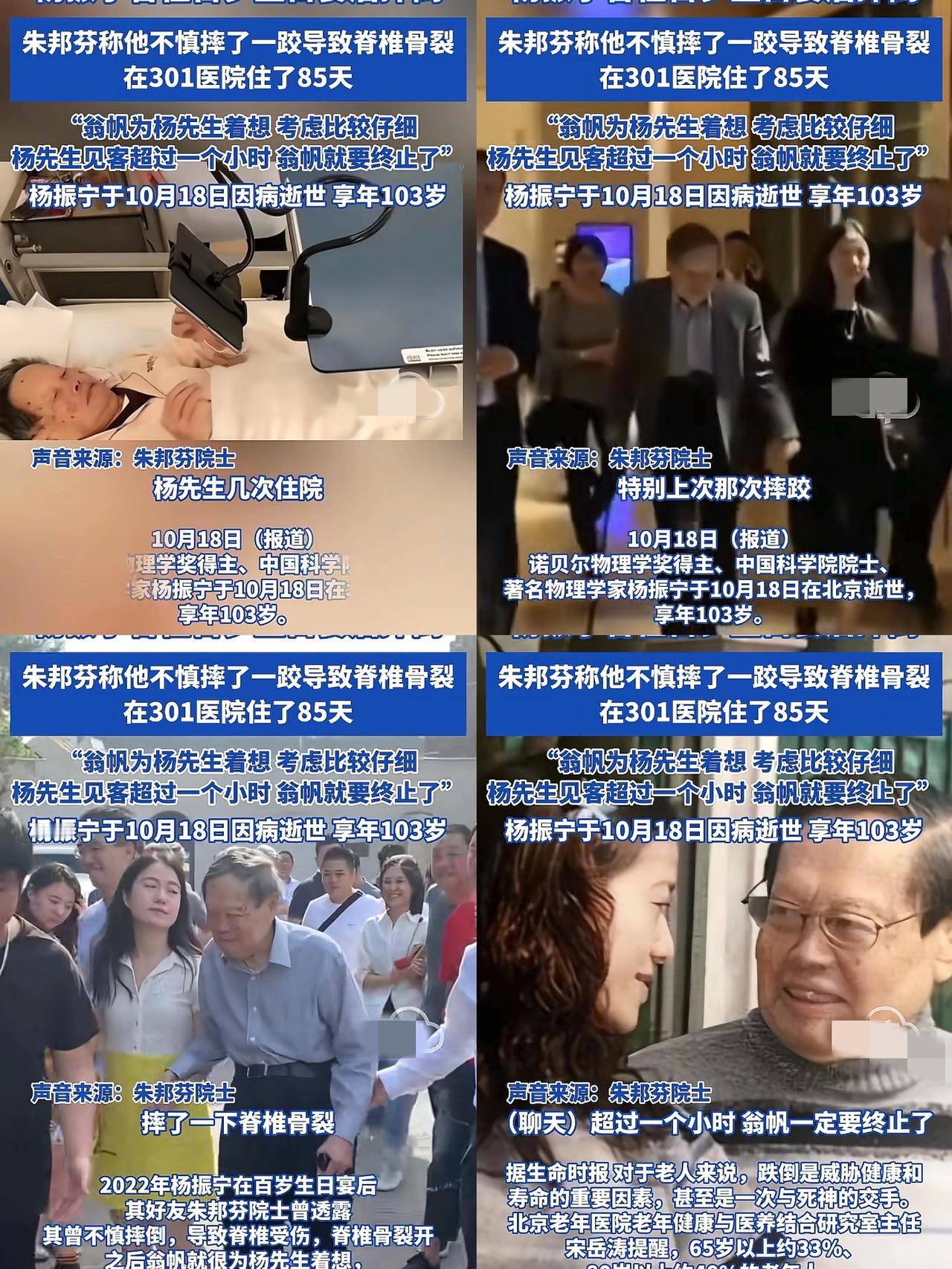

用户10xxx00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片断
习惯孤单 回复 08-10 13:28
我虽然没看过但是我第一反应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用户10xxx97
权利和义务相符……你享受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却去偷人难道不该沉井?20元大洋买了,你可以不卖……
红尘情歌苦中作乐
是孔莉。
红尘情歌苦中作乐 回复 08-19 08:30
谢谢你纠正、我的失误。
石头 回复 红尘情歌苦中作乐 09-04 11:22
怎样豉汁蒸排骨
用户18xxx42
从古到今男人都好像瘫痪了,个个都说要找个女人伺候他
夏紫衣 回复 09-12 18:32
还真是,富贵人家女仆,穷人家老婆,都是底层人民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