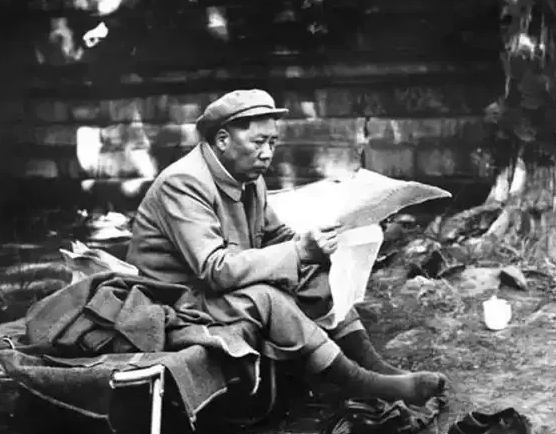1950年,因遭到不公正对待,中国遗传学奠基人李景均毅然离开内陆前往香港,无处可去的李景均,竟然得到了诺奖得主穆勒亲自向美国国务院求情,希望将李景均接到美国!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的香港,对李景均来说就像个牢笼,他带着妻女逃离后,才发现手里没有任何合法证件能离开。 就在他走投无路时,一封登在美国《遗传学杂志》上的求助信,在美国遗传学界掀起了波澜。 诺贝尔奖得主穆勒,一个素未谋面的美国人,竟亲自写信给美国国务院为他求情,甚至准备动身来香港接他。 究竟是什么,能把北大史上最年轻的系主任的顶尖学者,逼到这步田地?故事要从他的第一个重大决定说起。 1936年,李景均拿着家人凑的钱,远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他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现代遗传学,更被杜布詹斯基等学术大牛点燃了热情,把当时还很新的群体遗传学,当成了自己一辈子的方向。 学业有成的同时,他也在芝加哥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和一位美籍华人组建了家庭,那时候,他已经在美国站稳了脚跟,前途一片光明。 1941年,中国抗战最难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逆流而上的决定:回国,但归国之路远比他想的要艰险。 为了躲避日军潜艇,轮船只能绕着走,从旧金山绕到印度,再走缅甸,最后踏上危机四伏的滇缅公路,到了香港,随身带的支票兑不了现,一家人顿时身无分文,幸亏有朋友和当地地下组织帮忙才没困死。 整整五个月的折腾,当他终于到广西大学任教时,人已经瘦得脱了相。 可即便是在战火里,他也没放下学问,背包里永远塞满了书和资料,同事都开玩笑说他是个“移动的实验室”。 不过,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抗战胜利后,李景均的才华得到了认可,年仅34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农学院系主任,成了北大校史上最年轻的系主任。 当时的他,像是要把失去的时间都补回来,白天上课,晚上就在油灯下写书,写出了中国第一本《群体遗传学》,他以为,好日子终于来了。 谁知,一场风暴正等着他。 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传来的米丘林-李森科主义被捧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科学正统,而李景均坚持的摩尔根遗传学,一夜之间被打成了“资产阶级伪科学”和“资本主义毒草”。 他从受人尊敬的学术带头人,变成了被批判的靶子,先是他在农大校务委员会的课被无端停掉,接着,连做研究的实验室都不让他进了。 一次开会,主持的干部竟当众指着他鼻子骂他“崇洋媚外”,脾气倔的李景均气得当场摔了本子,一位苏联专家更是当着二百多师生的面教训道:“你们中国同志搞遗传学,就该跟着我们社会主义阵营走,” 即便如此,李景均还是想做最后的抗争。 1950年,他顶着巨大压力,出版了另一本著作《遗传学原理》,然而,这本书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书刚印出来,就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堆得像山一样的样书,被直接拉到造纸厂化成了纸浆。 学术理想被彻底碾碎,生活也走到了绝路,学校每月只发给他四十斤小米当工资,根本养不活老婆孩子,有一次孩子高烧不退,妻子抱着孩子去医院,却因为掏不出挂号费,只能绝望地蹲在医院门口哭。 1950年春天,他借口回上海探望病重的母亲,带着全家悄悄南下广州,再辗转到了香港,为了不让人起疑,他甚至在家里留下了许多还会回来的假象。 在香港,他收到了国立台湾大学的聘书,但他拒绝了,在他心里,学术自由比什么都重要。 1951年,在美国同行们的倾力帮助下,李景均一家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他在匹兹堡大学从生物统计系教授干到系主任,先后当选美国遗传学会副主席和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他提出的临床试验随机/双盲原则,今天依然是现代医学研究的基石; 1998年,他获得了美国人类遗传学会颁发的杰出教育奖,这是对他一生学术成就的最高肯定。 据说,周恩来总理得知他出走后,在政务院会议上大发雷霆,痛骂了教育部负责人。 到了80年代,国内派人专程请他回国讲学,这位已经满头白发的老人只是摆摆手说:“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了,”一句平淡的话,背后是一道再也无法愈合的伤疤。 2003年,李景均在美国去世,享年91岁。 当年被学生们偷偷藏在抽屉里传看的《群体遗传学》,如今被郑重地摆在图书馆最显眼的位置,烫金的封面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他当年呕心沥血的手稿,也被珍藏在北大农学院的旧址展览室里,供后人瞻仰。 进一步看,也正是这些惨痛的教训,才促使中国后来有了中科院的“百人计划”和教育部的“长江学者”这类政策,就像官方白皮书里强调的,要“以史为鉴,营造尊重人才的良好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