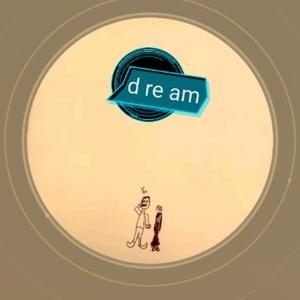上海,陈先生参加社区工作者招考,笔试面试双双通过,政审阶段却因为查出陈先生被记录有精神分裂症患者而受阻,记录显示他患这一“病症”已经十一年了。而陈先生却认为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患精神分裂症,然而这场持续五年的“洗冤”之路,至今仍未走到尽头。 (来源:热度新闻) 2009年,刚入职场的陈先生因人际关系困扰,和母亲一起走进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寻求帮助。“只是想找医生疏导压力,两次沟通都很简单,没做任何仪器检查,更没人说我有病。”陈先生回忆道。 此后他顺利辞职成为教师,结婚生子,考取驾照换发证件,生活从未出现异常。 转折发生在2020年,35岁的陈先生参加社区工作者招考,笔试面试双双通过,却在政审环节意外碰壁——系统显示他是“重大精神疾病管控人员”,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追根溯源才发现,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早在2011年就将他的信息上报至卫健委,依据竟是2009年那次心理咨询记录。 令他费解的是,作为需要重点随访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从未收到过医院的回访,辖区也无相关关怀记录。为证清白,他先后做了多次检查:2020年该院专家会诊称“诊断依据不足”,2021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认定其“目前精神状态正常”,2024年上级医院更是将诊断修正为“急性应激障碍”。 但这些“正名”材料未能撼动原始记录,涉事医院坚持“诊疗符合规范,未误诊”,对于为何时隔两年才上报、未履行告知义务等问题,仅以“时间太长”“系统不完善”回应。 陈先生诉至法院,却因“不属于民事案件处理范围”被驳回,陷入“医院不申请、卫健不受理、法院不处理”的困局。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如何看待此事: 1. 医疗机构的告知义务与诊疗规范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明确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因医疗机构未尽到告知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涉事医院未能举证证明2009年已将“精神分裂症”诊断结果告知陈先生及其家属,且未采取后续治疗、随访等必要措施,明显违反诊疗规范。精神分裂症作为慢性严重性精神疾病,需依据幻听、妄想等典型症状综合判定,仅通过两次口头咨询即下诊断,难以满足医学上的确诊标准。 2. 重大精神疾病的上报与管理责任 《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医疗机构对确诊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应当及时将相关信息上报至所在地精神卫生防治技术管理机构。但上报需以明确诊断为前提,且应保障患者的知情权。 精神分裂症属于法定必须上报的六种严重精神障碍之一,医院虽有上报义务,但在无充分诊断依据、未告知患者的情况下擅自上报,且未履行后续管理职责,已构成行政不作为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3. 政审受阻的法律依据与救济困境 《公务员录用规定》第二十条要求报考者需“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精神病史是否影响录用需结合病情严重程度与履职能力综合判断。但陈先生的核心困境在于,错误的诊断记录导致其丧失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截至目前,陈先生的“精神分裂症”记录仍未撤销,这场横跨十余年的误诊风波,不仅让他错失工作机遇,更给他的生活蒙上阴影。正如他所言:“我不怕承认疾病,但不能接受被‘创造’出的疾病。 对此,你怎么看? 秋日生活打卡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