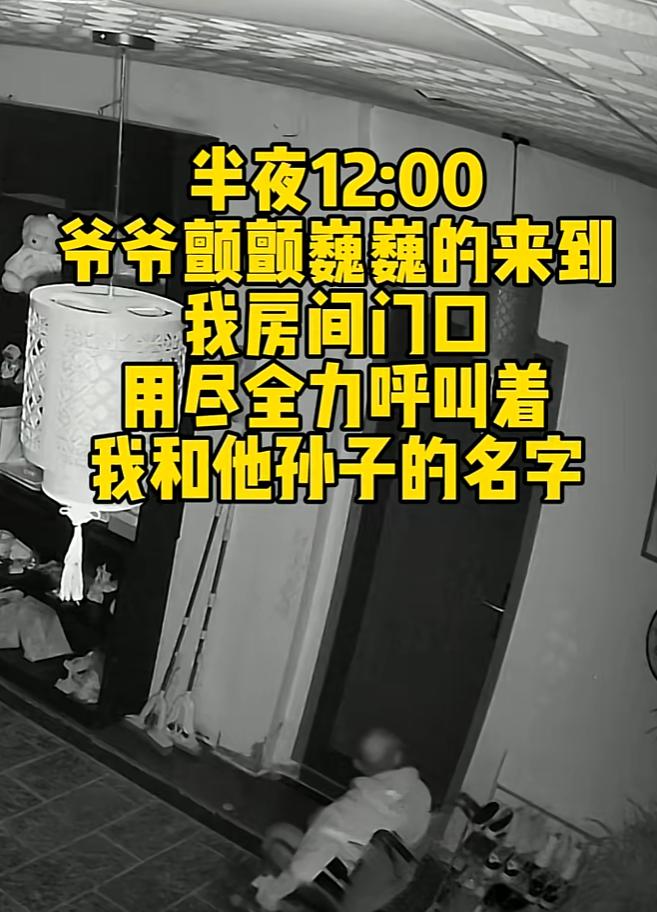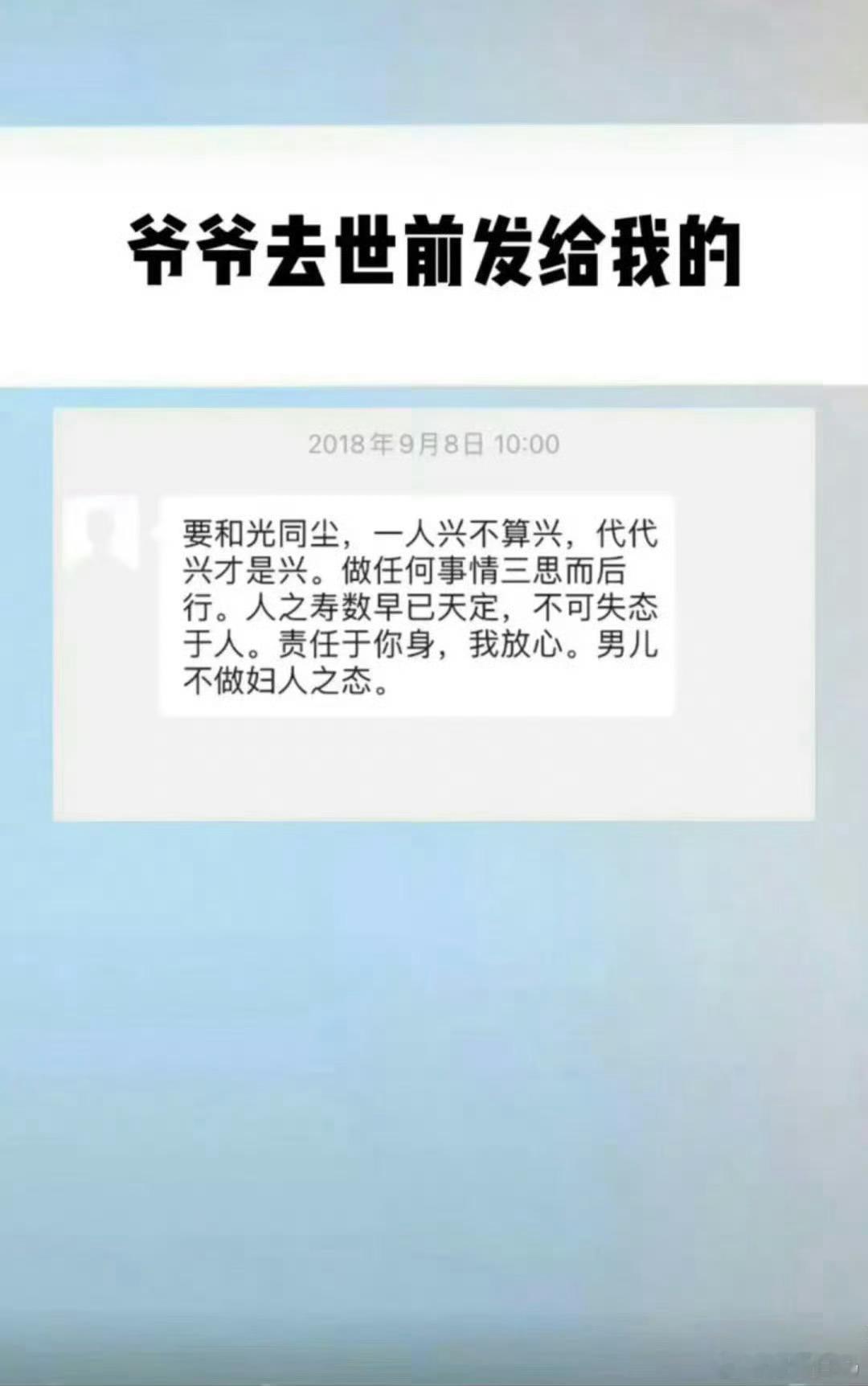今儿回老庄子探亲,一进堂爷爷家院儿就愣了——90岁的人了,正佝偻着腰在压水井那儿费劲往下按,皱得跟老树皮似的手还沾着井沿儿的湿泥,旧铁桶里的水晃荡着,洒在地上洇出一小片黑印子。 进屋更心堵,灶台上摆着半碗剩玉米糊糊,碗边还沾着米粒儿,筷子是裂了缝的旧竹筷。我问他咋不叫孙子来搭把手,老爷子往炕沿儿上一坐,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他们忙哩,我自己还能动。”可我瞅见他起身时,手撑着炕沿儿缓了好一会儿,腿都在打颤。 记得小时候他总揣着糖,见着我们这些小辈就往兜里塞,秋天还爬树给孙子们摘枣。咋就老了老了,连口热饭都没人递?我蹲在院儿里帮他刷碗,水冰得手疼,可心里更疼——这人老了到底图个啥啊?你们说,要是咱老了遇上这事儿,心里得多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