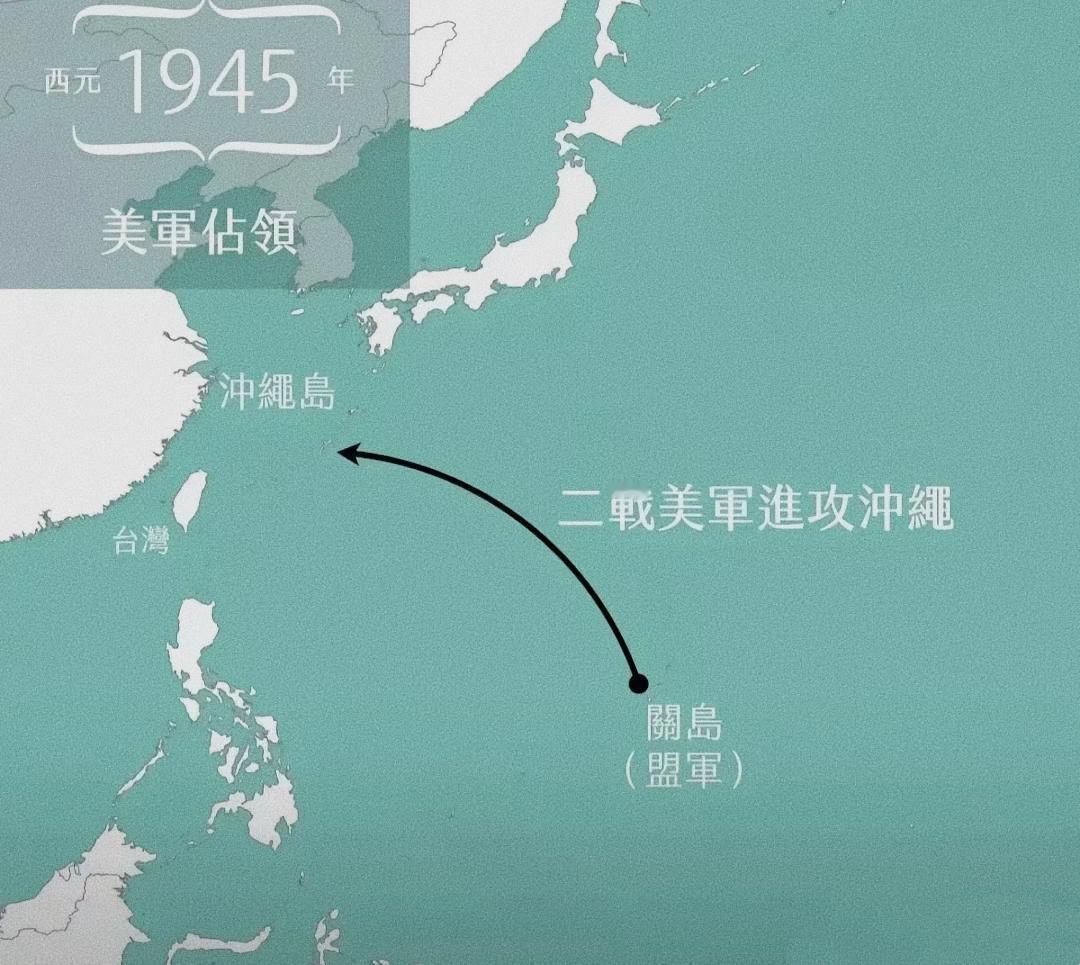近代日本学者的中国观:唯利是图、气质文弱、善于虚言、民风败坏。 他们是怎么一步步看不起中国的,先是尊孔讲礼,后来一句“民风败坏”满天飞,日本近代知识界这一段蔑华的转向,文人开路,报纸开声,课堂跟上,军队落地,甲午仗打完,南京城成废墟,线索都在纸面上能看到。 江户那会儿,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不一样,武士读四书五经,讲孔孟之道,儒学是官学,文人把汉学当底子,不懂汉学不配称人这话有人挂在嘴边,清朝里子已经烂,外面那层还硬着,面子还在,国土摆在那,明治维新之前,东亚这张桌子上,老大哥的椅子还稳。 鸦片战争的信息传过海峡,失败是失败,日本人没把这当镜子看,甲午才是拐点,日本一脚踢过去,中国摔倒,书房里的光环破了,学者不再翻中庸大学,开始翻人的脾气和秉性,民族性三个字站到了案头。 德富苏峰先说话,这人当过贵族院议员,办报出书,明治政府跟他熟,他的判断很直,框架也完整,他把中国人归纳成唯利一类,仁义礼智是壳,父子之情、家国大义,遇到利字就让路,他甚至丢了个法子,说要读中国人,试着把论语倒着读,子曰忠信礼义是拿来改的,说明这些东西正是短板,他观察到遇利动作快,平时懒散冷淡,事来了像换了人,这套看法不是他一个人在写,整代人里不少人点头。 宇野哲人那边也接着说,他是哲学家,后来自民党有人拿他的理论,他把家族主义拆开,看里面的动机,说这是利己的捆绑,靠血缘把自己的利益做大,连孝顺都被理解成一种投入和回报,这些话被学界吸收,课本里藏进去,孩子们读起来不觉得奇怪。 文弱这个词贴上来,德富继续,他说从皇帝到平民都重文轻武,打仗只会摆场面,几十万大军能打的不多,他提一个细节,中国人爱吵,不爱动手,打仗也像这样,旗号很响,先去找人谈,战争像戏剧,场面要足,效果不紧,桑原骘藏也写到这一层,中国对战争没有尊重也没有准备,自卫战都拘着,军校拿清军的失败上课,义和团的虎皮披风大旗子,是看着厉害,真打一枪就散,他们把文弱总结成一种文化里的病,不愿牺牲,不愿硬碰硬。 还有一路人盯着“说话”,中野孤山的游记里写成都的事情,街边小贩会几句客套,把人说得不好意思砍价,遇到他是老师,摊主直接笔谈写久仰大名,称他大教习,价格就不好开了,他说中国人说话像唱戏,不带脾气,不伤面子,套路却一直在走,日本的交往习惯直一点,话是话,利是利,虚词不多,这套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路数,被他们叫成虚言之道,有人把它上升到欺诈的词,宇野哲人把语言也拉进来,说汉语有音乐性,有唱高调的优势,在谈判和谋利里有一种压人效果,时间久了,日本人对这种高情商变成了警惕。 更重的评价从实地跑的人来,军人和记者写的东西直接,小室信介在中国两个月后写下民风败坏这句,列了贪财、卖国、不知羞耻的见闻,他翻历史,说通敌者不少,像不当回事,高桥谦把各省按自己的印象贴标签,江苏狡,安徽也狡,湖南顽但也狡,四川男女不拘,勇敢又轻浮,广东卖淫成风,女性不以为意,这些话不是社会调查的量表,是偏见的清单。 德富苏峰还列了三件好物,鸦片、赌博、肉欲,他自己去看上海一家报社,写到编辑下午三点就在办公室吸烟枪,他把这些摆在文章里,读者看完得到一个结论,这个国家不该站在现代国家的队伍里,这些笔记和评论不只为表达,它们铺了一条路,把文化蔑视变成政策的底层理由。 尾声要把线收一收,从唯利的框架,到语言里的软骨,再到民风的标签,这一套拼成闭环,官方、媒体、课堂互相喂养,后来打仗、烧城、杀人,用的不是临时起意,是纸面上堆出来的逻辑,这些文字在历史的废墟边上看,像是给行动找一句话。 今天回头看,时代换了脸,日本不是当年的日本,中国也不是当年的中国,纸上的旧词还在,现实已经改了样,读书的人心里有数,历史能解释一些事,也不能解释全部,人走在现在,眼睛看向前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