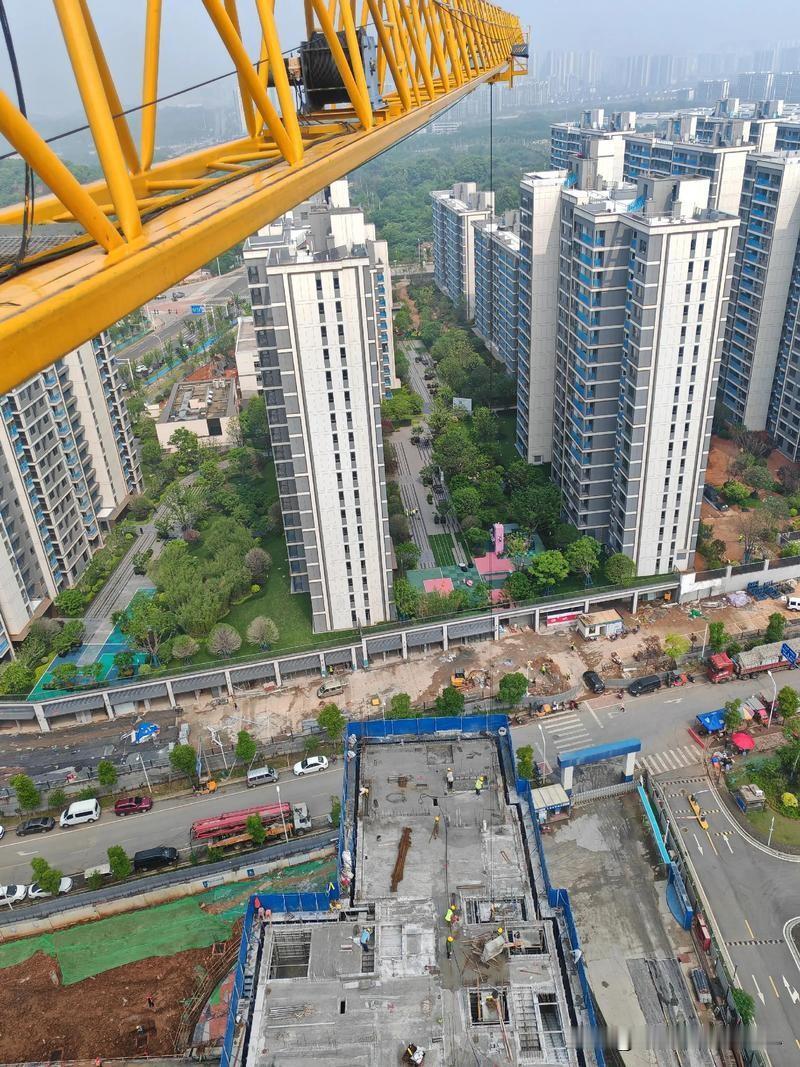我妈在别人家当阿姨,雇主想吃羊角蜜,我妈拿了一个羊角蜜洗干净,切了一盘给雇主端过去,雇主问我妈怎么不把瓜瓤刮掉,我妈解释说带瓜瓤吃着香甜,我在家一直都是这么吃的。雇主捏着银质水果叉,叉起一块带籽的瓜肉,眉头皱得像团揉乱的纸。“我们从不吃带瓤的,”她把叉子放回白瓷盘,瓷盘与桌面碰撞出轻响,“你看这籽,多影响口感。” 我妈在李姐家做阿姨的第三个月,厨房的瓷砖总擦得能映出窗外的玉兰。那天下午阳光斜斜切进来,她站在水槽前洗羊角蜜,瓜皮上的水珠顺着指缝滴在不锈钢盆里,叮咚响。她挑了个最鼓囊的,拦腰切开时,金黄的瓤裹着黑籽,像藏了一捧星星——在家我爸总说带瓤吃才够甜,连籽嚼着都有股脆香,她一直这么信。 切好的瓜块码在白瓷盘里,她端进餐厅时,李姐正坐在红木餐桌旁翻杂志。银质水果叉摆在盘边,叉尖亮得晃眼。 “李姐,羊角蜜切好了。”我妈把盘子往她面前推了推,指尖在围裙上蹭了蹭。 李姐没抬头,目光从杂志挪到盘子里,忽然停住。她捏起水果叉,叉起一块带瓤的瓜肉,眉头慢慢皱起来,像被风吹皱的湖面,最后拧成一团揉乱的纸。“小周,”她声音轻轻的,却带着点凉,“这瓜瓤怎么没刮掉?” 我妈愣了一下,手不自觉地摸了摸盘子边缘,“带瓤吃甜,汁水足,在家我和孩子都这么吃……”话没说完,李姐已经把叉子放回盘子,瓷叉碰白瓷,“叮”一声,轻得像根针。 “我们从不吃带瓤的。”她把杂志合上,封面朝上,“你看这籽,嵌在肉里,嚼起来咯吱响,多影响口感。” 我妈看着盘子里的瓜块,瓤里的籽黑亮亮的,忽然想起上周在家视频,我举着羊角蜜冲镜头晃,“妈你看,爸切的,带瓤超甜!”那时候她笑着说“慢点吃,别噎着”,现在这话堵在喉咙里,像含了块没化的冰糖。 她是不是觉得我不懂规矩?我妈捏着围裙角,指甲掐进布料。李姐家的玻璃杯永远杯口朝下扣在沥水架上,冰箱里的牛奶要标上开封日期,连擦桌子都得顺着木纹的方向——这些她都记着,怎么偏偏忘了这羊角蜜? “对不起李姐,我下次注意。”她弯腰想把盘子端走,李姐却按住了盘沿。“不用了,”她拿起叉子,叉了块没带多少瓤的,慢慢嚼着,“下次刮干净就行,你也累了,去歇会儿吧。” 我妈退到厨房时,听见餐厅里李姐打电话,“张太太说她家阿姨连草莓蒂都能雕成花,我家这个……唉,羊角蜜都不会切。”水龙头没关紧,一滴水落在盆里,和刚才的叮咚声不一样,沉得像砸在心上。 那天晚上她给我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以后在家吃羊角蜜,把瓤刮了吧,籽硌得慌。”我正啃着带瓤的瓜,含糊问“为啥呀”,她顿了顿,“没啥,刮了干净。” 挂了电话,我看着手里的瓜,瓤里的籽还沾着甜汁。原来有些习惯,出了家门就成了“不懂事”;原来妈妈的“一直这么吃”,在别人家的白瓷盘里,会变成皱起的眉头和轻响的瓷盘。 后来我再买羊角蜜,总会先把瓤刮干净,装在玻璃碗里。可吃到嘴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是籽的脆,是妈妈站在自家厨房,笑着说“带瓤才甜”时,阳光落在她鬓角的暖。
保姆打扫时,发现厕所角落粘着个微型摄像头。她取下设备,敲开雇主王先生的门:“您装
【68评论】【14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