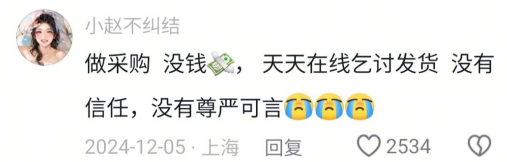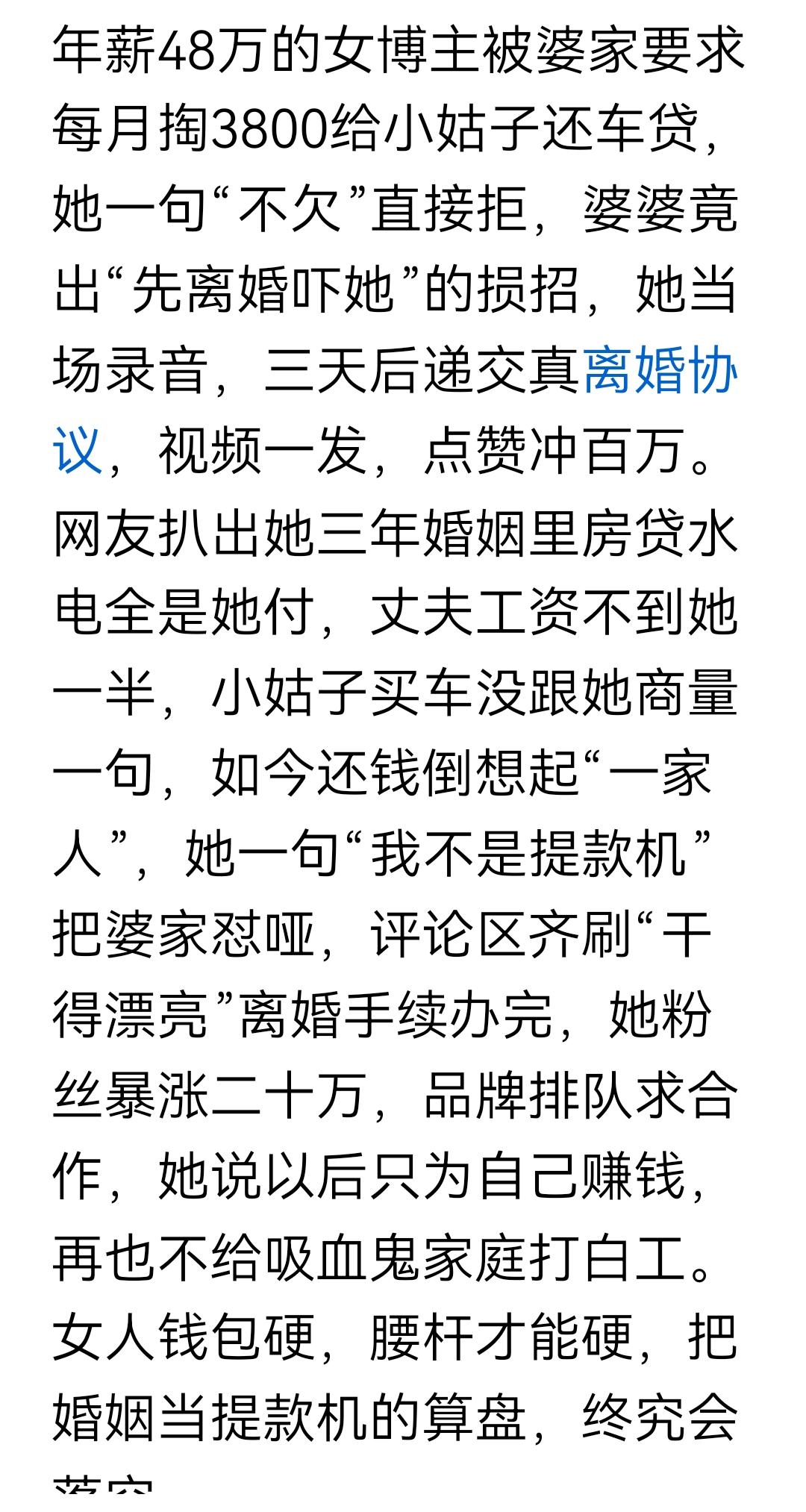我是小梅,一个普通的农村媳妇,嫁给了老实巴交的阿强。我们住在河南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村子不大,家家户户都认识,闲言碎语传得比风还快。 事情发生在前年冬天,那会儿天寒地冻,村里家家户户都忙着备年货,唯独我老公阿强家出了件大事——他的伯父,也就是我们叫“大伯”的老人,病得快不行了。 大伯那年已经九十高龄,身体一向硬朗,可突然就倒下了。儿女们(也就是阿强的堂哥和大嫂)早早给他穿上了寿衣,说是“迎老”,意思是让老人安详地走。 寿衣是那种老式的蓝布褂子,上面绣着金线,村里的规矩是,穿上寿衣三天内就该办后事了。堂哥和大嫂天天守在床前,脸上没半点悲伤,倒像是在等一个盼头。 阿强的公公(我公公)是个念旧情的人,那天晚上,他把我老公叫到跟前,声音沙哑地说:“阿强啊,你大伯待你不薄,小时候还给你买过糖。现在他快不行了,你回去看看,送他一程吧。”公公的话里带着命令,也带着一丝悲哀。 阿强是个孝顺人,二话不说就骑上电动车,冒着寒风去了大伯家。 大伯家离我们不远,就在村东头。我一辈子都记得阿强回来的那个晚上,他脸色苍白,眼眶通红。他告诉我,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死亡的气息——屋子里阴冷潮湿,大伯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寿衣松松垮垮地裹在身上,像裹着一层裹尸布。 堂哥和大嫂坐在旁边嗑瓜子,看见阿强来,连眼皮都没抬。堂哥冷冷地说:“爹已经一周没吃东西了,就喂点水,等咽气呢。”阿强走近一看,大伯的嘴唇干裂,眼睛半闭着,胸口微微起伏着,像是风中残烛。 那一刻,阿强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他想起小时候,大伯常给他做甜鸡蛋面汤——那是穷人家最滋补的东西,一碗热汤下肚,浑身暖洋洋的。阿强二话不说,转身就进了厨房。 厨房里冷冷清清的,灶台都落了灰。阿强翻出几个鸡蛋和一小袋面粉,手脚麻利地搅和起来。甜鸡蛋面汤?说起来简单,但他特意多放了点糖,又滴了几滴香油,想让大伯尝尝热乎的味道。 堂哥和大嫂在门外嗤笑:“干啥呢?爹都这样了,你还折腾啥?”阿强没理他们,端着碗走到床前,轻声唤着:“大伯,喝口汤吧。”大伯的眼睛微微睁开,浑浊的瞳孔里闪过一丝光。阿强一勺一勺地喂,汤水流进嘴里,大伯居然慢慢地咽了下去。 一碗汤喝完,大伯的呼吸平稳了点,脸上透出点血色。阿强以为这只是一点临终关怀,没想到,奇迹就这么发生了。 接下来的日子,大伯一天天好起来。阿强天天去看他,换着花样做汤:有时加红枣,有时放点姜末。不到一个月,大伯就能坐起来吃饭了;半年后,他竟能拄着拐杖在院里晒太阳。 村里的人都说这是“回光返照”,可大伯硬是活到了现在93岁,精神头比从前还好。按理说,这是件喜事,可堂哥和大嫂却恨得牙痒痒。他们原本盘算着大伯一走,就能分那点薄地和老屋,现在全泡汤了。他们开始在邻居那里嚼舌根,骂阿强“多管闲事”、“咒爹不死”,甚至说他是想独占家产。那些话像毒蛇一样钻回我们耳朵里——村头的王婶传话说,堂嫂在井边洗衣服时,指着我们家方向骂:“阿强那蠢货,一碗破汤坏了大事!爹要活到一百岁,我们还得伺候到老死!”堂哥更过分,逢人便说阿强是“克星”,害得他们没了指望。 我和阿强听到这些话,心都凉了。阿强是个闷葫芦,只会埋头干活,从不辩解。可我这当媳妇的,气得浑身发抖。我们两家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前逢年过节,还串门送点年货;现在呢?路上碰见堂哥家的人,他们鼻孔朝天,扭头就走。我们也不搭理——凭什么热脸贴冷屁股?我拉着阿强躲开,日子久了,两家成了仇人。 有时夜里,我躺在床上想:阿强做错了什么?他只是想让大伯走得不那么痛苦,却无意中揭穿了人心的贪婪。一碗甜汤,救了一条命,却碎了一段亲情。如今,大伯还健在,常偷偷托人给我们送点自家种的菜,可堂哥他们连这都要骂。村里人说闲话,说我“挑唆”阿强,可天地良心,我只是心疼老公——他善良得像个傻子,换来一身脏水。 去年冬天,大伯过93岁生日,堂哥家办了个小席,没请我们。我和阿强远远看着那灯火,心里五味杂陈。阿强低声说:“小梅,我做错了吗?”我握紧他的手,只摇了摇头。 有些事,对错没那么简单。善良有时像一把双刃刀,能救人,也能伤人。可如果重来一次,我相信阿强还会端上那碗汤——因为良心,比闲言碎语重得多。 现在,我们依旧过自己的日子,只盼着时间能冲淡这些恩怨。或许等到大伯真走的那天,一切都会不同?谁知道呢。人生如戏,我们都在戏里演着各自的角色,只是这出戏,演得太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