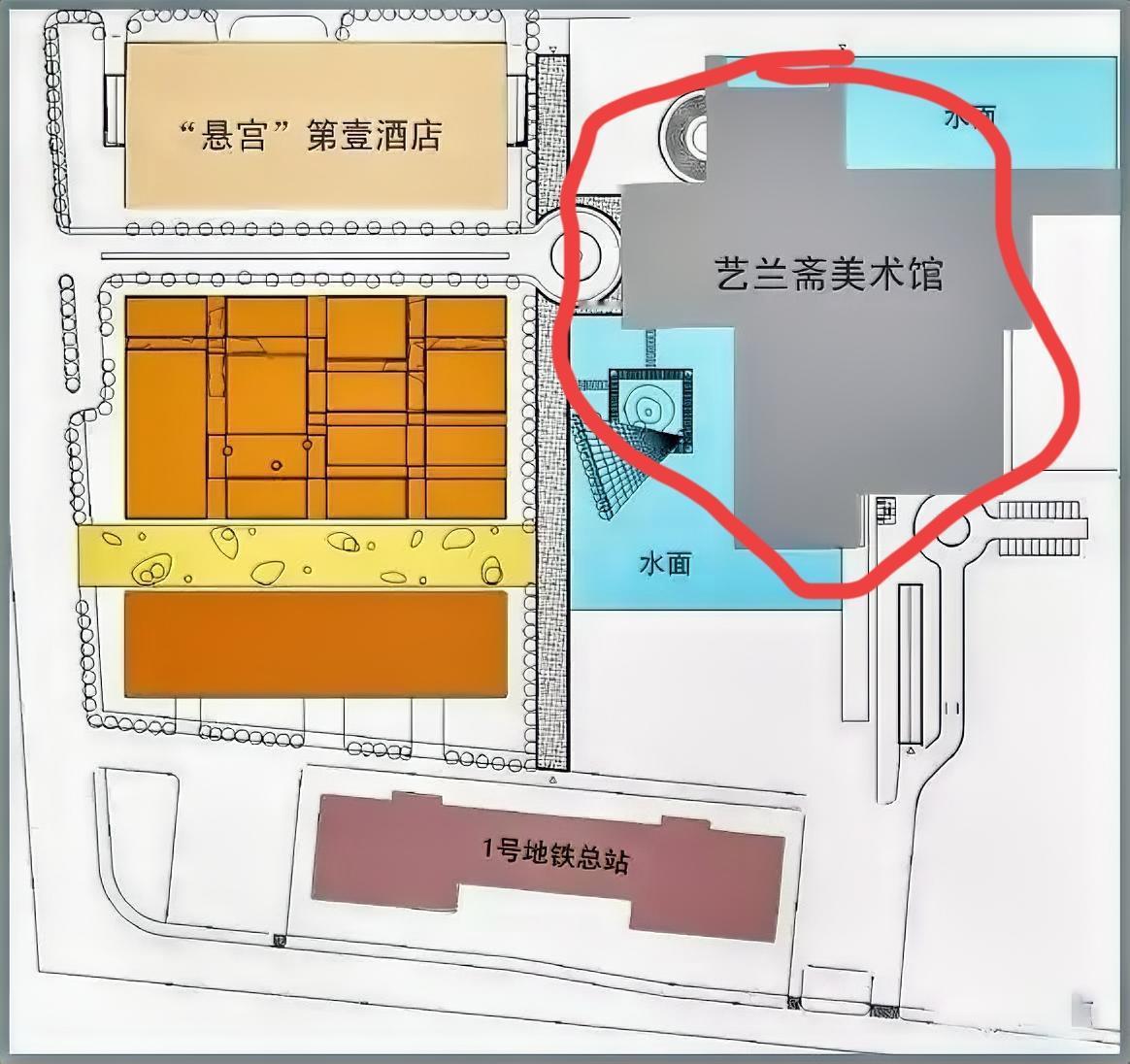1980年,国家以2400元的价格收购一名大三学生的画作。没曾想,不久之后,这幅画竟然成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厅里,有一幅画总能让观众驻足。 画面巨大,几乎铺满整面墙。 画中是一位老农的头像,他的脸像是被岁月反复揉搓过的古铜色土地,每道皱纹都深得像沟壑,干裂的嘴唇微张,双手捧着一个粗瓷碗。 这就是罗中立创作的《父亲》。 许多人站在这幅画前,会沉默很久,仿佛能从那双略显浑浊的眼睛里,看到整片田野和一个时代的重量。 这幅如今被誉为镇馆之宝的作品,它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次深夜的凝视和一颗被现实深深触动的心。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除夕夜,当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学生的罗中立,在校园附近看到了难忘的一幕。 一个老农裹着旧棉袄,蹲在公共厕所旁,守着粪池。 除夕是团聚的日子,空气中飘着饭菜香,远处有零星的鞭炮声,但这个老人却在寒夜里与污秽为伴,只为给土地积攒一点肥料。 这个画面像钉子一样楔进了罗中立的心里。 他跑回住处,快速在纸上勾画下那个孤独的背影。 这张速写,成了后来一切的开端。 罗中立对这样的面孔并不陌生。 他早年在四川大巴山地区生活了近十年,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同吃同住。 他熟悉他们手掌上老茧的硬度,懂得他们望着庄稼时的眼神。 他寄住家的老人邓开选,那张被山风和阳光雕刻的脸,早已刻在他的记忆里。 但那个除夕夜的身影,让他有了必须表达的冲动。 创作的过程并不顺利。 他最初画了《守粪的农民》,画面有夜晚的背景,但总觉得那个身影被环境淹没了。 他又尝试《粒粒皆辛苦》,描绘农民捡拾谷粒的虔诚,可还是觉得隔着一层。 他想要的不是讲述一个故事,而是让观者直接“面对”这个人。 最终,他决定采用前所未有的方式——用画领袖像的巨幅尺寸,来刻画一个最普通的农民。 他去掉所有背景,只留下一张脸,一双手。 他在画布上细细描绘: 那些皱纹不是皮肤的纹理,是长年弯腰耕作被岁月压出的痕迹,是汗水流淌冲刷出的沟渠; 那双手关节粗大变形,指甲破损,嵌着永远洗不净的泥土。 那是与土地死死纠缠了一生的手。瓷碗里只有一点清水,映不出丰足,只照见艰辛。 当这幅尚未命名的巨作逐渐成形,它强烈的真实感震撼了周围的人,也带来了疑虑。 那时正值社会思潮变化的时期,文艺创作刚从固定的模式中试探着伸出头。 有人认为画中形象“太苦了”,“不够积极”。 在作品送审参加1980年全国青年美展前,一位前辈建议,在老人缠头的白毛巾边加一支蓝色的圆珠笔。 这个生硬的添加像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它暗示着这是位“有文化的新农民”,使作品得以通过审查,悬挂在展厅墙上。 展览上,这幅画最初叫《我的父亲》。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站在画前,久久凝视。 他对罗中立说,把“我的”去掉吧,就叫《父亲》。 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这一字之改,意义深远。 画中人从此不再仅是某个具体的人物,他成为了土地的儿子,成为了用脊梁扛起生活的、无数沉默父辈的集体肖像。 最终,《父亲》荣获展览一等奖,被国家收藏。 那支为妥协而加的圆珠笔,后来也成为艺术与时代关系的独特见证。 四十多年过去,这幅画的价值早已超越艺术本身。 每当人们站在画前,看到的不仅是一张脸,更是一个民族走过的艰辛道路,是那些在土地上默默耕耘、用双手养育了国家的无名者。 它源于一次真实的触动,成于一次勇敢的直面,最终升华为一个民族关于泥土、生存与坚韧的永恒记忆。 主要信源:(中新社——人物丨罗中立:当年画出《父亲》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