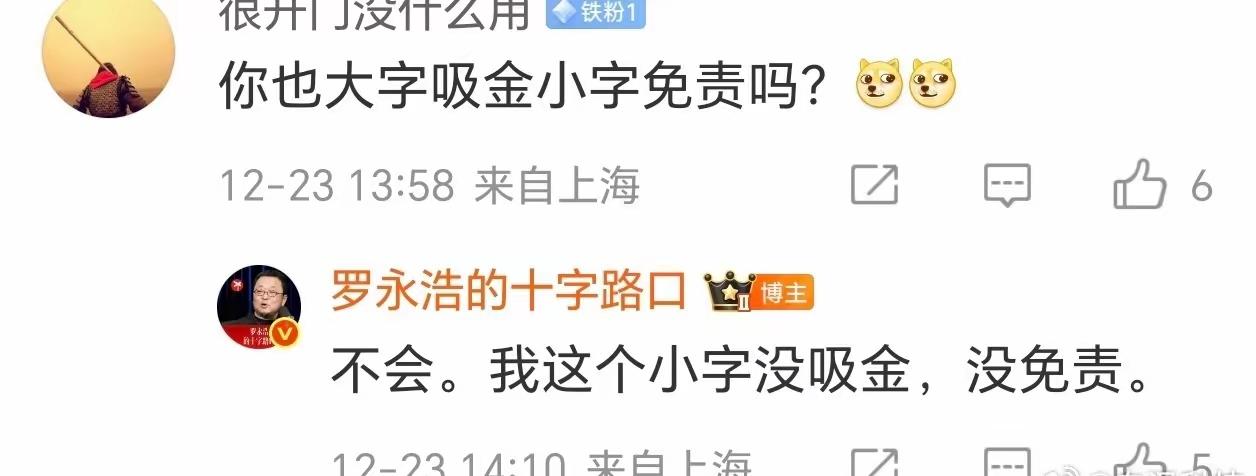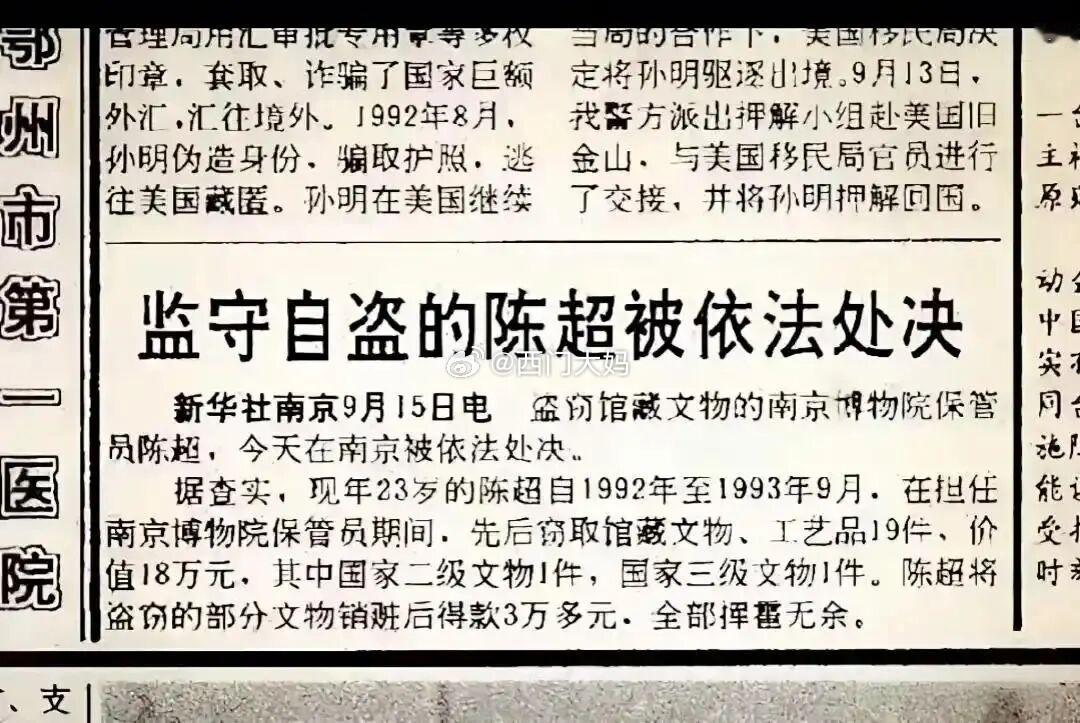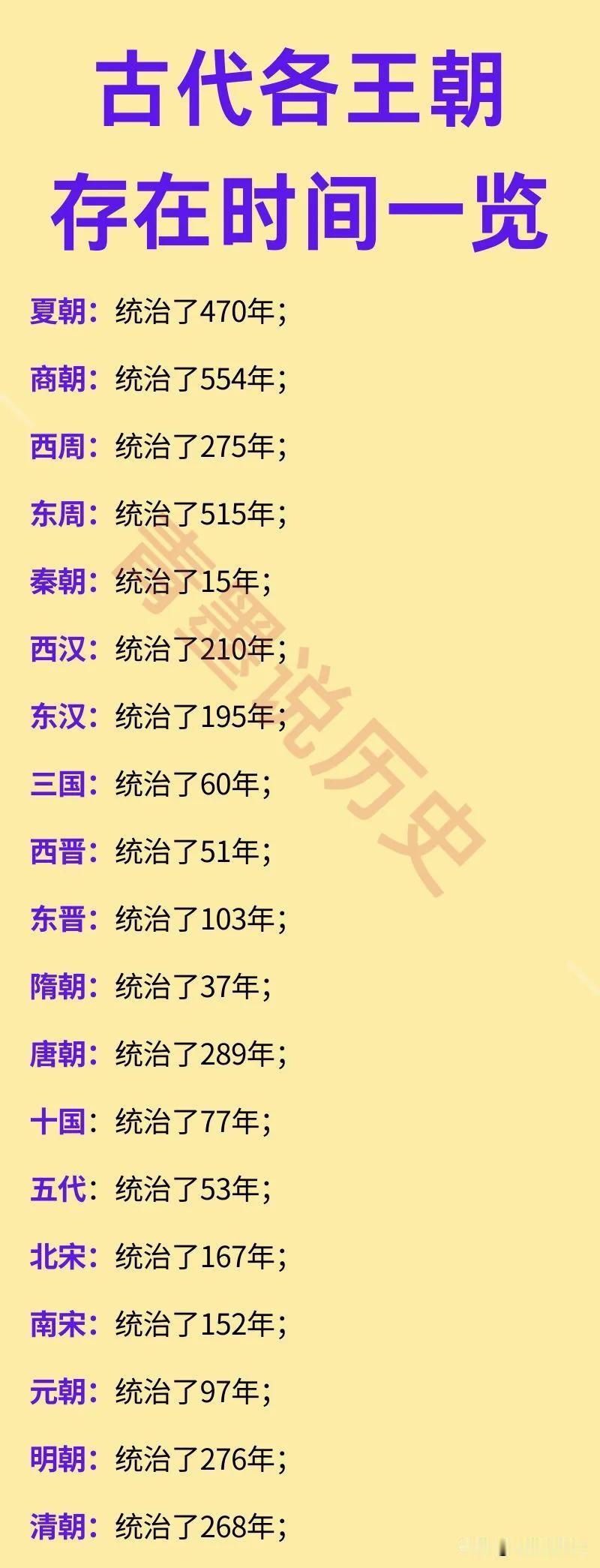1964年深秋的北京胡同,钱学森刚跨进家门,就被妻子蒋英堵在院里。 “三个月不回家,外面有女人了吧?”蒋英抱着胳膊,语气里带着气。 那会儿的保密制度严得很。 钱学森6月去戈壁时,只跟家里说“临时出差”。 签《保密承诺书》那天,他在办公室坐了很久,钢笔尖在纸上戳出个小坑。 后来蒋英去单位问,同事支支吾吾只说“保密原因,联系不上”。 她在办公楼后的花坛边坐了一下午,看着月季花瓣被风吹落,眼泪把衣襟洇湿了一片。 10月16日那天,蒋英去王府井买东西,突然听见报童喊“号外!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她挤进去抢了张报纸,手抖得差点拿不住。 照片上的蘑菇云在戈壁上空翻滚,她猛地想起钱学森走前那晚,在台灯下写材料,铅笔在纸上画着类似的弧线,嘴里念叨“这个角度,稳定性最重要”。 钱学森回家后,从提包里拿出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些焦黑的土块。 “试验场带回来的,”他递给蒋英,“你看这颜色,是冲击波灼烧后的痕迹。” 蒋英捏着瓶子对着光看,突然笑了:“原来‘蘑菇云小姐’长这样。” 钱学森也笑了,伸手擦掉她眼角的泪,“让你担心了。” 其实蒋英没闲着。 钱学森忙得顾不上家时,她把西方航空工程文献翻译成中文,字写得工工整整。 有次钱学森翻到她译的《飞行器动力学》,在页边写了行小字:“这里的气动系数算得比我还准”。 后来这页纸被蒋英剪下来,夹在乐谱册里,成了两人心照不宣的秘密。 现在军工研究所的年轻人们,大概很难想象当年的日子。 有次我去参观钱学森故居,看见那盏1964年的台灯还摆在书桌上,灯座上有个小缺口,是钱学森当年不小心用计算尺磕的。 讲解员说,蒋英晚年常坐在这盏灯下,翻钱学森的手稿,一看就是一下午。 那天钱学森展示焦土样本时,台灯的光刚好照在玻璃瓶上,土块的纹路在墙上投出细碎的影子。 蒋英后来在日记里写:“那些影子像跳动的音符,和他算的弹道曲线一样,都是写给国家的情书。” 如今东风导弹的尾焰照亮夜空时,总让我想起那盏台灯,信任和理解,从来都是最坚固的铠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