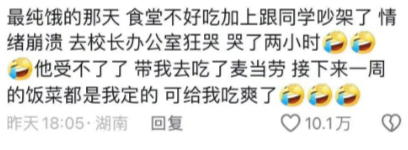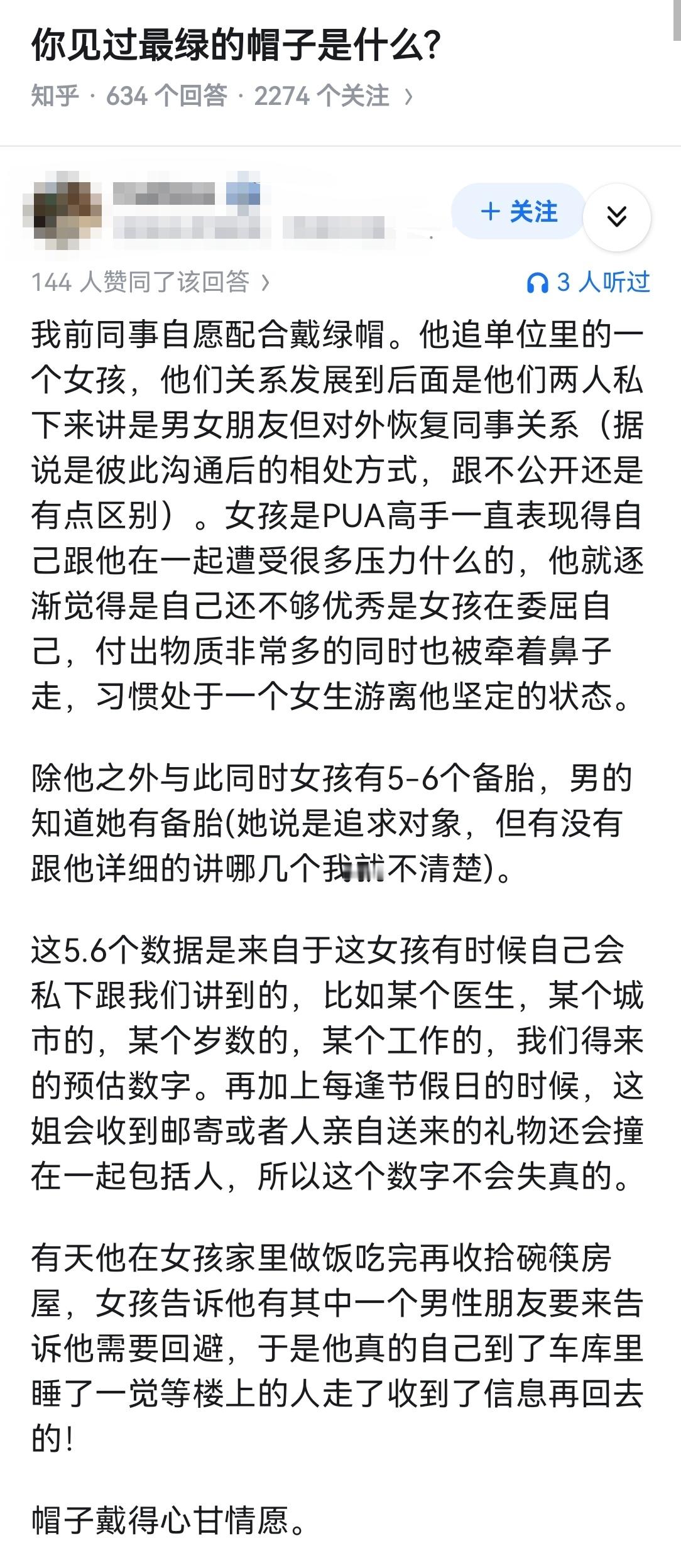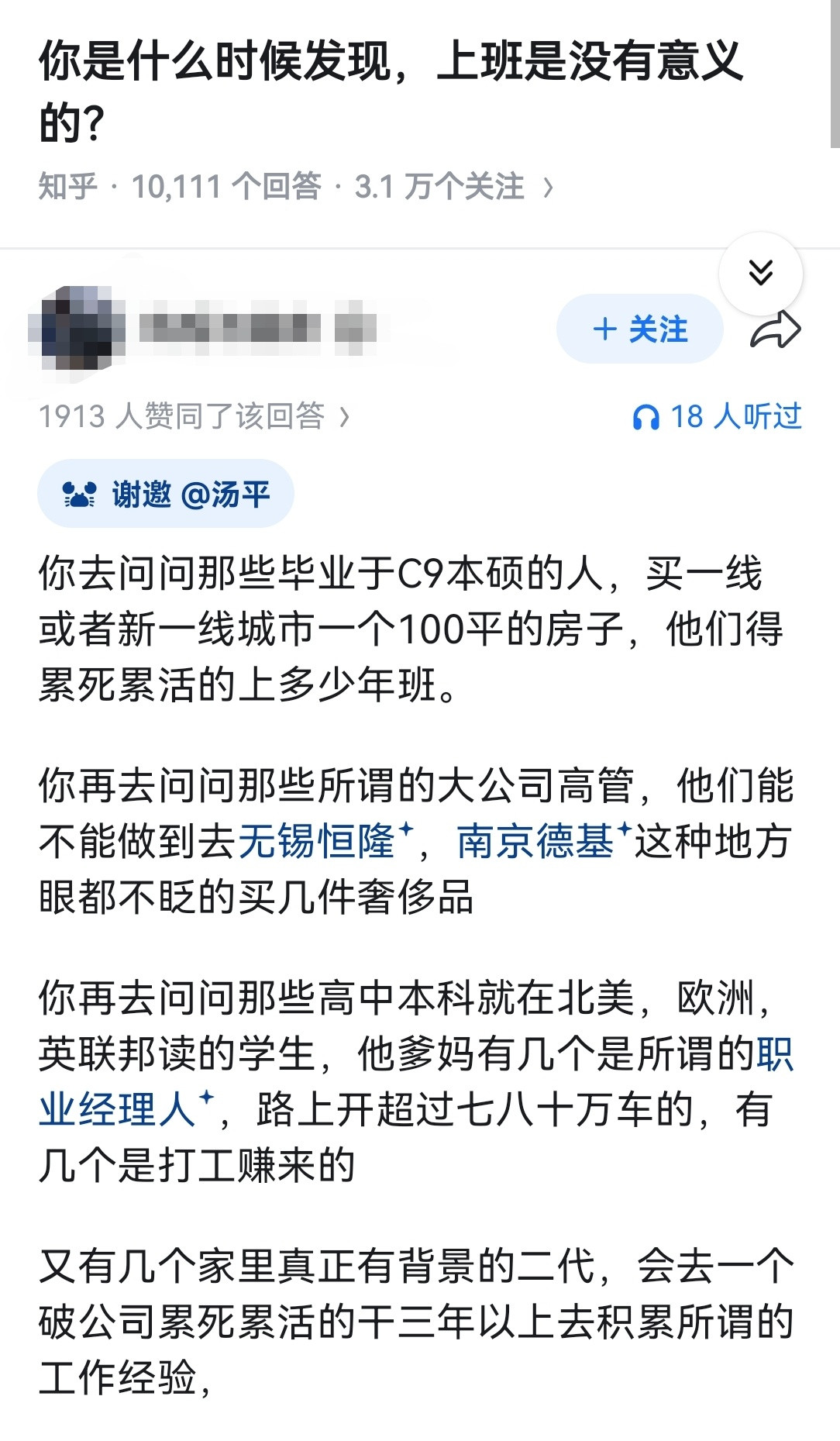我姐的前公婆,可都是精明人,说话办事滴水不漏的,用我们这里的方言,就是两口子都可奸了,心眼子可多啦! 姐姐离婚三年,我带着外甥小宝在老小区住,前公婆就住隔壁楼,阳台对着阳台,晾衣服都能看见对方晒的被子,可我愣是没跟他们说过一句话——心里头还堵着气呢,想起当初他们怎么变着法儿让我姐受委屈。 上周三傍晚,我下班回家,刚走到单元门口,就看见前婆婆蹲在花坛边,手里拿着个小铲子,正往塑料袋里装土。她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用皮筋扎在脑后,几缕白头发飘在额前,像秋天没扫干净的枯草。 “小敏,下班啦?”她抬头看见我,手里的铲子顿了顿,声音有点怯生生的,不像以前那样大着嗓门指挥我姐干这干那。 我“嗯”了一声,想绕开她上楼,她却赶紧站起来,塑料袋往我手里塞:“这是楼顶种的韭菜,刚割的,嫩得很,给小宝包馄饨吃,他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我没接,塑料袋口的韭菜叶子蹭到我手,湿乎乎的,带着股泥土腥气。心里头犯嘀咕:这老两口又想干啥?以前我姐买韭菜,他们总说“外面的菜打农药,吃了对孩子不好”,现在倒主动送来了? “不用了,阿姨,我们刚买过菜。”我往后退了一步,手里的包带勒得肩膀疼。 前婆婆的手僵在半空,脸上的笑也僵了,像被冻住的面团。她低下头,用铲子扒拉着花坛里的土:“我知道,你们还记恨我们。其实……其实当年是我们糊涂,总怕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就想着多攥点钱,多管点事,以为那样是为他好,没想到把你们都逼走了。” 我愣住了。这话要是三年前说,我能把菜篮子扣她头上,可现在听着,她声音里的颤音像根细针,轻轻扎了我一下。 这时候,前公公从楼洞里出来,手里提着个保温桶,桶盖没盖严,飘出股鸡汤味。他看见我,脚步顿了顿,把保温桶往身后藏了藏,脸涨得通红:“老婆子,跟人家说这个干啥,快回家。” “你别拦我!”前婆婆突然提高了声音,眼泪啪嗒掉在韭菜叶子上,“小宝上周发烧,我在医院走廊坐了半夜,看着他小脸烧得通红,心里跟刀割似的。以前我总说‘孩子小,哪那么娇气’,其实是我怕花钱,怕你姐嫌我们穷,帮不上忙还添乱……” 我想起上周小宝发烧,我抱着他在医院排队,确实看见个穿蓝布褂子的老太太在走廊长椅上坐着,当时没在意,原来真是她? 前公公叹了口气,把保温桶递过来:“早上杀了只老母鸡,给孩子炖的汤,放了点山药,你姐以前说喝这个养胃。你要是不嫌弃……”桶把手上缠着圈胶布,磨得发亮,像是天天拎着似的。 我接过保温桶,桶底烫得我手心发麻。低头看那韭菜,根部还沾着湿泥,叶子上有几个虫眼——哪是买的,分明是自己种的,舍不得打农药。 这时候,小宝从幼儿园回来了,背着小书包跑过来,看见前公婆,愣了愣,突然喊:“爷爷奶奶!” 前婆婆眼泪流得更凶了,蹲下来想抱孩子,又赶紧把手在褂子上擦了擦:“哎,小宝乖,奶奶给你留了糖葫芦,在冰箱里冻着呢。” 前公公从口袋里摸出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两根糖葫芦,山楂红得发亮,糖衣结着白霜:“早上在早市买的,你小时候就爱吃这个,说酸溜溜的,吃完能多吃一碗饭。” 我心里猛地一酸——小宝三岁时爱吃糖葫芦,后来换牙,我姐不让吃,这事我都快忘了,他们怎么还记得这么清楚? 回家的路上,小宝举着糖葫芦啃得满脸都是糖渣,我提着鸡汤和韭菜,保温桶的温度顺着手指往心里钻。突然想起以前总觉得他们“奸”,可“奸”的人,会在医院走廊守着生病的外孙半夜?会记得孩子多年前爱吃的东西?会把自己种的菜、炖的汤,小心翼翼地送过来,还怕被嫌弃? 或许,他们不是“奸”,是穷怕了,是老了没安全感,总想着用算计和强硬护住自己那点可怜的尊严。就像我奶奶常说的,人心是块田,你种啥就收啥,他们以前种了刺,现在想种点花,可土都板结了,哪那么容易发芽? 那天晚上,我给姐姐打电话,说了这事。姐姐沉默了半天,说:“明天我带小宝去看看他们吧,顺便把我买的按摩仪给他们送去,听说前公公腰不好。”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隔壁楼的阳台亮着灯,前公婆的身影在窗户上晃着,像是在收拾什么。韭菜在厨房的篮子里放着,绿油油的,透着股劲儿,像极了那些被生活磋磨过,却还没死心的希望。 现在想起他们,我还是觉得这老两口心眼多,会算计,可那心眼子里,除了精明,好像也塞着点别的——是惦记,是后悔,还是人老了,就想抓住点实实在在的暖和气?谁知道呢。反正日子过着过着,你就会发现,这世上哪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人,大多都是揣着点私心,又藏着点真心,在烟火气里慢慢熬着罢了。
我姐的前公婆,可都是精明人,说话办事滴水不漏的,用我们这里的方言,就是两口子都可
凯语乐天派
2025-12-30 16:32:49
0
阅读: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