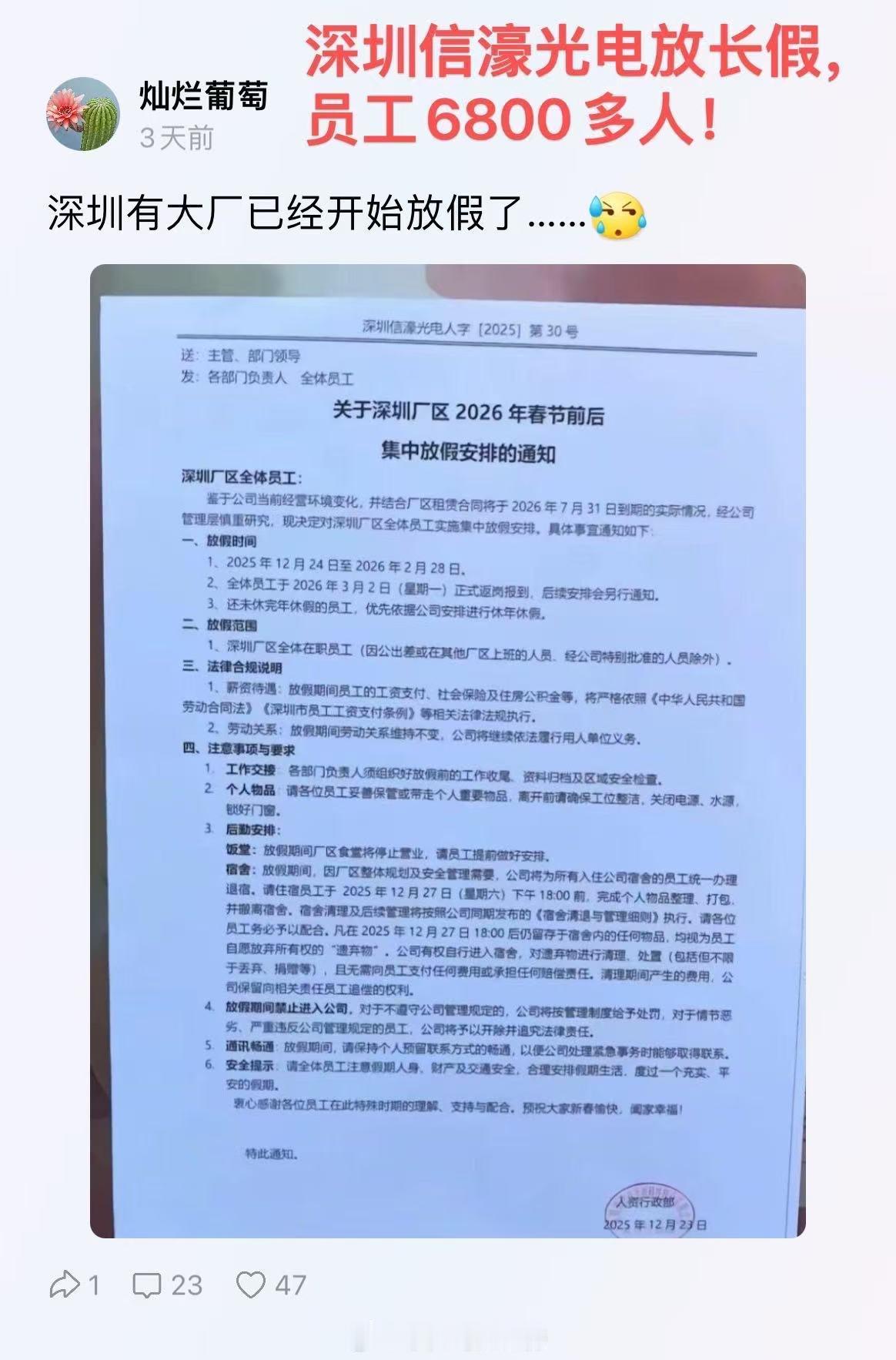1945年,46岁的王世瑛再次怀孕。 重庆的夏天总是格外闷热,尤其是那年,空气里除了湿气,还飘着战争尾声特有的紧张。 她站在窗前,手轻轻放在隆起的腹部,听着远处隐约的防空警报,心里盘算着给远在美国的丈夫张君劢写封信。 可提笔又放下,联合国会议正是关键时候,她不想让他分心。 记得二十年前在上海,泰戈尔访华的招待会上,冰心拉着她的手说:"这人虽爱谈政治,骨子里却是个纯粹的读书人。 "那时张君劢刚从德国回来,穿着笔挺的西装,在人群里侃侃而谈哲学与宪政。 她没想到,这个总把家国挂在嘴边的男人,会成为她一生的牵挂。 婚后她成了他的"私人秘书",誊写手稿时,总能在字里行间看到他没说出口的温柔。 抗战打响后,张君劢忙着组党办报,满中国跑。 她带着四个孩子在北碚落脚,看着街上逃难的孩子越来越多,索性用家里积蓄办了所难童学校。 邻居老李婆婆常说她傻,"自己孩子都顾不过来",她却觉得,这些孩子也是国家的未来。 1943年《新华日报》来采访,她只说:"君劢在前线为国家争前途,我在后方守着这些孩子,都是应该的。 " 肚子里的孩子来得突然。 医生说高龄产妇风险大,劝她通知张君劢。 她摇摇头,那时联合国宪章正在起草,他提出的"文化主权平等"条款好不容易被采纳,"国家的事比我的事要紧"。 8月12日那天,她被抬进宽仁医院时,还在叮嘱校工:"明天的课别耽误了。 "只是她没想到,这次见面,成了她和孩子们最后的告别。 消息传到纽约时,张君劢正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言。 秘书递过电报,他当场就红了眼眶,手里的文件散落一地。 后来听人说,他中断会议赶回国,三天没吃一口饭,只是反复念着"曾经沧海难为水"。 在重庆的墓前,他写了副挽联:"廿年来艰难与共,辛苦备尝,何图一别永诀"。 字是抖着写的,每个笔画都像浸着泪。 晚年的张君劢住在纽约的公寓里,用十二年写了本《世瑛行状》。 手稿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尽是些生活细节:她喜欢在灯下绣兰花,给孩子们讲故事时会模仿各种动物叫声,办学校时为了筹钱在雨里站了两个小时。 每年春节,他都会带着这本手稿去墓地,坐在墓碑前轻声读,像她还在世时那样,絮絮叨叨说家里的事。 去年去斯坦福大学,我见过那本泛黄的手稿。 最后一页写着:"世瑛走后,我才明白,她守着的不只是我和孩子,更是这个国家最珍贵的东西。 "现在重庆北碚的难童学校旧址还在,墙上嵌着块小石碑,刻着"1938-1945,王世瑛与28个孩子"。 阳光好的时候,石碑上的字会发亮,像她当年办校时,总在深夜亮着的那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