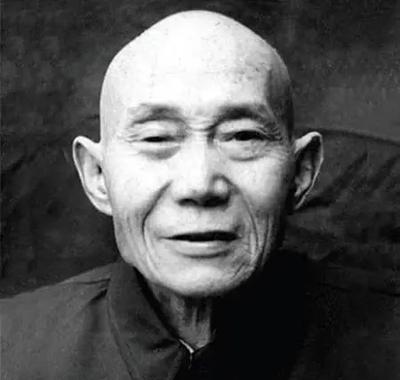1937年冬的南京,吴长友把二姨太推向日军军官时,手指在发抖。 他以为这是场划算的交易,用一个女人换全家富贵,却没看见对方眼里一闪而过的轻蔑。 女人的尖叫像被剪刀剪断似的突然停了。 吴长友僵在原地,日军士兵正把他的二姨太往门外拖,那身他亲自挑的旗袍被扯得变了形。 他这才发现,自己准备的“投名状”,在侵略者眼里不过是块随手丢弃的脏布。 南京城里的吴长友,靠着家里的地产和鸦片生意,早把自己活成了土皇帝。 1937年秋,城外炮声越来越近,他还在扩建豪宅,觉得战火离自己远着呢。 直到日军攻破城门,他才慌了神,连夜翻出所有积蓄,又想起年轻貌美的二姨太,觉得这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饭局上的清酒还没冷透,日军军官就搂着二姨太的腰笑。 吴长友本来想上前说句“太君慢用”,却被士兵一脚踹在地上。 额头磕在青砖上的疼,远不及听见二姨太哭喊时的心惊他突然意识到,这些人根本不把他当“合作者”,只当他是条摇尾乞怜的狗。 几天后,吴长友的豪宅被翻了个底朝天。 日军说他“私藏军火”,其实就是看上了他保险柜里的金条。 他跪在地上,看着士兵把古董花瓶砸得粉碎,看着自己新买的地毯被军靴踩来踩去,那上面绣的“富贵吉祥”四个字,像在嘲笑他的愚蠢。 没人知道二姨太最后去了哪里。 只听说那段时间,南京安全区的国际委员每天都在记录失踪的女人,有个和二姨太同龄的寡妇,被日军从地窖里拖走后,再也没回来。 吴长友后来疯了似的找,却在一个雨夜被日军当成“可疑分子”捅死在巷子里,血顺着青石板流进排水沟,和雨水混在一起。 吴长友到死都盯着那块被踩脏的地毯,好像想从“富贵吉祥”的图案里找出答案。 其实答案早就写在南京城的断壁残垣上背叛同胞的人,从来没有活路。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那些和他一样当过汉奸的人,不管当初多风光,最后都得为自己的选择付账。 1937年冬的南京,吴长友把二姨太推向日军军官时,手指在发抖。 他以为这是场划算的交易,用一个女人换全家富贵,却没看见对方眼里一闪而过的轻蔑。 女人的尖叫像被剪刀剪断似的突然停了,他这才发现,自己准备的“投名状”,在侵略者眼里不过是块随手丢弃的脏布。 南京城里的吴长友,靠着家里的地产和鸦片生意,早把自己活成了土皇帝。 1937年秋,城外炮声越来越近,他还在扩建豪宅,觉得战火离自己远着呢。 直到日军攻破城门,他才慌了神,连夜翻出所有积蓄,又想起年轻貌美的二姨太,觉得这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饭局上的清酒还没冷透,日军军官就搂着二姨太的腰笑。 吴长友本来想上前说句“太君慢用”,却被士兵一脚踹在地上。 额头磕在青砖上的疼,远不及听见二姨太哭喊时的心惊他突然意识到,这些人根本不把他当“合作者”,只当他是条摇尾乞怜的狗。 几天后,吴长友的豪宅被翻了个底朝天。 日军说他“私藏军火”,其实就是看上了他保险柜里的金条。 他跪在地上,看着士兵把古董花瓶砸得粉碎,看着自己新买的地毯被军靴踩来踩去,那上面绣的“富贵吉祥”四个字,像在嘲笑他的愚蠢。 没人知道二姨太最后去了哪里。 只听说那段时间,南京安全区的国际委员每天都在记录失踪的女人,有个和二姨太同龄的寡妇,被日军从地窖里拖走后,再也没回来。 吴长友后来疯了似的找,却在一个雨夜被日军当成“可疑分子”捅死在巷子里,血顺着青石板流进排水沟,和雨水混在一起。 吴长友到死都盯着那块被踩脏的地毯,好像想从“富贵吉祥”的图案里找出答案。 其实答案早就写在南京城的断壁残垣上背叛同胞的人,从来没有活路。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那些和他一样当过汉奸的人,不管当初多风光,最后都得为自己的选择付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