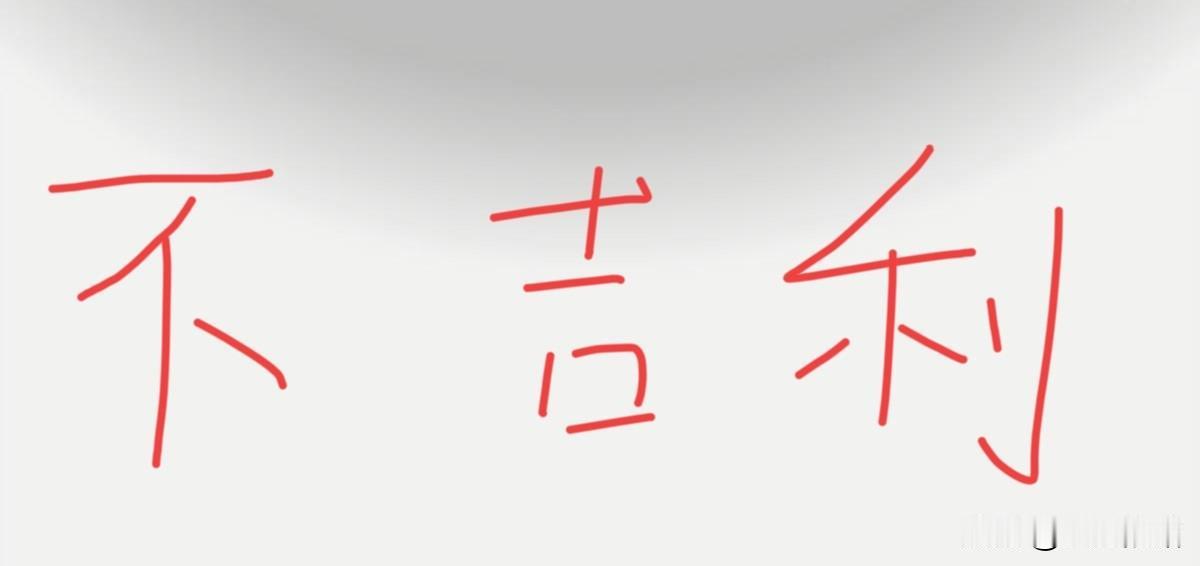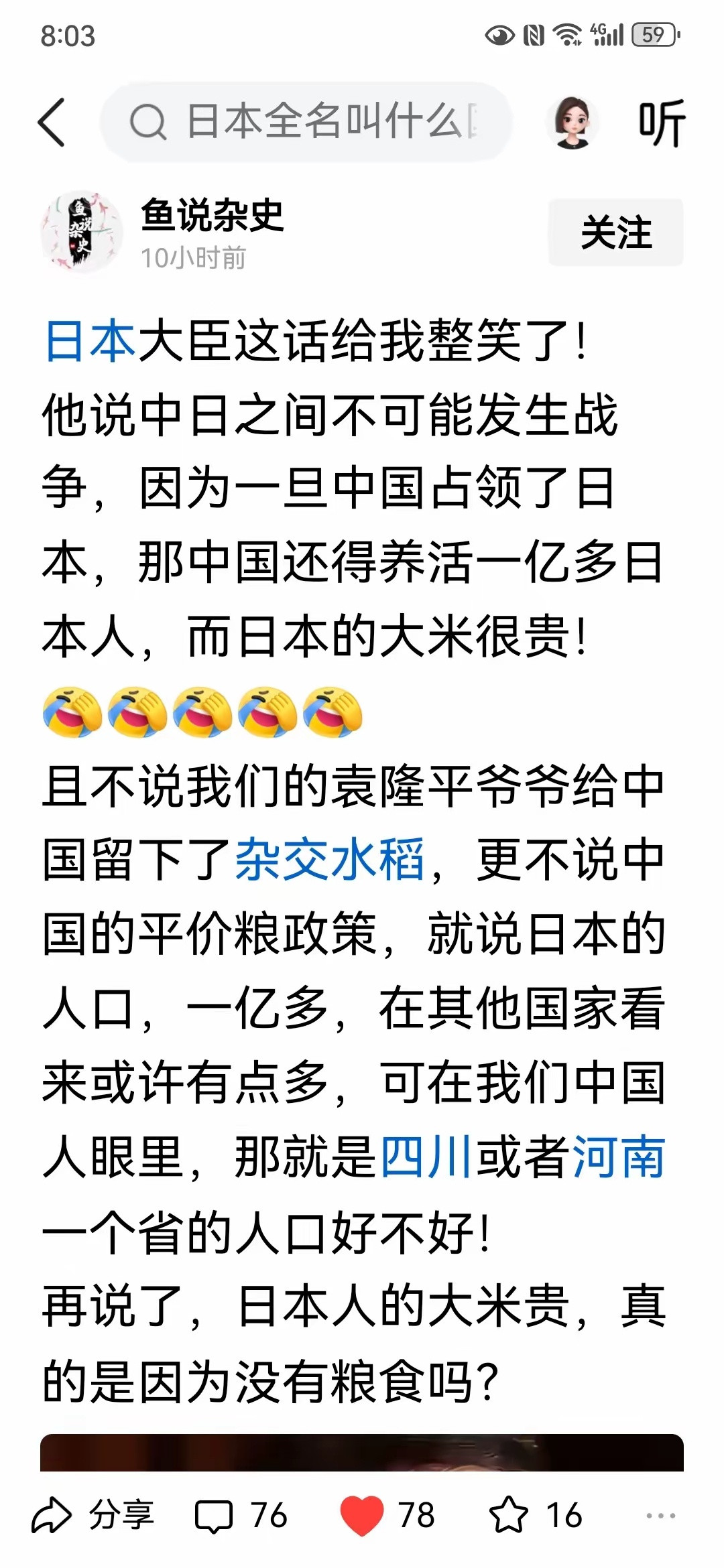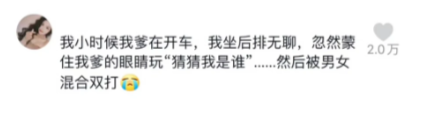[微风]2018年,记者问老干妈的创始人陶华碧:“老干妈为什么一直用这家玻璃厂的玻璃瓶,是为了保鲜、防渗漏、更显质感吗?”陶华碧摇摇头,记者好奇:“那到底是为了什么?”陶华碧随后的回答,让现场所有人愣住。 1996年,贵阳街头的凉粉摊前,还没有什么“商业帝国”,只有一个为了供两个孩子读书而拼命的农村妇女,那时陶华碧面临的不仅是资金短缺,更是产品根本“立不住”的危机。 为了省钱,起初的辣酱装在塑料瓶里,但这简直是场灾难:滚烫的油泼进去,劣质塑料不仅容易变形渗漏,还会让辣酱染上一股怪味,刚攒下的回头客尝一口就皱眉。 为了保住招牌,她认准了必须要用耐高温、不串味的玻璃瓶,她揣着仅有的一点积票跑遍了全城的工厂,得到的回复却像是在驱赶乞丐。 大厂的门卫甚至都没让她进去,主管们甚至懒得正眼看这个穿着磨破了解放鞋的女人,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话:“几百个?简直开玩笑,哪怕是一万个起订我们都得考虑考虑。” “小本生意”这四个字,像一座大山,把她的求生路堵死了。 就在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凉粉摊眼看就要断供的时候,南明河畔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玻璃厂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两个落魄者的抱团取暖。 那天的车间里充满了破败的气息,已经三个月发不出工资的王厂长,看着眼前这个眼神里透着狠劲的女人。 陶华碧并没有像乞讨者那样示弱,而是蹲在地上,指着那一堆落灰的样品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承诺:“您先赊给我几十个瓶子应急,等辣椒酱卖出去,货款一分不少。如果我陶华碧这辈子做赔了,我就来给您厂里扫大街,扫到把债还清为止!” 正是这股市井里迸发出的决绝打动了对方,在车间主任老张头的默许下,王厂长破例开了仓库,那一刻,不仅是三百个瓶子的交接,更是两颗心在绝境中的碰撞。 当那批特制的加厚玻璃瓶装满红油透亮的辣酱摆上摊位,穿西装的商贩甚至还要拿起瓶子对着光端详,感叹这玻璃看着比塑料“高级十倍”。 这笔几十个瓶子起的“烂账”,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变成了一份哪怕董事会吵翻天也无法撼动的铁律。 随着商业版图的扩张,尤其是到了2000年以后,无数精明的包装商蜂拥而至,报价单一张比一张低,塑料包装技术的进步也让成本诱惑变得巨大。 2012年的那场内部会议上,矛盾彻底爆发。在这个数据至上的时代,年轻的高管拿着财务报表,甚至连儿子李贵山也试图劝说:“妈,改用轻便的新型塑料瓶,运输损耗能降,成本至少缩减三成,年轻人也喜欢轻量化。” 陶华碧的反应是激烈的,她甚至拿起桌上的玻璃罐重重地砸了下去,在她看来,这不仅仅是省钱的问题,她随手抓过竞品的塑料瓶对着灯光,指着那薄得透光的材质反问众人:高温杀菌的时候,有没有毒素渗进去?而在三十度的高温下暴晒三天,只有她手里这只笨重的玻璃瓶,能保证里面的红油依旧清亮诱人。 “那是人家救命的恩情,哪怕再便宜,咱也不敢换!”指着墙上那张2003年与王厂长在烟囱下的合影,满屋子的高管鸦雀无声。 当年的小作坊变成了知名企业,而那个差点倒闭的国营厂,也依靠这源源不断的“十年长约”和每月十万级的订单量,硬生生挺过改制潮,活成了西南最大的供应商。 这份“死磕”不仅仅停留在情义层面,更内化成了近乎偏执的质量标准,哪怕是远销美国的今天,在厂区的流水线上,依然保留着源自上个世纪的传统。 那是当年老张头教给陶华碧的验货诀窍:无论是谁,每批新瓶入库,都得用指关节或者指甲盖在瓶身上划过。 必须是清脆的“铮铮”声,那是玻璃烧制火候到位的回响,差一点闷响都不行,年轻的95后质检员小林或许并不完全理解这背后的沧桑,但他知道,敲三下听声辨质,是这里必须遵守的铁律。 而在大洋彼岸,当金发碧眼的家庭主妇举着瓶子惊呼这是“中国调味品里的爱马仕”时,那特意保留的凹凸防伪纹理,其实藏着当年那个秃顶厂长手把手教给陶华碧的吹制工艺。 所谓的契约精神,在这里被还原成了最原始的模样:你予我雪中炭,我还你一世暖。 甚至这段关系已经超越了一代人,去年冬天,老厂长的孙子大学毕业回来接班,接到的第一笔生意依然是来自老干妈的订单。 而在那整整齐齐码放的三十万只玻璃瓶箱底,压着一封陶华碧的亲笔信,信里提到的不再是生意,而是重提当年王哥说过的一句“瓶子碎了可以再造”。 暮色四合,南明河的流水倒映着窑炉不灭的火光,生产线上那一排排鱼贯而出的红色玻璃罐,在塑料包装泛滥的货架丛林里,依然站得笔直而坚硬。 这就是中国商人最质朴的商业哲学——有些账是记在账本上的,算得清利润;而有些账是刻在骨头里的,算的是良心。 信源:中华包装瓶网——老干妈玻璃瓶背后的秘密 - 包装瓶网--专业的瓶子、瓶盖交易网站... 界面新闻 看完陶华碧的经营哲学,你就会明白老干妈为何如此强大